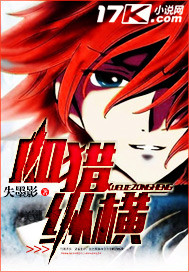出云号在仁川河里航行,走到第三天,风平浪息,速度快了不少。小厮卢侗不知是染上了时疫,还是得了风寒,看看一病不起。身子忽冷忽热,高烧不止。周武消停了一些,忙前跑后,热的时候用冷水浇,冷的时候给他盖上厚厚的棉被。
妮可也吓得不轻,赶紧跑过来帮忙。可自己一无经验,手脚又笨,根本就插不上手。所谓帮忙,也是帮倒忙,添乱,不是打翻了药罐,就是弄泼了汤碗。周武又不敢责备她。毕竟自己是奴才,她是主子。只好劝她回舱房休息,她能自己照顾自己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卢侗的病丝毫没有起色,且越拖越糟。周强坐不住了,央了船上的老水手过来察看。老水手看了看卢侗的舌苔,又替他把了下脉,沉吟了半晌,斩钉截铁地说:“小伙子一定是感染了恶性疟疾,得马上住院治疗,耽误不得,也耽误不起了。”
无奈其时,出云号正在河上航行。一江如练,天水茫茫,根本就靠不了岸。还是老水手有办法,拿出一面漕运的三角旗挂在桅杆上,迫停了一艘货船。恰好货船也到仁川郡码头,老板周武、卢侗都认识。
老板见是漕运使府上的人,二话没说,就带着水手上来,把卢侗抬上了他的船。货船扬起风帆,其去如飞。
卢侗一走,所有的银子都归周武保管、用度和花销。周武失去了约束和监管,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不分日夜在舱室里撩妹,花天酒地,摆阔,充大尾巴狼,渐渐地露出了他破落户的本色。
至于妮可,周武也管得少了。一日三餐就是一碗煎豆腐,一碗咸萝卜条。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把主仆之位颠倒了过来。妮可敢怒而不敢言。
也不知是妮可命中该有此一劫,还是时运不济,她渐渐感觉到有点胸闷,呕吐,食欲不振。看看也像卢侗一样,身子忽冷忽热,高烧不止,身上起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妮可几近昏迷,成天恍恍惚惚。
起初,周武还熬点汤药,搞点冷饭给妮可充饥。后来,他也渐渐地失去了耐性,开始对妮可不闻不问。饱还是饿?吃了还是没吃?他都满不在乎,把漕帅的叮嘱丢到了九霄云外,根本就不管妮可的死活了。
倒是船上的水手和旅客见妮可可怜,经常跑过来问候,或施一碗粥,或给几个煎饼,饥一餐,饱一顿,妮可才活了下来,才不至于丧命。人的一生里,总有一些怀念或感恩,在生命中最寒冷、最残酷的时候出现。
周武有了银子,又失去了同伴卢侗和主人妮可的管束,胆子愈发大了起来,私欲日渐膨胀。每天只要出云号一靠岸,他就背着银子上岸去赌。去的时候意气风发,信心满满;回来时,垂头丧气,两眼血丝。
人哪,总是想孤注一掷,最后一搏,把失去的一切一下子都赢回来。没想到越陷越深,越赌越输。以至于输了良心,输了人性,输了仁爱和自尊。
其实,赌搏,赌的就是一个心态,一种心境。优秀的赌手面对巨额财富、海量钱财,都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而有些赌手,见财起意,利欲薰心,没赌之前就已经乱了阵脚,就已经输了。
眼看着包袱里的银子越来越少,越来越轻,周武的心一下子慌了起来,萌生了孤注一掷时念头。有赌就有输赢,是死是活?总得赌一赌,搏一搏。他不信自己的手一直这么背,命一直这么苦,人总有云开日出、时来运转的时候。
一天,出云号照例进港泊靠,周武拿起包袱掂了掂,剩下的银子不多了,约摸八十两左右。他胡乱地扒了一碗冷饭,拎着包袱就上了岸。港叫龟山港,是仁川河上游最繁华的一个港口。街上人来人往,游人如织,港口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周武路过一家按摩店的时候,从里面浪出来几个妖艳的女郎,个个涂脂抹粉,举止轻佻,很生猛地往周武怀里扑,心肝宝贝地叫个不停。周武吓了一跳,本能地护住了包袱里的银子,就像老母鸡见了黄鼠狼一样,逃之夭夭。比较而言,周武对女人不感兴趣,他嗜好的是赌。
在一家叫聚云轩的赌场,周武停了下来,抬头望了望挂在檐上的招牌,记忆中还有些印象,前些年他来过几次。有一次他赢了一百多两,有一次赢了二百多两。算起来,这里应该是他的福地。
周武进了屋,上了楼,屋子里吵吵嚷嚷,热闹非凡,牌九,麻将,炸金花,轮盘赌,一应俱全。堂倌很客气地迎了上来,点头哈腰地说:“客官,牌九还是麻将?里面三缺一。”堂倌回过头,指了指最里面的一间包箱。
“麻将吧!”周武点了点头,拎起包袱朝麻将房走去。相对而言,周武会打麻将,牌技不错,且胜算较大。
包箱里有人抽烟,乌烟瘴气。三个搭档,一个中年秃子,一个满脸雀斑的老男人,一个镶大金牙的锦衣男,早就等在那里了。周武朝各位点了点头,客气地坐了下来,开始码牌,摇骰。骰子滴溜溜地旋转,周武的心也悬了起来。
刚开局,周武的手气很顺,连糊了两手大牌,进了十几两银子,乐得眉开眼笑。看来,这里真是他的福地。周武鼓起勇气,乘胜追击。无奈,手气不佳,被镶大金牙的锦衣男连成了几手大牌,把刚刚赢的银子又吐了出来,还另赔了十几两。
赌局渐入佳境,镶大金牙的锦衣男手气很顺,想什么就来什么,想瞌睡就有人送来了枕头。盘盘抢在周武前面截糊,把他气了个半死,忍不住咒爹骂娘,捶胸顿足,把麻将牌摔得卟卟响。
紧接着,镶大金牙的锦衣男又连糊了几手大牌,可周武一摸装银子的包袱,里面空空如也,只得赊欠。连赊了几盘,镶大金牙的锦衣男不耐烦了,一推麻将,愤愤地说:“不打了,不打了,输现钱,赢赊账,没意思!伙计,还有值钱的东西没有?可以抵债的?”
“有,我老婆,国色天香,可以抵一千两银子。”周武心如电转,一下子就想到了女主人妮可。
“抵一千两?你老婆是天仙?”大金牙两眼鼓凸。
“要不,那就五百两。”周武讨价还价。
“哼,想得美。”大金牙不依不饶。
周武和大金牙唇来舌往,互不相让。最后,以六十两银子成交。可怜的妮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被侍候自己的奴才出卖。周武有了卖妮可的六十两银子壮胆,继续码牌,摇骰。无奈,手气太背,大势已去,一个回合下来,六十两银子又输得干干净净。
牌桌上,大金牙眉开眼笑地点着赢来的银子,眼角的鱼尾纹根根翘起,一行三人立马押着周武回船讨债。周武带路,抖抖索索地站在妮可的舱房前,苦丧着脸,不敢抬头,脸红得像泼了猪血,支支吾吾地说:“就这间舱房,人在里面。”
大金牙十分得意,嘿嘿一笑,飞起一脚踹开了舱门,扯开嗓门大喊:“美人,你丈夫已经把你输给我了,六十两银子。今晚,咱们来个洞房花烛。”
昏暗的豆油灯下,妮可正睡得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踹门,缓缓地转过脸来。大金牙见到妮可的脸,就像大白天看见了鬼魅,身子筛糠似地抖了起来,一屈膝跪倒在地上,捣蒜似地磕个不停。
大金牙妮可认识,他就是扒过她钱的锦衣男子。只不知几个月不见,他怎么镶上了金牙?原来,妮可和他在亦庄分手后,锦衣男子贼性不改,又因扒窃被一个蛮汉抓住,打豁了嘴,磕掉了两颗门牙。
锦衣男子索性镶了两颗金牙,扮成一个阔佬的样子,流窜到龟山港一带作案。扒了一些日子,嫌扒窃风险高,来钱慢,干脆就和几个哥们在赌场里设了个局,专宰周武这样的肥猪。居然,屡屡得手,连妮可都赢下了。
周武不识时务,懵头懵脑地走了过来,扯了扯大金牙的衣角,嘻皮笑脸地说:“老板,我老婆不错吧!值不值一千两银子?”依周武的本意,是想找大金牙再讹一笔银子,自己好去扳本。无奈周武挑水找错了码头。
大金牙从地上一跃而起,一把揪住周武的衣领,左右开弓,狠狠地搧了他两个耳光,咬牙切齿地说:“打死你,打死你个瞎了眼的狗奴才,欺主罔义的东西。你他妈的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卖的是老子的祖师娘哪,绑起来!”
候在舱门外中年秃子和雀斑男人得令,不由分说,立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粗麻绳,四攒五勒,把周武捆得结结实实,像端午的粽。秃子和雀斑男人还不解恨,秃子在周武脸上啐了一口。雀斑男人对准周武的身子,在他的膝弯里狠狠地踹了一脚。周武一声闷哼,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大金牙看到瘦骨峋嶙、奄奄一息的妮可,实在是有些心痛,竟忍不住唏唏嘘嘘地哭了起来,有些激动地说:“我的个姑奶奶,你怎么瘦成了这个样子?天啦,你叫我们怎么向老堂主交代。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俗话说:盗亦有道。知著堂堂主巢三巢天虎闻讯,带着一大帮徒众连夜赶来了,把出云号围得水泄不通。龟山港恰好是他的地盘,老堂主夫人有难,他岂能袖手旁观?强龙不压地头蛇,在龟山港,他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人多力量大。徒众们请郎中的请郎中,买吃食的买吃食,把个妮可像祖宗一样供了起来。郎中探了探妮可的脉,看了看她的舌苔,拈了拈胡须,若有所思地说:“女主像是风寒入內,身子忽冷忽热,在老朽店里住上几天,开几剂中药,发发汗,祛祛寒就好了,不妨事,不妨事!”
徒众们发一声喊,卸下了一扇舱门,做成了一副简易担架,七手八脚地把妮可抬了上去,盖上了厚厚的棉絮,前呼后拥地跟在老郎中后面,向老郎中的药店飞奔。那情形,就像上演了一出人道主义的集体救援。
巢堂主送走妮可,倒剪着双手正要上岸,大金牙赶了上来,拱了拱手,客客气气地说:“堂主,这个欺主罔义的家伙怎么发落?他为了六十两银子,卖了我们的祖师娘!”大金牙指了指吓得瑟瑟发抖的周武。
“沉江,这样的败类留在世上就是浪费粮食。”巢堂主看了周武一眼,伟人似地挥了挥手。
徒众们得到最高指示,马上找来一只大麻袋,抱脚的抱脚,摁手的摁手,劈头盖脸地套在周武的头上。周武被摁,双脚乱蹬,大喊大叫。不知是谁?随手脱下了一只臭袜子,死死地塞在周武的口里,堵住了他的嘴。
一个壮汉抽出一根竹杠,绕上麻袋口上的绳子,抬着周武朝岸上飞奔。正是凌晨三、四钟左右,河面上一片静寂,三三两两的渔火,闪闪烁烁,就像魔鬼的眼睛。河畔的村庄里,隐隐传来零零星星的犬吠。
在一个很陡峭的河岸边,徒众们放下麻袋,合力推向悬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壮汉气喘嘘嘘地赶了过来,挥了挥手上的一张关防,大喊:“堂主,使不得啊使不得,这个家伙还有些来头,有漕帅府的关防。”
巢堂主阴沉着脸,拿住关防凑在灯下看了看,确实盖着漕帅府的朱红大印。巢堂主哈哈大笑,三下两下将关防扯得粉碎,迎风一抖,碎片满天,斩钉截铁地说:“别说是关防,就是盖了皇帝老子的玉玺,老子也照沉不误。这样的人留在世上,就是对善良的糟践!”
话音未落,麻袋骨碌碌地滚下了悬崖,传来了扑通一声巨响,溅起了一片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