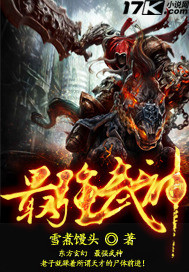苔丝全权代表西津县广济豆制品公司,与妹妹艾米莉谈完项目,商定了一些合作事宜。艾米莉连夜北上,回了首都。苔丝留在西津县继续打理生意。广济公司才刚刚成立不久,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断奶,百废待兴,还离不开大人的照顾。
跟国贸商行联了姻,靠上了国贸商行这块金字招牌,广济就等于接上了天线,就像穷书生中了状元。无论是信用还是货源都有了保障,生意也越做越顺。渐渐地,从单一的豆制品加工,逐渐扩展到五金、百货、陶瓷、布匹、粮油等二十多个门类。白花花的银子滚滚而来,苔丝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有了银子作后盾,苔丝又把触角伸进了邻县,先后在广平府的罗山县、孟德县、先沛县、尚义县、宁武县设立了分号,逐步占领了农村初级市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并有了自己的码头,船队,货物集散、存储仓库。
占领了农村初级市场,苔丝慢慢把目标瞄准中型城市,并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先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百货公司,巧用借壳上市的方式,成功打入了广平府,占领了市场,赢得了口碑和商机,事业如日中天。
广济公司的姐妹们都摸不清苔丝的来头,再加上她自已守口如瓶。一时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她是波斯来的公主,精通十八国语言,能掐会算,能知未来休昝。还有的说,她是儒商鼻祖陶朱公的女儿,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不值钱,什么东西俏,什么东西不俏,闻一闻就知道了。
还有的人传得更神。说国贸商行那么大的老板,都对刘小梅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刘小梅一定是天上的神仙下凡,财白星君赵公明元帅男托女生。并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和广济公司扯上了关系,有了刘小梅的帮衬,发财致富那是分分秒秒的事。
苔丝一笑置之。
俗话说: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夜行。不知怎么的,苔丝想去看看许超大哥,想去看看梅英生了没有?生的是男是女?这个想法一旦明朗,就愈来愈强烈得不可控制了。一连几天,弄得苔丝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里乱得一团糟。
启程的那一天是个晴天,阳光明媚,碧空如洗,苔丝的心情就像惠风一样和畅。她情不自禁地吹响了口哨,指挥车伕和僮仆,在马车里放上米面、肉菜、食用油、绸缎、布匹等等,满满荡荡,直到放不下为上。
车队浩浩荡荡,一共有四辆马车,第一辆由皮毛店的罗老板驾车开路,第二辆由苔丝带四个护卫居中,第三辆、第四辆装的都是货物。罗老板的皮毛店早不开了,他被苔丝收编,成了孟德县商行的总经理,活得滋润、气派多了,脸色红润,肚子也大了起来。
车声辚辚,马蹄嘚嘚。
车窗外的村庄、树木、河流、田野,都潮水似地向后退却。苔丝止不住地百感交集,浮想联翩。人的一生离不开恩和怨,也跳不出恩怨的窠臼。人活在世上其实很简单,就是有恩报恩,有怨报怨。
不知什么时候,马车慢了下来,走走停停,简直是蜗行蚁步,把苔丝急得吐血,派了一个护卫下去打听。护卫回来报告说,前面山下老虎咬死了人,家属闹事,有官兵封锁了道路,一时半刻恐怕走不了。
走不了,就只有等。苔丝坐在马车内,等得心急火燎。车窗外,隐隐传来了惊天恸地的哭声,声音高亢,尖锐,一声长,一声短,抑扬顿挫,就像锐器划在玻璃上。苔丝反正闲得无聊,索性下了车,朝哭声大步走去。
哭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来,被老虎咬死的人还不少,蒙着白布,摆在老百姓晒棉花用的蕈子上,高高矮矮,长长短短,一共有九个。这些老虎也有些怪,咬死人不是为了吃饱肚子,而是为了好玩,或者,疯狂报复。
苔丝不知是搭错了哪根筋,突然来了兴致。她依次揭开白布,察看了那些人的伤口。有咬掉胳膊的,有咬断腿的,有咬掉耳朵的,有咬坏屁股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场面既有几分血腥,也有几分恐怖。
现场有官兵把守,不时还有些衙役、捕头出出进进。老虎是林中之王,是山上的猛兽,衙役、捕头们就是想管,也管不了,也没这个胆量。衙役、捕头欺欺老百姓还可以,要真正与老虎为敌,恐怕会吓得个个打摆子,人人尿裤裆。
老百姓可管不了那么多,更何况家里死了人,正在气头上,窝了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他们一拥而上,揪辫子的揪辫子,抓头发的抓头发,把衙役、捕头们的衣服撕成了布条条,揍得哭爹叫娘,满地找牙。衙役、捕头们挨了打,一迭声地叫人向知县老爷求救。
知县老爷还没到,道路却通畅起来。苔丝赶紧上了马车,车队浩浩荡荡向许家村进发。昨天刚下过雨,道路有些坑坑洼洼,车子驶进泥坑里,溅起一朵朵浑浊的水花,胶皮轮子上沾满了屎一样的黄泥。路上看完热闹回来的老百姓,都自觉地避在两边,议论纷纷。
上了岔道,再走二、三百米,就是许家村的地界了。苔丝的心莫名地激动起来,你说怪不怪?虽然这里算不上故乡,她却有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
远远望去,许家村沉浸在一片苍翠之中,绿树掩映,林子里浮满了紫色的雾霭,鸡鸣、犬吠、牛哞、牧童的吟唱,应和着溪水里,鸭子拍打着翅膀、嘎嘎乱叫的声音,组成了一曲雄浑而又辽阔的交响,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音符。
在许超家的葡萄架下,马车缓缓地停了下来。罗老板的性子急,扯开了嗓门大喊:“许大哥,你在家吗?”屋里无人应声,水井旁却站起来一个女人,背上用绑带绑着一个孩子。是许超的妻子梅英
梅英有些腼腆,竖起一根指头嘘了嘘,有些心痛地说:“罗大哥,你轻点声。许超为了打虎,已经熬了五、六个通宵了,人都瘦得脱了形。这不,刚刚睡下。”
罗老板撩开稻草帘子,苔丝看见,屋子里的稻草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猎人。有抱着铁叉子的,有拿着木棒棒的,有枕着伙伴大腿的,一个个衣不解带,疲倦之极,睡得跟猪一样死沉。看来,虎患不除,他们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苔丝不忍心去打扰许超,就和梅英坐在水井旁的麻石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苔丝这才知道,瞎眼老娘上个月走了,坟在埋在对面的树林里。
梅英生的是个儿子,八个多月了,叫许勇,同他爹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宽额头,大眼睛,长大了,一定会像他爹一样,迷死不少女孩。苔丝忍不住抱了过去,在孩子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苔丝还听说,近段日子以来,老虎经常出来伤人,见到活物就咬,吓得商旅行人都不敢过岗,农民不敢进山耕种,樵夫不敢上山砍柴。
知县老爷下了死命令,限令猎户们在一个月之内肃清虎患。并三天一比,五天一限,动不动就把猎户们拘去敲打。猎户们没被老虎伤到,倒被这些狗衙役打得死去活来。许超的身上就满是棒疮,走路也一瘸一瘸的,痛得咬牙切齿。
看到梅英满脸泪光,苔丝也十分心痛,六神无计。她吩咐随从们轻点声,以不打扰许超睡觉为前提,把车上的米面、肉菜、食用油、绸缎、布匹等都搬进厨房,等会儿给各家各户都分一点。本来是想风风光光,衣锦还乡,在人前显摆、显摆,却碰到了这档子的倒霉事。苔丝有些沮丧。
就在这个时候,空中传来了镗镗几声锣响,一队官兵挎刀执戟、耀武扬威地冲进了院子。领头的头戴乌纱、身穿蟒袍,看样子,是个知县。苔丝以为是老熟人、西津县的陈知县,想去打个招呼,见个礼,一看不是,又悻悻地坐了下来。
知县一勒马缰,在院子中央停了下来,气急败坏地大喊:“搜,给我搜仔细一点,看猎户们回来了吗?”一个士兵撩开了稻草帘子,大声报告:“知县老爷,猎户们都躺在屋子里睡觉呢!”
“好哇!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不给本官去抓老虎,却躲在屋子里睡懒觉,抓…抓…都给老子抓起来,往死里打!”知县老爷有点结巴,脸涨得通红,接着又喊:“执刑官,藤杖侍候,每人重责六十,以儆效尤!”
骑在马上的兵马都头一声令下,士兵们一拥而上,鹰拿燕雀,把猎户们从睡梦中抓了起来,一个个五花大绑,在院子里站成了一排。
第一个挨打的是许超,因为他是猎户头头,负有领导责任,重点教训的对象。许超倒没什么,一不讨保,二不求饶,就像到邻居家里去喝酒一样随便。
许超挨打,苔丝就坐不住了。她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轻蔑地看了知县一眼,冷冷地笑着说:“听见了吗?放了,给我把他们都放了,现在,马上!”
知县被苔丝的气势吓住了,可他很快就镇定下来,气势汹汹地说:“你是谁?敢对知县老爷指手划脚?你把自己当根葱,谁拿你醮酱?”
“我叫刘小梅,是陈宽、陈知县的朋友。”苔丝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知县正准备喝斥苔丝几句,喝令执刑官马上动手。这个时候,一个老衙役走了过来,附住了知县的耳朵,叽叽咕咕地耳语了几句。
知县的脸立马由青变黄,又由黄转红,满脸堆笑地说:“下官胡青,新上任的知县,不知是陈宽、陈知县,不陈宽、陈知府的故人驾到,有失远迎,得罪,得罪!”
“哼。”苔丝点了点头。她万万没有想到,知县会变脸变得这么快。
“放了,放了,陈宽、陈知县已经荣升广平府知府了,刘小姐,你要替我多多美言几句啊!”胡知县挥了挥手,还是有点结巴,哭丧着脸,接着又说:“刘小姐,下官也没办法啊!这帮刁民要抬着尸体,到广平府、到益稼郡去告御状,我拦也拦不住,连我的蟒袍都扯烂了。”
苔丝暗自有些好笑,好不容易才忍住。她抬起了头,朝知县望了过去。果然,胡知县的蟒袍扯脱了线缝,开了一条口子,露出了里面红颜色的底裤,春光乍泄。脖子上呢?也被挠得青一块,紫一块,血迹斑斑,像狗舔过一样。
更为搞笑的是:胡知县的脚上的粉底朝靴,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一只。没办法,他只好用一只草鞋代替,一只脚穿朝靴,一只穿草鞋;一只脚是土豪,一只脚是乞丐,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不丁不八,滑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