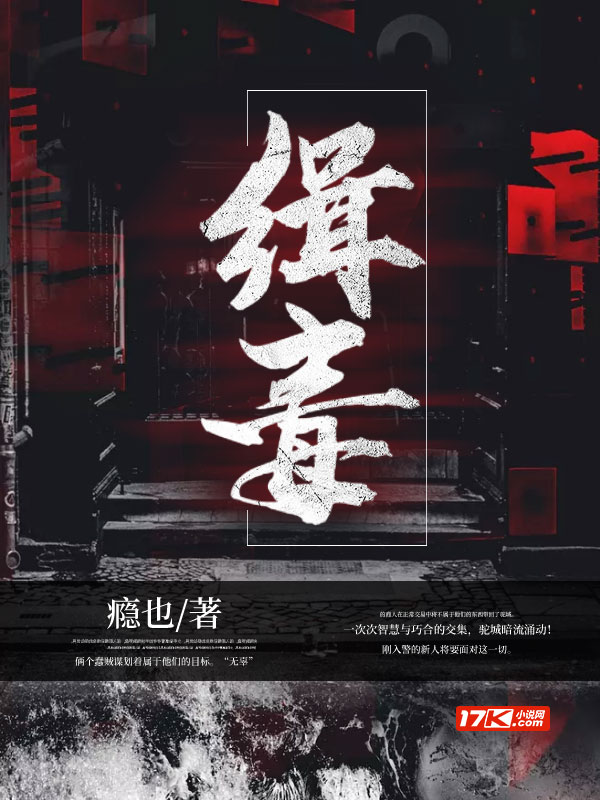苔丝的心情糟透了,一点都不好。
苔丝化名刘小梅,沦落成黄记豆腐铺里的一个豆娘,为了完成每天的定额而不停操劳。每天两斗黄豆的定额,对于一个熟练的豆娘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对于从小养尊处优的苔丝来说,就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打豆腐、卖豆腐,其实,就像作物套种、轮作,必须环环相扣。每天早上出门时要把黄豆泡好,泡胀,再挑着晚上打好的豆腐出门,沿街叫卖。运气好的话,下午二、三点货能脱手。运气背的话,卖到月亮出来也卖不完。
回到家,又得赶紧到库房领新豆,磨早上泡好、泡胀的豆子,磨好豆浆又得赶着点卤,烧锅,过滤,压制豆腐。第二天一早又得泡黄豆,出门卖豆腐。
过日子就好比推磨。而人哩,就像一头蒙住了眼睛的毛驴,不停地推着石磨、围着生活旋转,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第一次上街卖豆腐,苔丝怎么也开不了口。你不开口,谁晓得你在卖豆腐?大家都以为她是个哑巴。渐渐地,苔丝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可她喊一声,脸也要红半天。想想自己一个千金大小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却要靠卖豆腐为生,她就要惆怅半天。
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从第一次开始的。有了第一次,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所有的第一次加在一起,再生发开来,就是多姿多彩的人生。
一来二去,苔丝就摸清了门道,找到了一些经商的规律。她发现:靠近南关市场的人流特别多,每天有早、中、晚三个高潮,其他的时间都是淡季。
苔丝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她在南关市场进口处支了个摊儿,抓住早、中、晚三个节点。同时,她还增加了豆干、豆筋、豆腐脑等其他品种。盆大刮得粥来。一天下来,她除了上交给黄老板的例子钱,居然还有六、七钱银子的盈余。
黄记豆腐铺的生意一直十分红火,几乎垄断了西津县一半的市场份额。傲来国不产黄豆,主要依赖进口。买黄豆要凭关系,资源十分紧俏。而黄老板的岳父就是首都一家大商行的老仓管,叫胡守仁。他总能搞到物美价廉的黄豆,而且从未阻过手。
由于是靠岳父起的家,黄老板自然对妻子十分客气,忌惮。妻子胡巧,是首都丽春楼的一个粉头,用西方人的话来说,粉头就是性工作者,靠身体挣钱的人。
胡巧每个月回来两次,一是查岗,二是治丈夫的饿痨。胡巧在的那几天,黄老板装得格外可怜,老实,循规蹈矩。胡巧一走,他就原形毕露,放浪形骸,到处打情骂俏,拈花惹草,就像一条发了情的公狗。
苔丝就深受其害,不胜其烦。
本来,苔丝和豆娘吴月、蓝苹睡一间房,女孩子打打闹闹,也有个照应。可黄老板说,要腾出一间房放豆子,借故把吴月和蓝苹都支走了,在苔丝住的房子里放了几十袋豆子。
让人气愤的是:放豆子就放豆子呗,黄老板还偷偷配了一把钥匙,经常三更半夜到苔丝房里搬豆子,借机调戏,揩油,把苔丝逼进了墙角。
有一天晚上,黄老板趁着老婆胡巧刚走,又借口搬豆子,赖在苔丝的房里不走。他厚着脸皮,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进行试探和挑逗,把苔丝恨得咬牙切齿。
苔丝不动声色,装着非常开心的样子,十分殷勤地在炉子上烧开水,泡茶。黄老板非常高兴,两只贼眼直勾勾地盯着苔丝高高隆起的胸部,口沫四溅地说着下流活。
黄老板眉飞色舞,苔丝嗯嗯啊啊地点头附和。水开了,她提着壶去给黄老板泡茶,走到桌子边,踩到散落在地上的黄豆,脚下一滑,一个趔趄,把一壶滚烫、滚烫的开水都泼在黄老板的裤裆里。苔丝马上红着脸从地上爬了起来,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黄老板一声尖叫,鬼打了似的跳了起来,捂着火烧火燎的裤裆,落荒而逃。苔丝后来听说,黄老板的那东西烫坏了,蜕去了一层红皮,擦了一个多月的马油,才稍稍有一点好转。苔丝总算清静了一些日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苔丝设好了的局,水壶、炉子都是道具,包括散落在地上的黄豆,都是苔丝事先就撒好了的。她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黄老板这个傻子上钩了。
阶级敌人是永远不甘心他的失败的。
黄老板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脸上有些挂不住,开始疯狂的反扑和报复。凡是苔丝来领黄豆,就会领到一些变了颜色、籽粒不饱满的次豆。次豆不出豆腐,明摆着就是亏钱,赔本赚吆喝。
可苔丝有的是办法,活人哪会让尿给憋死?她干脆不领黄老板的豆子了,到张秃子那里去进货、出货,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她邀了几个十分要好的豆娘,在外面张罗房子,准备另起炉灶。
黄老板一听傻了眼,心拔凉拔凉的。这几个豆娘都是店子里的销售精英和业务骨干,一古脑都跑去投靠了对手,跟张秃子合作。就等于资敌,等于用杀猪刀剜他身上的肉,拿到手的市场份额,就会被张秃子夺走。
解铃还须系铃人。
黄老板想来想去,只得提了烟酒,请皮毛店的罗老板出面讲和。他一咬牙,在富华楼摆了一桌,给苔丝陪罪,压惊。酒桌上,他拍着胸脯保证:再不给苔丝发烂豆子了,再也不敢对她动手动脚。如有下次,就是畜牲一个!
苔丝摆平了黄老板,就等于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接下来的日子就过得顺风顺水。那份顺,就像是假的,就像做梦一样。好比一个人在打麻将,想什么,就来什么,闭上眼晴乱打一气,也可以听牌、糊牌。用一句艺术一点的话来说,叫沾了仙气,有了天使之手。
在西津县城和下设乡镇,苔丝和几位要好的豆娘联手,设了十几个豆腐销售摊点,将触角向基层延伸,并成立了一个豆腐销售、加工联合体,自负盈亏,几位股东各占了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生意滚雪球似地越做越大,银子滚滚而来。
联合体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进货渠道,统一价格,统一品种。苔丝购置了四辆马车,配备了专人,将统一生产的豆干、豆筋、豆腐脑、水豆腐等十几个类型的豆制品,在清晨配送至各个销售点,再下发到各个摊位。
自从企业实行直销以来,规模越来越大,苔丝牢牢控制了几大经营要素。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减少了流通环节,节约了生产成本,效益也跟着水涨船高。不愧是巨商之后,苔丝天生就有生意人的头脑。那种精明和机智,仿佛来自血液和遗传,是长在骨子里的。
黄老板乐得眉开眼笑,与苔丝合作,实现了互利双赢,他是最大的金主,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联合体的黄豆都是由他提供的。豆干之类的所有豆制品,都在他的作坊里统一生产。虽说利润由大家共有,可规模上去了,市场份额大了,他分得的也不少,比之前涨了两倍多,一个月差不多二千两银子。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很多年以前,黄老板是东关市场一个杀羊卖肉的小屠户,干的是刀口舔血的勾当,一个月下来,挣个四、五两银子,就已经哈哈笑了。银子少禁不住花,每年都是布挨布,皮挨肉。直到后来,他娶了现在的妻子胡巧,才在老丈人的帮衬下开了家豆腐店,日子才渐渐上也有了点起色。
妻子胡巧是黄老板在丽春楼买春时认识的。丽春楼是一家妓寮,规模不小,莺莺燕燕也很多。黄老板之所以一眼就看上了胡巧,是因为她说一口地道的西津话,人也长得秀气。一来二去,俩个人就熟了,再加上黄老板能哄会骗,胡巧很快就从了良,终于有了归宿。
按理说,胡巧从良之后,应该安份守己的过日子,再加上黄老板已在老丈人的帮衬下,开了家规模不小的豆腐店,过日子绰绰有余。可胡巧做妓有瘾,跟黄老板处久了,已经厌倦,又跑到丽春楼重操了旧业。长这么大,黄老板听说过喝酒上瘾、打牌上瘾、抽烟上瘾的,没听说做**上瘾的。而现实生活中偏偏就有。这个世界真是有些千奇百怪。
黄老板气疯了,开始疯狂地报复。可他在生意上又离不开妻子,离不开自己的老丈人胡守仁,又不得不有所顾忌,有所收敛。渐渐地,他患上了性格分裂症。妻子在,他是一个人;妻子不在,他又是另外一个人。
人的存在,其实,就是一个矛盾。一个永远也无法统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说,人的一辈子都生活在矛盾之中。
在这个世界上,黄老板最佩服的就是刘小梅。虽然,他曾经骚扰、伤害过她,刘小梅也反过来给了他一些教训。从表面上看,刘小梅漂漂亮亮,文文静静,跟一般的女孩子没什么区别。可她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什么样的场面她都能够控制,从容,淡定,处变不惊,就跟神话、戏剧里的那些女皇一样,雍容华贵,气度不凡。
特别是做生意、经商,刘小梅的眼睛就像有毒,能洞穿一切,看清实质,找出问题的根本和症结。不得不说的是,成立联合体,统一进货渠道,统一产品价格等等一切,都是苔丝的主意,他不过是个幕后支持者而已。他有些暗自庆幸,选择跟刘小梅合作,是他这辈子最明智的选择,一笔空前绝后、最伟大的生意。
市场是残酷的。
优胜劣汰,是丛林法则,也是自然规律。有人笑,就有人哭;有人赢,就有人输。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张秃子就倒了大霉。他的生意被联合体挤垮,市场份额也被对手一点点地侵占,蚕食。规模越做越小,生意越来越差,因为一连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员工纷纷跳槽。
张秃子唉声叹气,连死了的心都有。为了东山再起,他决定定个日子,把手上的资产全部拍卖,清空。
拍卖会在一家私塾里举行,来看热闹的人很多,真正出手买的人却很少。有人趁机落井下石,出的价钱还不够总资产的一个零头。很明显,有人想捡漏子,占便宜。按照张秃子的估计,总资产价值一千二百两银子,打点折,一千两也可以成交。可会上,买家少的只出了五十两,多的也只有一百八十两,明显的是墙倒众人推。
张秃子欲哭无泪。
拍卖会的下半场,来了一个神秘的买家,戴着墨镜和宽檐帽,看不清脸,也不知是男是女。来人十分阔绰,一开口就叫了八百两纹银,把场上的买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张秃子喜出望外,趁机讨价还价,双方都稍微让了一点点,最终以一千两银子成交。
签好合同,兑了银子,交割完财产和账册,张秃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紧紧地握住了神秘买家的手,激动地摇啊摇。渐渐地,他感觉出对方的手温柔,细腻,有些异样,不像是一个男人的手,不由得疑窦丛生。他松开手,支支吾吾地说:“你是…你是谁?”
“我是刘小梅,你的竞争对手。”苔丝十分爽朗地笑了笑,摘下了墨镜和头上的宽檐帽,露出了满头如瀑的青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