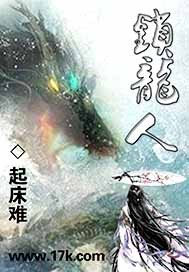马背上的云齐跟且颖谈到了一个让他们都将要遗忘这次别离的话题,这个话题也不得不让我们又一次没有了章法,没有人不想按套路出牌,可惜有的时候却是牌分明就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却没有找到套路,我想这总比套路在手里没有牌要有趣得多。闲话休说,二十年前,我们重回那里。
且春澈,山东济南府人;云中鹤,江南扬州府人。从地理位置上来分析的话,两人是打死也不住到一个屋子里去的。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尽管人究其一生之长来说,很少有人过得生活像是小说,或者散文,一生到了尽头回首去看往往只是杂文,不过是偷偷骂骂别人,偶尔被别人偷偷骂骂自己,可是只拿人生中的某一个或者几个场景来看的话,总会觉得它来得那样机缘巧合,好不热闹。且春澈跟云中鹤两人正是如此,此前曾述,这年适会大考之年,汴京城内游人如织,这游人之中又多以赴考之人居多,那且春澈虽也是府城中人,门庭不大,也算体面,可他进了汴城门,行在御街之上,一时间且还是感到目不暇接,放下那繁华不讲,单说这街道真是足够场面,虽说济南府也是省府所在,看得这御街才算是长了见识,那时街的宽度基本上跟一千年后济南的经十路相差无异,更不用说那汴河之上北门之外的场子地了,济南府的府街上也有这样一块场子地,与此场子比起来那就太相形见绌了,基本上等同于一千年之后的泉城广场和天安门广场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亲眼目睹了这京城阜盛,才知道什么叫世面,什么叫农民。
不知不觉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且春澈心想要尽快找家旅店住下来才是正事,当街一路打听,所有店铺都没有了房位,且春澈心中暗骂:不成想如此繁华之都,竟无容身之店,既这样,那也算不得什么好去处了,不过是人多势众,充个体面而已了。边是如此想,他还是边在做着寻一个客房的最后努力。往前又行了几步,且春澈见到街中有一小巷,很是狭窄,远远地看到里面一个旗子摇摇晃晃,风一吹旗角晃出一个“店”字来,一闪又躺回去,且春澈心想不知那是一个什么“店”,八成应是旅店,不管是什么店了,天将要黑下来,只要写着不是“黑店”先住下来再说,想到这里,且春澈紧走几步赶上前去,走到旗子近前抬头看去果然是“旅店”二字他才放下心来,赶忙问那店家还有没有房间,店小二招呼道:“这位客官,嗯……房……说有就有,说没有它就没有……,有那么一间房……”
且春澈看那小二说半天嘟噜不清楚,有些气恼道:“什么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的。到底有没有?”
小二道:“不是,房是有一间,就是……就是有点蹊跷,一般没有人愿意住。”
“挨着茅房?”且春澈猜测道。
“不是……”小二边说边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有女流氓?”且春澈接着猜。
“不是……”小二如此着摇。
“那是什么,你他娘的快说啊?”且春澈有些崩溃了。
“就是……你有的时候能在里面看到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东西,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小二一口气说出来,长长舒了一口气。
“不想看到的?鬼吗?”且春澈说出来自己都吓坏了,脸都有些白了。
“差不多吧,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反正有的人住着住着就跑了。也有的人住着就没有什么事,一觉睡到大天亮,你还要不要住?”小二漫不经心地问道,看来他本来就没有指望这桩生意。
“我要!”且春澈正要答话,只听背后一个家伙抢先喊了一声,待他回头看时,见是一个白净书生,想来也应是赴考的,且春澈眼睛一瞪说道:“要什么要?我已经要了。”
那书生见状,忙说道:“这街上寻了个遍,再没有什么住处了,想来这房若果真如他所说你恐也未必敢住,我平生最不住鬼怪神灵的,不如我们两个一齐住下,将就一夜便是了,我倒要看看有什么蹊跷?”
且春澈仔细一想,这书生言之有理,也不吃亏,于是笑笑就答应了,两人相互报了姓名算是认识,又各付了一半银子便随着小二往楼上去了,那间房二楼靠楼梯处,按理说如此开阔处不应闹什么鬼才对,一般故事所讲鬼怪之室多在走廊尽头,云中鹤心中暗笑必是这小二故意是讹银子编的瞎话,想来真是好笑。他抬头去看且春澈,也是满面笑意,大约心中也是如此盘算罢。那小二将两人引至门前,交了钥匙便急匆匆地下楼了,并不也多看他们一眼,两人心中暗笑这小二演戏还真是敬业,到现在了还装模作样跟真的似的。两人相互对视了一下,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