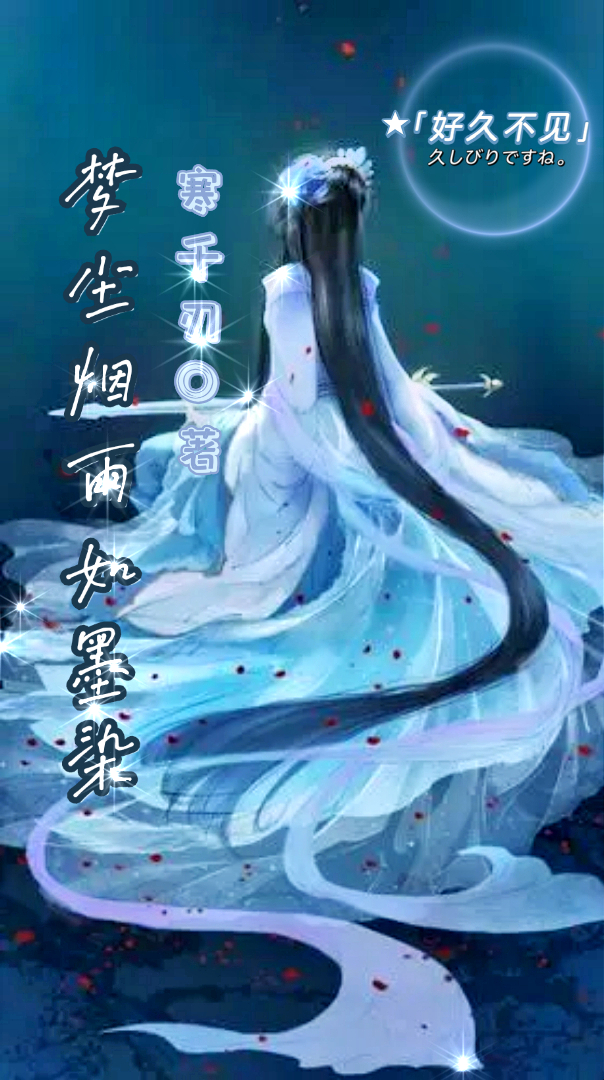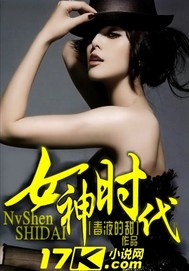五更天,马蹄声碎。
两个人,一匹马,半盏月,云中鹤夫妇都走出门来送且颖,且颖上前一步跪地施礼,泪流满面,云中鹤欠身将其拉起说道:“莫再如此儿女情长,我早便料到你会离此而去,但没想到会这样快,既如此,莫牵连,神京路远,自此北上千里迢迢,我让云齐送至长江岸,过了那长江,你们二人便莫再相互牵念,于谁都无所益处,春澈兄走时曾将你托付与我,如今你北去本是孝悌之事,我不便横阻,只是如今江湖险恶,天下混乱,你此去凶多吉少,如主意已定,那就快些上马去吧。”说罢云中鹤挥一挥手面露微笑。
且颖又向那夫妇拜了几拜方才赶快转身同云齐上马而去。云齐勒紧缰绳双臂将坐在前面的且颖抱住,大呵一声“驾”,那马撒开四蹄飞也似地跑开了。
说来这马也颇有来历,本来云家并无此马,虽原亦有几匹马,但都已暮年垂老,一如一起垂老下去的管家原离,云中鹤生性仁慈便将这些老家伙一并养着。那是前年刚入秋,一日云家三口晨练归来,途经那竹林时见一马闲游至此,此马低着头,四蹄微曲,似乎身体十分虚弱,见到云家三口并不惧怕,倒是颇为大胆地靠上前来,云中鹤见状颇是惊奇,近前一看此马通体赤红,毛发光亮,体格健壮无比,只是此马精神萎迷,且马尾靠腿处有一外伤,近看似为人所刺,不知何人之马伤游至此,于是只好先养了只等人来认领。后不过半月且颖与管家原离寻至竹园,且颖住下次日游玩至后院,见得棚中此马顿时抱马痛哭,云中鹤忙问其因何故啼哭?且颖泣曰:此马为家父之马,十余日前,家父对其母子两人说:“今朝中有人陷我且家于水火之中,恐无力回天多有不测,想我且春澈平生为人义气,做事磊落,一生死有何惧,只是难为了你们母女二人,我此生少舛多坦,并无太多艰辛之事,若说遗憾,倒确有一憾,我明日即驾马南下以了此憾事,三日当归你们母女二人在家静候,凡事我早已与管家原离交待清楚,三日后我若不归必遇不测,你们自不必等我,一切听从原离安排。”说毕此言家父便驰马而去,想来应是来寻云叔叔,只是不知家父所言憾事为何事?
“啊”,当时云中鹤大吃一惊,叹道:“原来春澈兄曾至园外,距我仅一步之遥,想来必是春澈兄在路上发现有人追踪暗算怕我受牵连,便下马用剑刺了马尾自己下马引开耳目,自己被人或擒或害。难怪当时此马神情暗淡,想来其必也有所察觉春澈兄之凶难这事了。只是春澈兄所谓憾事我并不知晓,也无从猜测。”正所谓无巧不成书,自此事发,云中鹤郁郁寡欢少有笑颜,常常步至后院马棚,睹马思人,感慨良久。
两人上马之后,一口气跑出凤凰之城,天渐渐亮起来,西边的天空还是阴沉沉的,而身后的天上已经有很好看的云朵。且颖跟云齐说道:“云齐,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不懂,不知道为什么,我从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很熟悉,仿佛经过了几生几世我都在等着你,而今,你就坐在我的背后,而我们却在从一个分开走向另一个分开?”
云齐道:“第一眼?你是这种感觉?”
“嗯。”
“为什么我也是这种感觉,好像是一个旧相识,以前分开了,转过一条街,就在那里又重逢了,刚见到你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仿佛我不在这个天地间了,我到了另一个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不用人把你介绍给我认识,我们一步之遥,却再熟悉不过。只不过,现在我们又要离开了,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人生可能就像是驿客住站,驿馆就在那里,你住进去了,我也住进来,你往西,我往东,然后又是分开,直到来生再次住进同一个驿馆。”云齐哀伤地说着。
“不知道是不是来生,来生可能我们还会住错驿馆”且颖纠正道。
“世上有鬼的,你知道吗?”云齐突然提起这样一个话题。
“可能有吧,如果真的有前生来世的话,我真希望世上有鬼。”且颖在马背上抖了一下,云齐将他抱得更紧了。
“当然有的,家父曾经跟我谈起过这个问题,当然他还提到了你的父亲。”有且颖的印象里,云齐从来没有用如此神秘的语气说过话。
“我的父亲?且春澈吗?”且颖问。
“是的。”云齐在春日凉凉的风气里有些兴奋与激动地说着,“家父说起过,二十年前在与你父亲同住的那天夜里经历了一件灵异怪事,从那以后,他们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可是他们谁都不能忘记,后来你说到令父此生曾有一憾事不得其解来寻家父,想来也应为此事罢。”云齐压低了声调跟且颖贴耳说道。
“啊?”且颖在马背上努力地扭过头来盯着云齐看,仿佛背着身说话看不到表情总不踏实,“到底是什么灵异的怪事?他们遇见鬼了吗?我早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我怎么感到身上冷冷的?”
“你听我慢慢说啊,反正路还远着,我将你一路送至汴京去参加县选,省得天高路远地出了什么差池。关于此事我也是那日父亲才跟我说起的,我这几天也一直心神不宁地思虑此事,并不得要领,本不想跟你说起,生怕日后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会害怕。”云齐看来并不急着讲那灵异之事,且颖着急着又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等不及地说道:“快说啊?到底是什么怪事?他们到底遇上了什么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