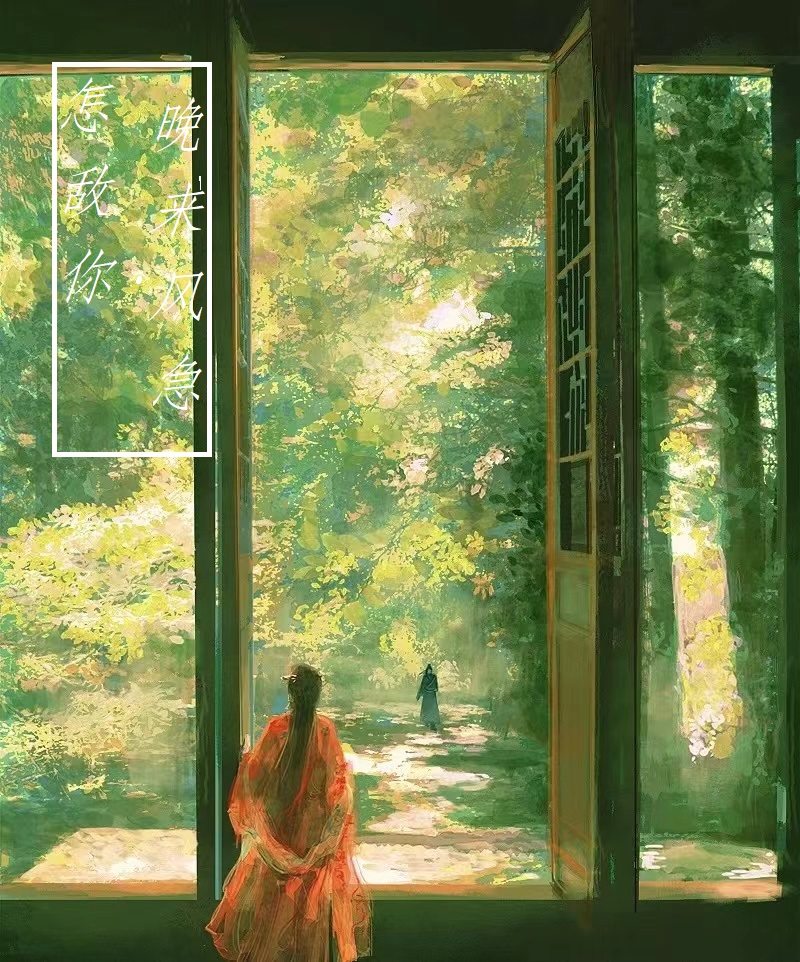脚步声传来。
覃沧月和鄢柳赶忙站好。
一个年过半百却依然容光照人的端庄贵妇人在丫鬟仆妇的簇拥下,款步朝这边走来。
覃沧月赶忙带着鄢柳迎上去蹲身施礼:“奴家覃沧月,拜见老夫人。”
“大胆。”贵妇人旁边的一个仆妇未等老夫人开口便呵斥覃沧月道:“见了老夫人,胆敢不下跪。”
覃沧月一愣。
直起身正待重新下跪拜见,那老夫人冷哼一声道:“不必了。”
覃沧月站在那,跪也不是,不跪也不是,鄢柳在后面小声提醒覃沧月:“礼物,礼物。”
覃沧月转身从鄢柳抱着的一堆礼盒上拿起一件,打开了,呈于老夫人面前,笑道:“奴家为老爷和老夫人选购了几样礼物,请老夫人过目。”
老夫人睨了一眼盒中之物,又将覃沧月上上下下打量一遍,忽然伸手将覃沧月捧在手中的礼物打翻在地,恨声道:“怪不得,果然是,一脸的妖媚之气。阿海他曾经流落外地,差点丢掉性命,就是因为你吧?若不是唐推官偶然遇到,将他捡回来,阿海他有没有命回来都还是未知。他昨儿个着人来通禀说少夫人要回府,我就知道会是你。无媒无证,就胆敢自称少夫人,你这来路不明的狐媚子,也配?。”
“老夫人,您怎么能这么说少夫人呢?大帅他……”鄢柳欲替覃沧月辩解,话没说完便被老夫人身边的仆妇冲过来狠狠打了几巴掌,将鄢柳抱着的礼物也通通打翻在地,叮叮当当摔了一片狼藉。
覃沧月赶忙上前护住鄢柳,跪下求情道:“老夫人息怒,都是我的错,莫怪柳儿。”
覃沧月从小山村失踪的那段日子,聂如海遍寻不着,整日酗酒,疯疯癫癫,如痴如狂,被捡回来送到家,还是整日月儿,月儿的喊着,活像丢了魂儿一样。老夫人看儿子为了一个女子如此的神魂颠倒,简直气的咬碎一口银牙。如今这女子无媒无证,却以聂家独子夫人的身份大摇大摆前来拜见,她岂能容忍。
“你也知道是你的错吗?”老夫人恨恨道:“既然你都走了,阿海也好不容易振作起来,好好干一番事业了,你又回来干什么?还不是想攀附权贵?”
“我……”覃沧月低眸,无言以对。
老夫人揉着额角:“看到你我就气的头疼。桂阿嬷,让她们去那边跪着,别碍我的眼。”
桂阿嬷答应一声,命四个丫鬟仆妇分别押着覃沧月和鄢柳,丢到一处卵石小径上,趾高气扬道:“识趣的话就好好跪着,说不定老夫人气消了,还能放你一马,不然的话,哼,咱们家少爷,可是远近闻名的孝子,得罪了老夫人,以后少爷那,有你好受的。”
“是。”覃沧月懦懦点头,低声应是。
“哼!”桂阿嬷见她不反抗,白了她几眼,转身服侍老夫人进暖厅里去了。
“这……这怎么办啊?姑娘?”鄢柳颤声问。
“对不起柳儿,都是我连累你了。”覃沧月抚着她被打出掌印的双颊:“我确实害阿海他……总之,这是我该受的,我欠他的。”
“姑娘,可是,可是天这么冷,您身子弱,若有个好歹,大帅那怎么交代?”鄢柳四下看看,低声道:“现在没人,我去帮您把大氅拿来吧?”
覃沧月也确实冷到直哆嗦,只好点头:“那你小心点。”
鄢柳点头,轻手轻脚离开。
她拉开聂府大门闪身出去,大门就在后面被不知从哪跑出来的桂阿嬷关死。鄢柳吓得赶紧敲门,桂阿嬷在门后阴阳怪气道:“不想你家主子受苦,就乖乖侯着,等老夫人气消了,还能放你家主子一马。”
鄢柳闻言也不敢闹腾了。
守在门口的赫连将军问明鄢柳情况,不敢耽搁,赶忙命人去寻大帅。
天阴沉沉的,乌云好像压到了房顶。
冰凉的雨丝夹杂着雪花落下来。
覃沧月孤冷的跪在卵石地面上,垂眸忏悔,她施加给聂如海的,远比她想象中还要严重,今天跪在这,向他爱子心切的母亲赔罪,也是她应该受的。
聂如海从御书房出来,远远看到赫连博派去的近卫,心头便掠过一丝不详的预感。
他急匆匆辞别了皇帝楚天雄,奔下台阶,一问之下,马上倒抽一口凉气:“快,快,回府。”
他怎么忘了,当初他被捡回来送回家那段时日,他整日酗酒,疯疯癫癫,哭哭闹闹,母亲因恨铁不成钢打过他,罚过他,也在他面前哭着跪下求过他,后来他才重新振作,开始匡扶义兄起事……
他怎么能让月儿独自去面对母亲,母亲一定是早就对月儿恨之入骨了。
他却只记得母亲急切的想要一个儿媳妇,想要早日抱孙子,他以为,母亲看到儿媳妇回来,只会高兴的。
他太疏忽,太大意了。
天上还飘飘零零下着雨雪,他骑在马上,寒风吹打的他脸颊生疼。
月儿,月儿,母亲,母亲,他心里一遍遍翻江倒海。
这可如何是好?
两个时辰后,他踹门而入。
守在聂府门口的近卫们和鄢柳一起跟在后面。
“月儿。”聂如海扑过去将浑身湿透,嘴唇青紫,脸色暗沉,已经冻成冰人的覃沧月拽起揽进怀中,心疼不已,颤声自责:“月儿,月儿,都怪我,都怪我疏忽……”
“大帅,大帅,您身上湿,姑娘怕冷。”鄢柳在一旁拿着覃沧月的狐裘大氅提醒聂如海。
后面跟着一群丫鬟仆妇撑着伞的聂老夫人也闻声赶来。
聂如海用狐裘大氅将站立不稳的覃沧月裹了,交到鄢柳手中,对着母亲质问:“母亲,您为何如此为难月儿?”
“放肆。”聂老夫人本来念子心切,熟料儿子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质问,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狐媚子而质问她,聂老夫人勃然大怒:“我作为长辈,还无权责罚你一个姬妾吗?”
“她不是姬妾,她是我视之如命的女人。”聂如海情绪激动,极力遏制自己脾气,沉声解释道。
“阿海,你能不能清醒一点。”老夫人看宝贝儿子为了一个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失态,也怒气翻涌:“她当初是如何伤你的,你都忘了吗?现在你出息了,她又来攀附你,这样的女子,哪一点值得你如此相待?不过一个趋炎附势的狐媚子,就你傻,被她骗得团团转。”
“母亲,您要我怎么跟您说您才能相信,她没有骗过我,更没有趋炎附势。”聂如海指着厅前台阶上摔得一片狼藉的礼物道:“那些礼物,都是她用自己的钱特意为您和爹挑选的。”
“她自己的钱,她的钱还不是从你这来的?”聂老夫人不屑一顾道:“若不是看在她还懂几分礼数的份上,为娘早命人乱棍打死她了。就凭她能撺掇你对为娘如此无礼,她就罪该当罚,桂阿嬷,去,给我掌嘴那个狐媚子。”
“是。”桂阿嬷答应一声,就往覃沧月面前冲。
“你敢!”聂如海充满杀气的瞪眼,对着那桂阿嬷一声暴喝,吓得桂阿嬷一个哆嗦停在原地,求助的望向老夫人。
聂如海向着母亲扑通一声跪下:“母亲。也许,您还不知道月儿在儿子心目中的重要性,儿子这就告诉您。”
他从袖中抽出匕首,看着母亲痛声道:“月儿她流一滴泪,儿子愿偿她十觞血。”
“你说什么?”聂老夫人暴怒:“你昏了头了是不是?胡说八道什么?你拿刀干什么,你还想为了这个狐媚子杀了为娘不成?”
“儿子不敢对母亲造次。”聂如海垂眸,一刀捅进自己心口。
“啊!”聂老夫人一声惨叫:“你疯了,你疯了吗?来人,来人,拉住他,拉住他!快拉住他……”
所有人在聂如海充满杀气的目光下,都不敢上前。
又一刀,再一刀,虽不伤脏腑经脉,却刀刀喷血,覃沧月挣扎着想阻止,可是腿在卵石地面上跪太久,根本走不动,人在寒风冻雨中待太久,声音也发不出来,眼睁睁看着聂如海一刀又一刀捅向自己心口,血染满襟,她在鄢柳搀扶下步步向前,急切之下扑倒在地。
老夫人早已扑上去抢夺聂如海手中匕首,可她哪里抢得过,只能急怒交加,又哭又喊,还狠扇了聂如海几个巴掌。
“大帅,大帅……”鄢柳在一旁哭喊:“姑娘,姑娘她流血了,大帅……”鄢柳担心若大帅有个好歹,姑娘定会更加遭殃,于是趁着覃沧月摔倒流血,赶忙大声呼喊,也是希望可以阻止聂如海自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