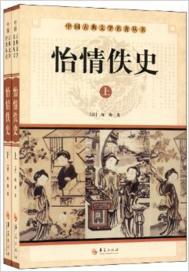因为事出突然,太过震惊,她和韩山羽还保持半跪着前后相拥**的姿势没有改变。
“奸夫*淫*妇!”聂如海冷声啐道:“杀!”
一声令下,提刀侍卫们蜂拥而上,数十把钢刀朝着他俩一齐落下。
“不要!”未待覃沧月反应,韩山羽惊呼一声,用血肉之躯紧紧将怀里覃沧月护住……
“小羽!……”覃沧月从睡梦中惊醒猛然弹起来。
“怎么了月儿?”一旁聂如海赶忙起身去揽她。
她闻言侧目,看到聂如海的刹那,好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惊惧不已的大喊一声:“啊!”猝然推开聂如海,摔跌下床,然后光着脚连滚带爬的跑出房间,穿着单薄中衣的她跌倒在积了厚厚一层白雪的院中。
突然的寒冷使她找回了一丝理智,反应过来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一时间,对小羽的担忧,对聂如海的愧疚齐齐涌上心头,她不由得抱紧双膝低低哭了起来。
紧跟着她同样赤脚出来的聂如海用随手拎出来的狐皮氅轻轻将她裹了,抱起来走进卧室,放在床上,轻轻拍着她后背,静静守着她,什么也没问。
她思念小羽,担心小羽,又对聂如海愧疚,清醒过来的她除了哭,就只能哭,她什么也不能说,也不知道该向谁说,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她除了恨自己,嫌弃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她蜷成一团哭肿了双眼,才发现聂如海穿着单薄的中衣还赤脚站在床边冰冷的地板上,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在安抚她,她更是愧疚自责,心如刀割。
她往里挪了挪,轻声对聂如海道:“我没事,你快上来睡吧。”
聂如海在床边坐下,伸手将她揽入怀中,在她耳边轻声低语:“月儿,没事的,没事的,我会一直都在。”
“我知道,我知道……”覃沧月收不住哽咽,眼泪簌簌下落:“对不起,对不起……”
“你别为难自己,月儿,我懂的,我都懂的,我不会怪你的。”聂如海将蜷成一团的她抱起来放在腿上,拉过棉被捂严实了,像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轻轻拍着她摇晃:“睡吧月儿,睡吧,别怕,别怕,有我在……”
天快亮时,聂如海轻轻将覃沧月放下,帮她盖好棉被,自己披衣悄悄走了出去。
他走后,覃沧月才再次迷迷糊糊睡着。
覃沧月醒来,进来伺候她洗漱的鄢柳几次欲言又止。
“怎么了柳儿?”覃沧月看出她有话要说。
“大帅他今天天不亮就出去了,脸黑的吓死人,姑娘,你们吵架了吗?”自从住进这个院落,聂如海顶多在另外一间房里处理公事,还从来没出过这个院落。
现在外面还下着雪,冰天雪地。
他能去哪?
覃沧月担心又心虚。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去铺子里问过了,大帅他带了两个人,去了山里。”鄢柳声音低低道:“姑娘,你们……”
闻言,覃沧月坐不住了,她奔出院落,穿过茶馆内院外厅,跑到街道上。
茫茫雪海中,街道上依旧人来人往。路面上的积雪都被铲到了路边,有些直接被车马碾踏成了泥泞。
鄢柳和负责看守茶馆的军士追出来。
覃沧月抓住那名扮作茶馆老板娘的军士焦急的问:“他往哪个方向去了?有没有说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那扮作茶馆老板娘的军士一脸恐惧又无辜的摇头:“大,大,大……他看起来很不高兴,小的哪敢多问啊!只知道他们往那边去了。”
覃沧月朝他指的方向看了看,是通往御笔峰的方向。
她发疯一样朝御笔峰方向奔去,鄢柳紧跟在她后面:“姑娘,姑娘,您慢点,路滑,小心……”
那扮作茶馆老板娘的军士赶忙回去叫来六名护卫,一起追在覃沧月后面:“夫人,夫人,您要去哪,小的们找轿子送您去啊!夫人……快,快去禀告大帅。”后一句是吩咐其中一名军士的。那军士领命,飞快的超过覃沧月,往御笔峰方向去了。
覃沧月茫然无措的奔了一阵,一个趔趄滑倒在地,坐在地上默默哭了起来,她这是要干什么,要去哪?找到他又能跟他说些什么?
路上行人纷纷侧目。
鄢柳过来扶她,她一身泥水的站起身,又失魂落魄的开始往回走。
她觉得心口有刀子在剜,一阵强过一阵的,疼的她几乎喘不过气,可她又觉得自己活该承受这种疼,她恨这么无力改变一切的自己,恨贪婪自私的自己。她恨无法停止思念,担心小羽的自己,她也恨一次次伤害聂如海的自己。
难两全,两难全,她只有一个人,一颗心,要怎么分才能都不受到伤害?
她泪雨汩汩,完全不在意路人异样的目光。
鄢柳引着失魂落魄的她走进茶馆,走入内院,走入浴桶。
她静静坐在热水里默默流泪。
鄢柳不知发生了什么,也不敢多问,只轻轻帮她梳洗着长发。
她一天水米未进。
心如刀绞。
泪如泉涌。
躺在床上,稀里糊涂,发着高烧。
随行杜军医被鄢柳叫进来看过了,开了药,在厨房熬了,灌她喝了几次。
鄢柳静静陪在她床前寸步不敢离开。
她总觉得,大帅若再不回来,她家姑娘就要一命呜呼了。
覃沧月当街跌倒,返回来前,已经有侍卫前去寻他们大帅禀报了,后来覃沧月起烧,鄢柳又两三次让侍卫去回禀大帅,直到现在,接近三更,派出去的侍卫有五六轮了,可无论大帅还是侍卫,人影都没回来一个。
夜深了,覃沧月意识更加模糊,口齿含糊的有一句没一句在说着什么,好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聊天。
鄢柳摸了摸她烫热的额头,赶忙喊军医进来。
军医查看后,摇头道:“夫人这是高烧不退,魇住了。”
“怎么办啊?军医?”鄢柳带着哭腔,眼泪汪汪祈求的望着一脸沉重的杜军医。
杜军医思索良久,心一横:“再给夫人灌一次药吧?”
鄢柳赶忙摆手:“不行不行,不能再灌了,都灌了七次了。”
躺在床上的覃沧月一会儿笑,柔声道:“小羽,你回来了?”
一会儿歇斯底里的喊:“别杀他,别杀他,求你别杀他……”
一会儿哭,满腹怨气:“你去哪了?去哪了,怎么都不告诉我……呜呜……”
“小羽,我好想你,小羽……”
……
“小羽是谁?”杜军医疑惑的看向鄢柳。
鄢柳摇头:“不知道。”
杜军医凝眉,沉思……恍然……
然后闭嘴不吭声了。
聂如海从门外走进来,来回扫视着鄢柳和杜军医,冷声问:“发生什么事了?”
“夫人她……”杜军医欲言又止。
“大帅您可回来了。”鄢柳泪汪汪的看着聂如海,又看向覃沧月:“姑娘她病的厉害,怎么办啊大帅!”
尚带着一身冰雪寒气的聂如海走到床边蹲下,小心翼翼探了昏睡的她烫热的额头,生怕自己的手凉到她,去抓她手的大手顿在半空,又迟疑放下,身体前倾,伏在她耳边轻轻呼唤道:“月儿,月儿……”
昏迷中的覃沧月一把抓住他衣领:“小羽,小羽,你快走,快走……”
聂如海轻轻拍着她抓住他衣领的手背,沉声对鄢柳道:“吩咐下去,去把镇子里所有大夫都找来。”
鄢柳应一声,转身去了。
杜军医惭愧道:“属下无能。”
“不怪你。”聂如海依旧脉脉含情看着人事不省犹自胡言乱语的覃沧月:“是这夜里的雾气有古怪。”
“雾气?”杜军医探寻的看向聂如海。
聂如海点头:“就是雾气。自从来了这儿,夫人总睡不安稳,发噩梦,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因为前几天的事情思虑过重引起的,没当回事。今日我去山上探查,发现这牡丹镇的整体布局就是一种上古阵法,这雾气于傍晚开始起,起于牡丹溪附近。至于具体原因,还需详查。”他心里已经有些眉目,只是还不想妄下定论。这种上古阵法,并无杀伤力,不是兵家所用,他只在典籍中见过,通常是用于墓葬守卫。也就是说,这座牡丹镇的建筑,是给守墓人住的。
若真是这样,那这座镇子东侧,也就是牡丹溪所在之处地底,必然有一座规模可观的古墓。结合天下术士奇人趋之若鹜的牡丹溪水底偶尔会出现的姹女银珠来看,那雾气,很可能就是地下银河和某种防腐药物挥发所散出的毒障。因为年深日久,毒气并不重,但防腐药物里有不少致幻成分,体质稍弱一点的人,就容易被其影响,放大心中喜悦或恐惧,引来幻象。
这也是牡丹镇能吸引大批不速之客的原因之一。所谓的圣水照心,就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