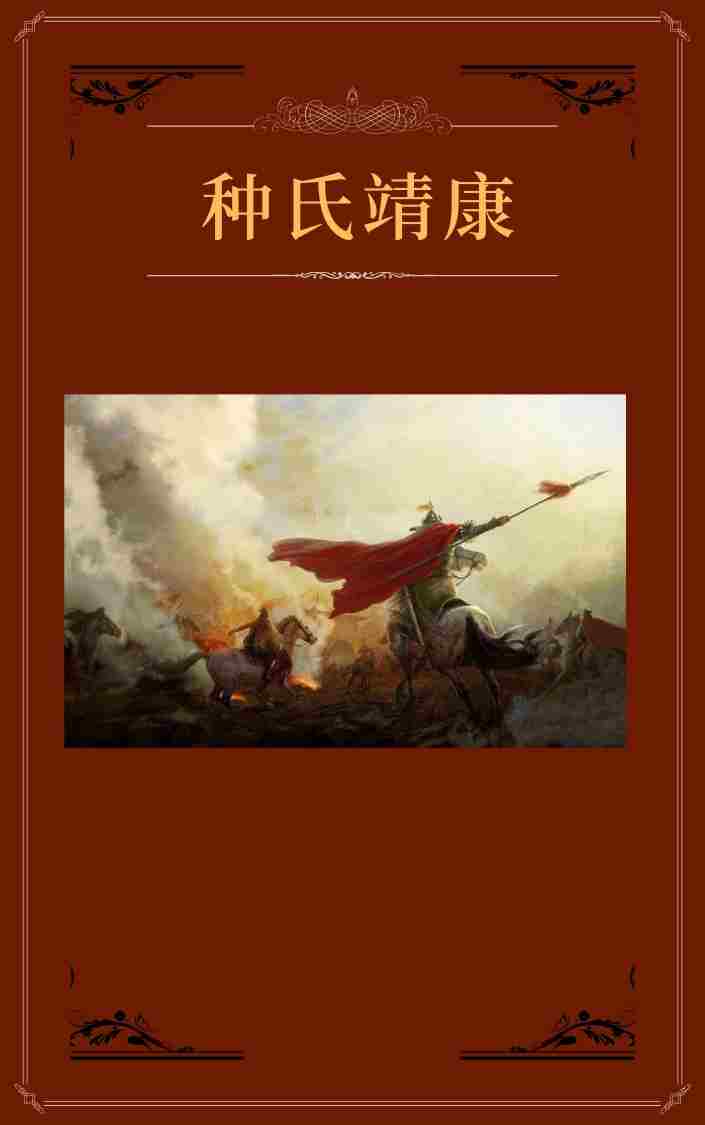他低头抵住覃沧月青白沁凉的额角,眼泪滴落在她的面颊上。为了她,他所有的坚持,所有的底线,所有的自尊,一次次被打破,摔碎,踩在脚底下,碾成灰,她却一次次以这么决绝的方式对待他,他心中有恨,有怨,有不甘,却又对她束手无策,他只能一次次选择臣服,选择接纳,选择忍受。
他究竟做错什么了?
难道他付出一切,都换不来她一个真心的回眸吗?
“月儿,月儿,你别这样好吗?别这样,你睁开眼看看我好不好,看看我。”聂如海满腹心事想要对覃沧月说,可她只是冷冰冰的闭着眼,拒他于千里之外。
“月儿,月儿……”他哽咽:“我答应你,只要你醒来我就放了你的小羽,只要你醒来,我就放你自由,我再也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了,月儿……”
他被泪水哽住,发不出声音,他恨这样懦弱妥协的自己,他恨这样没有尊严委曲求全的自己。
对她而言,一句轻飘飘的自由,对于他却意味着永远的失去,从此海角天涯,山高水阔,她都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他放弃的,是他的魂牵梦系,心驰神往,是他的心心念念,辗转反侧,是他的望断天涯,一日三秋,是他的红尘情梦,求之不得,是他的人间一世,深恋一生。
他说出这些话,已经是把自己逼到无路可退,放下所有尊严和不甘,卑微到尘埃里,燃烧着灵魂献祭,做出最后的祈求。
战场风云瞬息万变,自古以来没有必胜的战役,没有不倒的将军。他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会怎样,不知道她是不是偶尔也会为自己担心,他印象中,她总是云淡风轻,自然随和,笑对苦难,无惧生死,遇事总会先为别人考虑,是什么,将一个这样心无挂碍,本应无欲则刚的人逼到心力交瘁,万念俱灰?
我将丹心向明月。
明月普照全天下。
是明月的错吗?
她本高洁如明月,他偏偏想她只做自己一个人的夜明珠,是他错吗?
爱情本没有对错,前提是双方自愿,不伤害他人。
他或许真不应该拿另外一个人的性命胁迫她的。
越是这样,善良如她,又怎能在无辜之人受到伤害的前提下,直面自己的感情。
她明明羸弱,却能从尸堆上站起来,在鬼哭狼嚎,血肉狰狞的伤兵中*日夜穿梭奔忙,她胸怀苍生,却从来就没有她自己。
他觉得他懂她,他又觉得他根本就没懂过她。
乱世女子,如飘萍,如藤蔓,要么随波逐流,听天由命,要么攀附大树,罅隙里寻找生机,这既是命运之殇,也是时代之殇,是天定的选择。
她不同,说她顽强,她可以如野草般野火烧不尽,她既拒绝随波逐流,又不思寻找大树攀附。以她姿容,若想攀附,世间又有几个枭雄可以拒绝?说她脆弱,她又如翠玉般易碎易折。她总在自己和朋友之间权衡,总是选择先舍弃自己,真不知道该说她傻还是无私。
他理着她鬓发,吻着她额头,鼻尖,唇角,心头千般不舍,万般无奈,她从来没有属于过他,她将来也不会属于任何人,她只属于她自己,这个昏暗世间的唯一一抹亮色,她有她特有的姿态,要么绽放的灿烂,要么陨灭的决绝,逼她做出任何的妥协,都是对这世间仅存不多的美好事物的亵渎。
他将她紧紧搂在怀中,舍不得撒手。
也许,下一刻,他就要亲手送她离开自己的世界,从此陌路天涯。
他无比珍惜还能将她拥在怀中的不多的时光。
她体温一直在降。脉息越来越微弱。
他将她手心扣进自己手心,心里一遍遍祈祷,一遍遍发誓:“月儿,你醒来,我保证不再碍你的眼,我保证从你的世界滚的悄无声息,死的无踪无迹……”
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可以将她拥在怀里,****。
即使若她醒来会嫌弃,会抗拒,他也顾不得了。错过今日,他将一个人永生永世守着对她的思念,度日如年。
他*着她,好像要把自己掌心的热度渡化到她身体里去。
至少,这一刻,她还是他的。
他犹豫着,迟疑着,他怕她会忽然睁开眼,鄙视的,厌弃的看他。
脑中又有一个声音不停在鼓励他,最后一次机会了,错过了,你将后悔一辈子。
他鬼使神差****
他脑中最后一丝理智也被淹没的无影无踪。
......
,他要记住这一刻,永远记住。
他只想给她最舒适的体验,虽然,可能她并不会记得今天他为她做了些什么。
他从背后将她揽在怀里,起伏的胸口贴紧她光滑的后背,随着马车的颠簸轻轻晃动,感觉她逐渐上升的体温。
虻津,襄南军属地,一个尚未被战火过多洗礼的小城。
安静的小院里架着两个红泥小火炉,上面的药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浓郁的药味穿过回廊,穿过花架,从雕花窗棂里传进覃沧月的鼻子,覃沧月打了个大大的喷嚏,慢慢坐起身来。
被她喷嚏吵醒的还有躺在窗棂下躺椅上打盹的黑衣美男子,韩山羽。
韩山羽笑着走过来,摸了摸覃沧月额头:“太好了,月儿,你退烧了。你还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覃沧月没有回答,只静静看着他。
韩山羽掀开覃沧月身上薄被一角,露出她的双足,解开她双足上的绷带,拿掉药包笑道:“看来这个足底用药也是可以管用的。”
覃沧月仍旧一语不发,伸手捉住他的手,拉他到自己身边坐下,直接去扯他腰带。
韩山羽不着痕迹的转身躲开:“药应该差不多好了,我去看看。”
覃沧月一把拉住他,终于哽咽出声:“给我看看你的伤。”
韩山羽笑道:“怎么刚醒又哭。我没事,都好了。”
覃沧月摇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欠缺考虑,害了你,害你受那么多苦。”
韩山羽又坐回床边,替覃沧月抹着眼泪安慰道:“我没事,真的没事,都已经好了。现在你也自由了,等你身体养好了,我们就可以去找地方隐居了。”
“自由?隐居?”覃沧月不解的看着韩山羽。
“是啊!”韩山羽眼中也有泪光闪过:“聂大帅他……”
韩山羽正待回答,瞥眼看到窗外有个熟悉的身影正朝这边看,那人见韩山羽发现了他,索性大方走进来。是端着两碗药汤的黄军医。
“来,你俩都先把药喝了,聊天有的是时间。”黄军医不由分说把托盘伸到两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