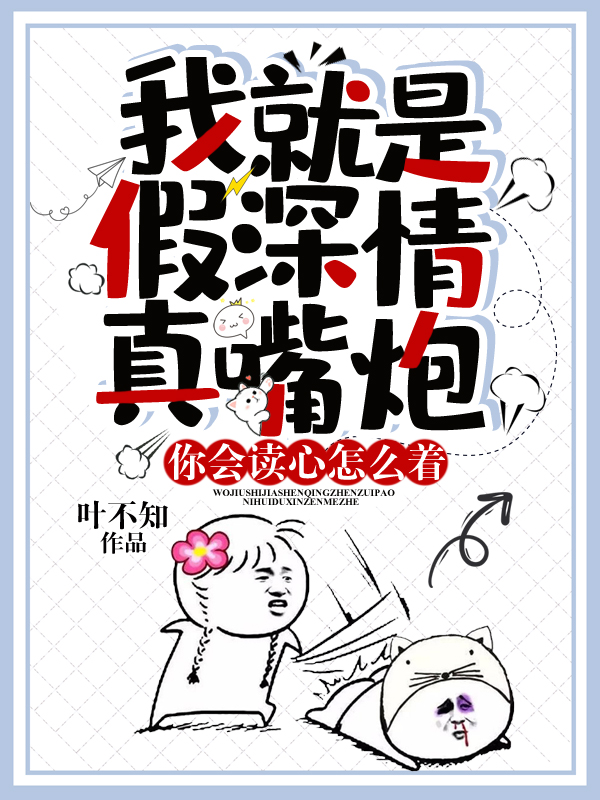自从看出来聂如海的异样,覃沧月便有意识的和他保持距离。好在她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生活勉强可以自理了。
聂如海似乎看出覃沧月的冷淡,以为覃沧月不适应他那么黏腻,便也收敛了些。
转眼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聂如海站在租住的院落不远处一株开满淡黄色小花儿的巨树下发呆。
覃沧月走到他身后,他马上察觉转过身来笑道:“月儿。”
“你有心事?”覃沧月开门见山,他以前曾多次提过要回隆中找他大哥,这一耽误就是好几个月,他再也没有提起,覃沧月知道他是因为自己的伤。现在自己伤好了,不能一直拖着他吧。
“没有啊!”聂如海过来捉住覃沧月的手:“手怎么这么凉,你是不是受寒了?”说着就将手探上覃沧月额头,覃沧月赶忙避开,顺便不着痕迹的假装整理鬓发,抽出手:“以前多次听你提起要回隆中,我知道,后来是被我绊住了,现在我伤都好了,天气也暖了,……”
“跟我回隆中吧!”聂如海再一次捉住覃沧月的手,满眼真诚恳切,也有祈求:“去隆中,我们成亲,好不好?好不好?”
“成亲?”覃沧月从没想过,也并不打算想。父皇母妃的例子摆在眼前,在男子眼中,女子是什么?装饰?玩物?甚至还不如。男子自己三宫六院,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男子睡了千百女人,他不会责怪自己半句,他不会觉得自己有半点不妥,而女子呢?只能独守空房,一旦有了情深之人,就得被赐死,孩子就得被丢入冷宫里不闻不问。
在男子眼中,女子轻贱如斯。
那么女子又为什么要那么想不开,非得找个男子成亲?
我覃沧月这一世,只想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活,绝不轻贱到甘愿去做任何一个男人的附属品,玩物。
何况,覃沧月曾听聂如海说起,他虽身无功名,但其母出自隆中大儒世家的云家,父亲亦是书香世家聂氏一族的单传独苗。到了他这里仍是一脉单传。他虽出身书香门第,儒门世家,却不喜文墨独喜武功兵法,现在跟在枬阳郡守,也就是他口中的大哥楚天雄身边做个闲散的统军督头。
覃沧月抽出被聂如海紧紧握在烫热掌心的素手,歉然道:“聂公子还不知道吧!我是牦苏人,我们族里没有成亲的规矩。”
“你,你说什么?”聂如海不可置信的望着她:“你怎么可能是牦苏人,从第一次见到你,你就是中原人的装扮,而且,举手投足,你并无异族习性。”
牦苏人可以一妻多夫,聂如海怎么会不知道。
他后退了一步,又一步,摇头:“不,不是的,你骗我的。”
“我没有骗你。”覃沧月肯定道。
“不,你骗我的,你骗我的。”聂如海眼泪喷涌而出:“你说过,你是清溪城肃王姨族岑家庶出小姐,怎么可能是牦苏人?你骗我的对不对,求你不要骗我好不好?求你。”
覃沧月歉然的看着泪如雨下的聂如海,知道他之所以这样难以接受,是因为他和父皇一样,都受中原礼教影响极深,觉得女人就应该是男人的私有财物,而男人就该是女人的主宰,男人三妻四妾就很正常,理所当然,女人多夫就是淫&贱该死,罪无可恕。
他越是伤心,她越是坚定。
在这个中原天下,女人,连追求平等的资格都没有,真是无语问苍天,这是为什么?
覃沧月转身走向不远处的院落。
她不想面对聂如海的眼泪。
聂如海无微不至照顾了她几个月,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她是感激他的。
但不代表就要把自己送给他当报酬。
那是对自己的侮辱,也是对聂如海的亵渎。
聂如海在巨树下站着,呆呆的,一动不动,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令月儿如此厌烦,不惜撒谎来拒绝他,月儿自从看出他对她的心思,就一直有意无意的疏远他,躲避他,他认定了月儿是为了拒绝他才编出自己是牦苏人的谎话,想让他知难而退。
泪水悄悄的流,月亮爬上树梢,冷冷照着他,茕影寥落,可悲可笑。
月儿明明是心里有他的不是吗?月儿是喜欢他的不是吗?为什么现在又对他如此冷淡?
聂如海想不通,在悬崖上,她完全可以看着他自刎的,她却先一步主动跳下了悬崖。她昏迷中第一次醒来,就拉着他的脸让他吻她,当时他以为是她劫后余生再次见到心爱之人的情不自禁。当时他也是情不自禁的,他在她睡着后又吻了她好久,动心动情,入肝入肺,甚至失控脏了里衣。他当时吻着她,流着泪,第一次知道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滋味,第一次知道,情与欲是什么感觉,第一次,为一个女子日夜忧心,喜极而泣。在来小山村的路上,她被颠簸的疼极了,他看得出来的,他用嘴巴喂她水,她情不自禁的吮吸,难道都是假的吗?难道不是下意识的情难自控,身不由己?
不,她是爱自己的。聂如海很肯定,岑沧月,他的月儿是爱他的。
那她告诉自己她是牦苏人是何用意?难道不是为了让自己知难而退,而是……而是以退为进?
难道她还有别的心上人,和自己一样的,令她难以割舍,情不自禁的另一个人?
不,不,不可能的。若真有另一个人,那她为何还会只身漂泊?
聂如海思绪飘摇,联想万千,始终找不到一个有力的着陆点。
他很痛苦,很迷茫,很抓狂,他一拳狠狠打在巨树树干上,一声闷响,淡黄的小花被震的纷纷扬扬从枝头飘落,随着晨风起舞,清香入尘,在晨曦映照下绚烂如梦境。而立在花雨中的华美白衣少年却沉浸在自己内心的痛苦挣扎中对这因有他在,而更加震撼人心的美感浑然不觉。
年年春如旧,岁岁花不同。
今年的春天,在聂如海生命中,无疑是最绚烂也是最冰冷的。谁说春如旧,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又何止是花,还有心啊!多年后他仍能清晰记得今年这个春天,他发现岑沧月不辞而别后的那份刻骨绝望和深沉失落,心痛的如同被万箭刺穿,想疗伤又找不到伤口,只能眼睁睁的任着它痛。
天已大亮,丽日普照,他总算勉强收拾了思绪,去准备早饭。
月儿嗜睡,一般要到日上三竿才能起来。
他平时起早了,经过她房前都会小心翼翼的放轻脚步,生怕扰了她美梦,影响她心情。今日也不例外。
饭好了,月儿还没起床,日头已经老高,难得一个好天气。
聂如海走到月儿门前,轻轻呼唤,好像怕惊了她美梦似得。
叫了几声,侧耳倾听,里面毫无动静。
“我进来了?”聂如海招呼一声,轻轻推开门。月儿重伤多日,一直是他贴身照顾,进出月儿房间已是常事。
房内安安静静,空无一人。
被褥叠放整齐,还是他昨天放置的样子。
月儿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应该是在家养尊处优惯了,一直有人伺候的原因造成的。
聂如海头皮发麻,仔细看了看那被褥,没错,确实是他亲手叠放的样子,月儿没有动过。
也就是说,月儿昨晚,根本没有睡。
他迅速在小小院落四周巡查了一番,没有月儿踪迹。
他又跑去问遍小山村所有人,大家都摇头说没有见过。
聂如海泄气的跌坐在地上,不甘心的猜测,月儿不告而别了,月儿她悄悄的走了,月儿不想看见他,月儿讨厌他黏着她,月儿嫌弃他,看不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