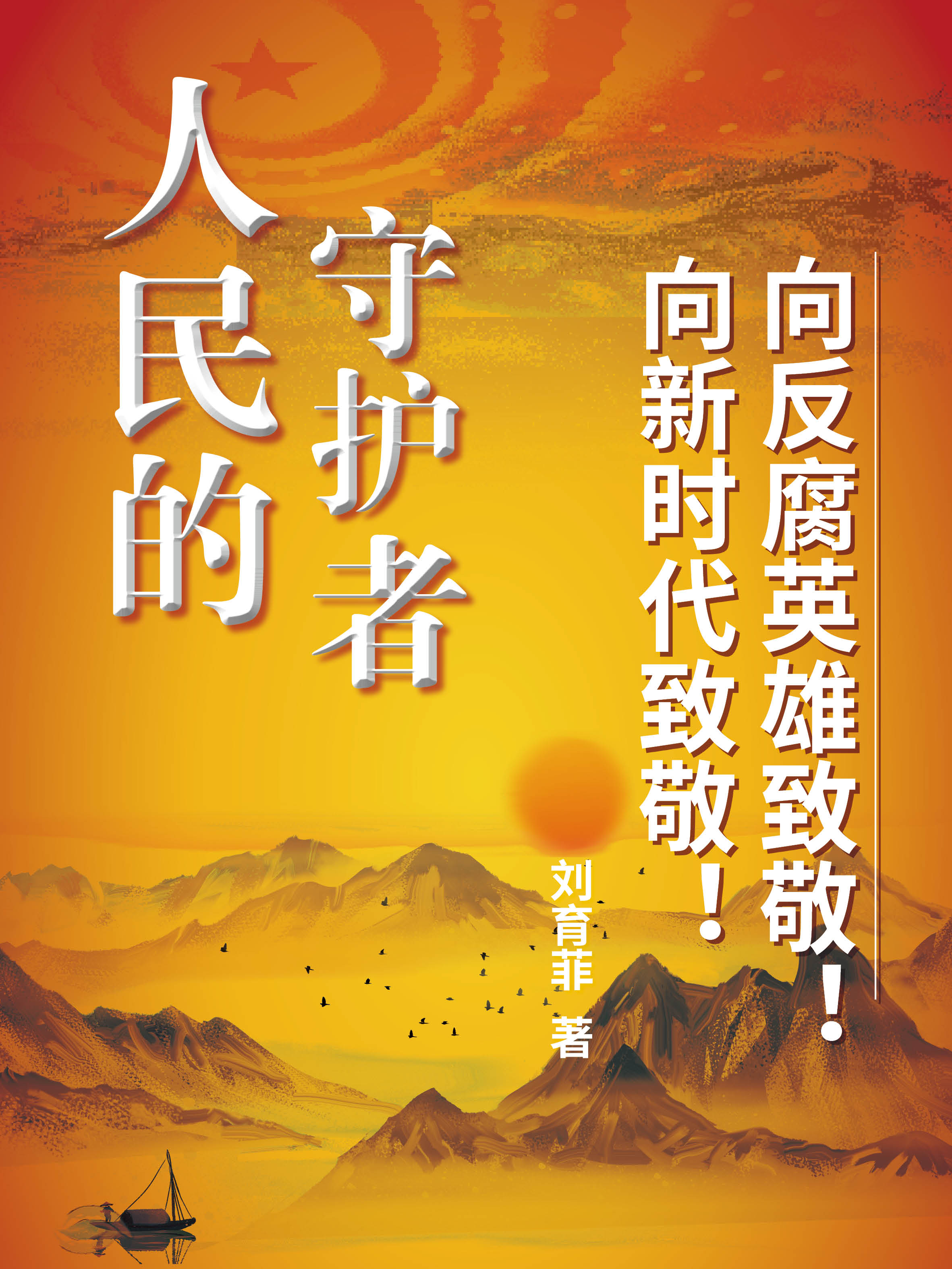八大王防地和我们的游击区中间,隔着一片干旱的沙河。宋青原和他叔叔宋贵斌换了便衣,一个长袍毡帽,腰中扎个搭包。扮作买卖人,一个短打扮,头上戴块羊肚手巾,装成随行小伙计。驾着四辆小车,几副挑担。半夜就出发,由一班战士护送。天亮来到沙河边上,大家停住了脚,就见河对面沙岗上有人按暗号摇晃白手巾。宋贵斌还了暗号,让战士们原地留下。把自己的手枪和青原带的两颗手榴弹也解下来交给班长。吆呼车担向对岸走,这时对岸也走过来几辆车、几副担。双方在河中间停下来,对方一个姓夏的副官就过来和宋贵斌对口令。那夏副官穿一身青布裤袄,斜背条二把盒子、挂着尺多长的红绸。对完口令,举手在呢礼帽上行个军礼,说:“贵军义重如山,司令竭诚欢迎,也叫我带来点压车的东西,让他换着装车吧。”于是两边推车的,挑担的各自卸下自己的东西装到对方车上、担上。八大王送来的是纸烟、洋酒和百多斤海盐——那时根据地遭封锁,盐是珍贵物儿。
两边礼物换完,宋贵斌吩咐挑夫小车回去。夏副官就牵过两匹马来,让宋贵斌和青原骑上,朝对岸去。刚上了沙岗,就见一队扛枪的人排列整齐,带队喊声“敬礼!”各自把枪举了起来,原来他们是按日本操典排练的。只可惜枪支牌号太杂,长短不齐。每个人的打扮又各不相同。有棉袄外边鼓囊囊套件纺绸长衫的,有马裤上边配了件大襟棉袄的。日本军装,团龙马褂。争奇斗胜。
副官喊了声:“出发!”
带队的敬个礼,发出口令:“向右转,开步走!”
那个穿大襟棉袄的人从怀里掏出个喇叭,穿日本军装的从树下搬起个大木鼓挂在胸前,就吹打起来。
“嗒嗒嗒嘀,达达嗒嗒达……”
“咚咚咚!咚咚咚咚……”
吹打了里把路,就停了鼓乐。夏副官和宋贵斌并辔而行,说些闲话。一进村子就又吹打起来。引出一群群的老乡,紧靠着墙根。挤成一团,满脸惊奇地看这支队伍。他们既不像鬼子队伍进村,逃得连人影也不见;也不像根据地过队伍,人们亲热地挤到大队两边说说笑笑。他们既不靠近,也不躲开。说亲热不亲热,说惧怕也不惧怕。保持着冷淡的敬畏。队伍若歇下来,自有办公人送茶敬烟,老百姓也仍是远远地看着。
半晌午时分到了司令部驻地马圈子。
这马圈子本来只有一户地主宅门,十几家佃户居住,庄子不大。参谋长穿一身呢子军服,带了一排入列队欢迎,就从村口直排到了司令部门口。这一排人全是短打扮,短家伙。一色的黑洋布棉袄,呢子礼帽,从上半截看挺整齐。宋贵斌老远一看就下了马,和参谋长鞠躬寒暄。参谋长伸手让他前边走检阅队伍。他这才看见队伍的下半截。这下半截可就五光十色了。裤子有呢子马裤,甩腿夹裤,还有大缎子套裤。鞋有踢死牛洒鞋、日本马靴、尖尖皮鞋和纳了云朵的老头乐。司令部门口两个哨兵,倒是整齐的灰布军装,打着绑腿。两支大盖枪,还上了刺刀。
院子分两层,外院只有三间南屋。沿墙放着两根扒了皮的大圆木。圆木上坐着五六个穿便衣背匣枪的跟班。一见参谋长陪宋贵斌进门,就虎地一下全站起来,有立正行礼的,有进去通报的。参谋长指指宋青原对那些人说:“这是友军的弟兄,你们好好招待。”话声一落,有个跟班的就拉着宋青原的手,把他让进南屋。
这时里院就传出了一叠连声地呼唤:
“司令出迎了,司令出迎八路军宋代表。”
招待宋青原的护兵和宋青原一起都回身往月亮门里看。从堂屋出来六七个人,为首的一位矮胖身材,貌不出众。戴一副玳瑁架水晶养目镜,留着一字胡。有五十岁上下年纪。上身穿出风的猞猁小皮袄。第二个纽襻上戴着金表链,下身穿深蓝湖绸丝棉裤,用一双一指宽的黑色菱角带着裤脚,脚下白袜子,黑大绒骆驼鞍棉鞋。若不是在腰间隐隐露出白朗宁手枪的皮套,看去完全是个“瑞蚨祥”的二掌柜。身后跟着的几个人,却都是长打扮。有外边套了马褂,有套了坎肩的,都敞着大襟纽襻、卷起袖口,故意露着翻出的皮毛。
宋贵斌摘下帽,连着点了儿下头。穿短打扮留一字胡的人双手把拳揖了一揖,马上抢几步走下台级,拉住宋贵斌的手说:“久违,久违。辛苦,辛苦。多谢八路军首长垂青。”一边又问参谋长:“随代表来的弟兄们呢?”参谋长说:“就一位亲随,让到副官处休息了。”一字胡马上说:“告诉下边好好招待,不要怠慢了客人。”
于是一簇人寒暄着进了堂屋。
这里青原就问招待他的护兵:“中间那位就是八大王?”
护兵说:“就是我们司令,你看和和气气的,一恼起来杀人不眨眼。那枪法简直是神了,抬手打飞鸟,说打头不碰尾巴。”
宋青原说:“这模样我看着好面熟。”
护兵说:“日本人到处画影图形悬赏他的脑袋,济南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
宋青原说:“对了,我大概在报纸上见过。”
这时当官的都进了堂屋,外院的护兵们就挤到屋里来看这个八路军。
这三间南屋,沿北墙搭着两铺板炕。窗台上放着些手榴弹、子弹壳,靠南墙钉了二十来个木橛子。挂着步枪子弹带,只在迎门有个满是油垢的小桌,两条粗粗拉拉的长板凳。护兵们进来,见青原坐在板凳上,就都面对着他坐到炕沿上。有人向青原递烟,青原说:“谢谢,不会。”另一个就对那送烟的说:“人家八路有纪律,不抽烟不喝酒!”
敬烟的那个说:“当兵吃粮,就图个舒服痛快,烟酒都不动,活着还有个什么乐子呢?你们也不许玩娘儿们吧!”
另一个兵就说:“好容易来了个八路军的弟兄,咱打听点那边的正经事呢,你问许不许玩娘们!也不怕人家笑话!”
这几个当兵的,有三十多的,也有十几岁的。有浑身匪气的,也有还带着农民的朴实相的。大家问这问那,青原就借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减租减息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几个人听着不入耳,哼起淫荡的小调在一边擦枪。有的就抬屁股走了。那个敬烟的倒是兴致挺高,站在一边笑嘻嘻地听着,不时插上一句不着边的粗话,惹得大家一阵阵笑。忽然在门口站岗的一个兵闯进来了,大声骂道:“小六子,你娘拉个×的光在这儿卖嘴,换不换岗啦!我这腿赁给你了,总为你站着?”
小六子说:“你把下半截全赁给我还差不多!”
那站岗的放下枪就来抓小六子。眼看着要打起来,堂屋门口夏副官喊:“司令请八路军那位弟兄到上房来。”
这场火并暂时压下了。青原整理一下衣裳,大步走进了上房。
这上房是两明一暗的格局。里间门口挂着白门帘,外间新吊的顶棚,四壁一白落地。迎面墙上挂着幅中堂,画的是“秋郊牧马图”,两上穿古代衣服,头戴毡笠的人骑在两匹马上,赶着几匹马在山谷间闲荡。两边配着洒金地的对联,上联写“跃马横枪拒顽敌千里以外”,下联对“秉烛议阵操胜算帷幄之中”。题款是“远程卞司令雅嘱。春节早舒文敬书。”沿墙有条案茶几。中间红漆圆桌上摆满酒菜,那群穿长袍的正陪着八大王宴请宋贵斌。
青原在门口站住,参谋长就站起来说:“弟兄,司令命令我敬你一杯酒。你一路辛苦了。”
青原看看宋贵斌,鞠了一躬说:“谢谢司令,可我不会喝酒。”
这时那留一字胡穿皮袄的八大王就大声说:
“我知道八路军的规矩,讲的是官兵平等。我这儿还没这个习惯,没来得及设你的座位。敬你一杯,表示尊重贵军的平等作风。小弟兄,赏个脸吧!”
宋贵斌说:“既这么着,青原同志少喝一点。祝咱们抗日军人精诚团结。”
“好!”八大王虎地站了起来说,“咱们大伙同饮。”
青原从参谋长手中接过怀子,轻轻抿了一口,辣得“哈”了一声,脸立刻红了。大伙都笑。八大王盯着青原看了半天,没有坐下。青原发现八大王注意看他,不由得也看了八大王一眼。八大王忽然离位说:“你姓宋吧?”
青原说:“是啊!我叫宋青原!”
“爷们!巧遇啊!”八大王离开桌子,摘下眼镜,走到青原面前,“你真不认识我?”
宋青原笑起来了:“怪不得我刚才远远一看就觉得面熟!原来是程伯伯!”
“摆椅子,摆椅子!”八大王一边吆呼传令兵,一边向桌上的人说:“这是我大侄子!在天津我们住过对门。他跟我那狗子同学,还是小朋友呢!”
夏副官抓住酒壶,挨次满上酒说:“再喝一杯,祝贺司令跟这位弟兄喜相逢!”
这时外院吵起来了。奶奶祖宗一通乱骂。八大王问道:“外边怎么回事?”
夏副官出去看看,回来报告:“有两个弟兄因为换岗不按时打起来了!”
八大王说:“押进来!”
宋贵斌和青原交换下眼色,都有点不安。外边响了一阵脚步声,又静了下来。八大王并不理睬。夏副官等着又喝过一轮酒,这才报告:
“把人押来了,等司令吩咐。”
“裤子扒了,预备军棍。”
外边又是一阵忙乱声。一会儿夏副官把一头方一头圆的军棍双手擎过来了,八大王挽挽袖子,谦恭地对宋贵斌说:“家法不严,叫你们见笑。”就提着军棍出了屋门。那些陪坐的赶紧也随了出去。宋贵斌和青原也只好跟着走到门外。这时一个当兵的正反坐在那小六子背梁上,按住他的两手。八大王抡起军棍,狠狠地朝扒光了裤子的屁股上猛打。每打一下,那小六子都喊一声:“司令开恩,司令开恩。”
打了有二十几军棍,屁股红了,肿了,冒血丝了。陪同的人才纷纷讲情。
“司令,饶了他吧,大好的日子别让他搅了。”
宋贵斌跟上去说:“司令,看在我的面上饶了他吧!”
八大王停了手,面不改色地说:“谢谢宋代表。”
小六子说:“谢谢宋代表讲情。”
八大王说:“还有那一个呢?”
站岗的那兵早就吓的没了人色,扑通一声跪下就给八大王磕头。八大王说:“拉下去,冲这熊样儿,叫值星连长多打他几棍子。”说完带头回到屋里,洗洗手,接着喝酒。宋贵斌和青原早已没了吃喝的兴致,也只好勉强陪着。
吃过饭,夏副官把宋贵斌和青原送到客房去休息。
屋里剩下两个人时,宋贵斌才问青原:“你跟这个土匪司令怎么还有老交情呢?”
青原说:“交情不老,不过是三四年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