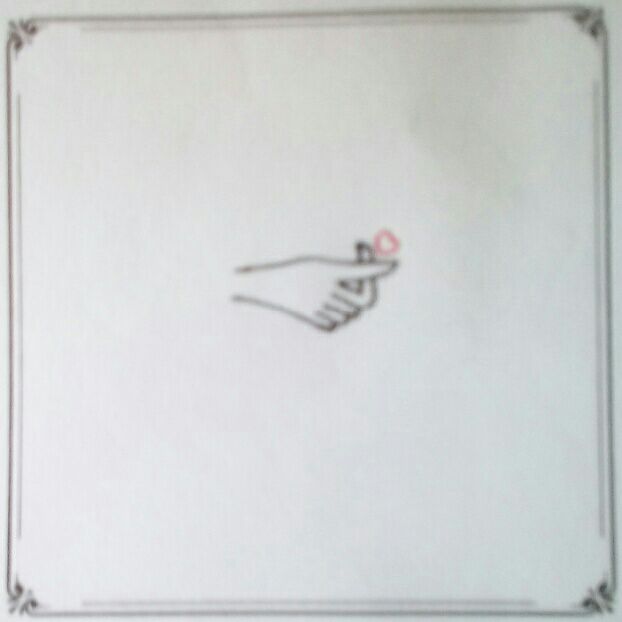傍晚在湖边散步,忽然发现这座小城建筑的美,晚风吹动湖边的柳树,夏天要来前的清新的绿,不知是不是早上那个梦的关系,灵夕忽然很想写封信给林书浩,告诉他她感受到的一切,他们不常联系,但是有时候突然的就很想和他说一些话,他们从来不打电话,还是只能写下来。
仍然是全麦吐司面包,苹果,牛奶,一天三餐都是同样的食物,竟然也不觉得腻烦,只是胃有点不舒服。
这小房间没有桌子,她坐在床上,铺在膝盖上写。
傍晚去湖边散步,不由感慨这个地方宜居,风景上当然是G城更美一些,但这个小城市有一种井然的美,我留意到它的建筑,间隔,朝向,都有一种设计的讲究,尽管我没有上去过高楼上的房子,但都能想到它的采光很好。我在N城看见的楼房拥挤,逼仄,听见人讲,房产商卖完小区里的房子后,又在留作花园的空地上建了两栋,活生生挤了进去,完了她说:“就算白天,也要开灯”。
前几天到荷城去,空气很好,但好像少了点美感,又到了L城,果然是工业城市。
有一间植物超市,是第二次进去看,完全忘记周围是闹市,像到了不知什么地方,也有人进来看,有的带走一盆花,或多肉,但我并不想。
在人来人往的街上,一个空旷的地方,有一个男子摆了许多好看的花来卖,是许多,比我见过的别的城市都摆得多,好几天都看见,我想他或许每天傍晚都去,我不知道他卖得多不多,但那不怕麻烦带许许多多花过去,一盘盘摆放,不停地修剪着的一份心,就为这个城市增添了许多美感。
设计合理的建筑,干净的空气,不拥挤的车流,宽阔的书店,图书馆,从容的人,从容的生活,许多地方有花,这才是合理的城市,合理的生活。
写了许多它的好,似乎是很适宜停留的城市了,但我没有这个打算,我知道这里是他乡,只适合短暂的停留,然后离开,或许真的是上了年纪,对生养的地方的水土依赖起来,我想过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从来都觉得要离开家里远一点的地方生活不要被干扰,我想试试不回家过年是不是少了许多琐事与麻烦,但我还没来得及去很远的地方,试试不回家过年,就已经觉得不想去别的什么地方不回来,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疲倦了,忽然觉得想安定下来。
从来都是去任何地方,行李简单,在一个地方停留,不买许多想买的书,不购置大件物品,行李简单得随时可以离开,但是忽然希望有个能停留不再不停迁移的地方,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感觉到安定,安心,家也不是,家是必须早晚会离开的地方,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吗?但我在他们那里也感受不到安全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哪里都很快要走,去找朋友常常也是,我总是不能“既来之则安之”,但是有的人却能让人感到安心我知道。
她知道这仍然是不会寄出,不会拍照给他看的信。
下了一早上的雨,也还是起得很早,心里或许有点着急,买不到书,日子在一天天过去。
或许也是这潮湿的环境让人无法睡,尤其楼下,上次来的时候就感到那棵芒果树遮住太阳光,这时候更是积了一洼黄泥水流不出去,楼下的铁门,一开门进来,摩擦到地上,那泥沙声让牙齿简直想咬人,阴暗的室内,潮湿的地面,似乎开门的瞬间惊起了沉睡的蚊子,细菌,集体向开门人扑过来,全身马上感到一阵寒痒。
从超市买来的一张夏被,下雨天没有办法洗,这样盖着,总感觉上面有一层腻垢,虱子,总感觉身上不停被虱子咬,这里痒那里痒,但看起来又没有任何异样。
没有一天睡得好,总是三四点睡去,将近五点醒过来,又很难再睡去,直到天亮才能又再睡一会。
她想回去了,但是她没有家里的钥匙,出门时她想要一个,但是她母亲说回去再从她那里拿,她知道她母亲的心理,她也没坚持要。
如果她回去,她母亲一定要她在她租住的房子里住,等她一起回去,但是她不想在那里住,逼仄的空间,比她这里更不方便。
月底了,月经没有来的迹象,似乎在意料中,只有在安稳的日子里正常,这个月多是奔波,不正常吃饭,剧烈的思考,情感起伏,她只有一方小小的镜子,不敢看自己,脸色一定很差。
再次去图书馆,上次没有到楼上去,这次上去了,像走在没落的大楼里,只有一个管理员在看手机,她忽然出现,像是天外来客,她小心翼翼走向书架,一排排似乎布满灰尘,花花绿绿的书,已经黄旧,有的破损,心灵鸡汤类的,机器类的,革命类的,有时限性的过时了的书,她不敢再细看,简直要完全破坏印象了,朝玻璃窗往下看了看,没落的城市,她马上要逃离这里了,管理员像一个定在了时光中的人,她想象她考进这里来工作,之前的兴奋感变成一阵惊悚,她匆忙走进电梯下去,没有一个人。
在一楼,不是周末,只有零星的几个人,上次她想看的书不见了,其他的也变成常见的没有吸引力的书,她回去了。忽然体会到再见只是破坏印象。
中午也无法睡去,难受得要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气味,但灵夕总觉得有什么气味,雨天的潮湿的环境,她感到细菌在疯狂地繁殖,味觉,嗅觉,触觉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异常敏感,直至混乱。
她感到窒息,她要出门去。刚下过雨,湿漉漉的地面,离开住宅区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在马路边上走,嘀嗒的下起小雨来,走在老树下倒一直没淋到雨,只听到声音,也没打算返回,反正拿着雨伞,前面看到湖边公园,雨越下越大起来,树没有了,只好打起伞,还是想到公园里去,或许只是不想回去,过来一个红绿灯,雨更大了,想到鞋子湿了没有得换,还是要回去了,又看到对街一个绿色邮政,但总不相信只是邮政银行,总觉得还有旁边还有邮局,雨水模糊了视线,竟然要过街去看,但是有没有邮局又怎样?她又不是在找,非要过去看有没有,莫名其妙得可笑。
早关了灯,也算是“早睡早起”,但是十一点半,忽然拿起手机给房东发消息,明天要退房,又何必这样浪费时间?
没有回复,兴许已经睡了,这个小城不见得像大城市晚睡,她只是担心房东不退回押金,当初是付一押一,没说至少租多少个月,但房东一定默认半年以上,灵夕当时当然不敢问,如果临时走也还有个借口——当初没说好。
早上六点钟手机振动,是房东的消息,“可以,但是不退回押金”,马上清醒了,果然。她做好不会退回来的心理准备,几百块钱对她现在没有工作还是很重要,她还是觉得有机会得回来,看她自己的了。
她看一个女记者的书,她写到一个摄影师怎么得到拍妓女的机会,他说,“要让她们同情你”,他变得很穷,吃都吃不上,她们看他确实穷,同意让他拍。
放低自己,她想。她想起看的第一家也说至少租半年,末了房东说了一句,“因为短期她搞卫生也很难”。她要自己清扫干净,完全恢复原样,这样房东不用打扫,得回的机会更大。
“......真不好意思,没想到只租一个月不到,我是过来考试,但没考上,当初以为我朋友已经同你说好,可能只租短期。我走的时候一定打扫好卫生,完全恢复原状......”
她没再回复她。她也没再发。
当然是要走的,说好是十二点退,十一点半已经都收拾打扫好,给房东再发消息,“我已经都收拾打扫好了,您看什么时候过来看一下电表水表,我也好把钥匙交给您”,“我还是希望您能退房租给我,我现在没工作,用钱也很紧张,希望能得到理解,谢谢您”。
她说她晚上下班回来看了水电表再退给她,钥匙留在门上就好。她也还是存了个悬念,她也许会扣她一半钱,理由是她没讲只租短期,但是能得回一半也总比都没得回来强。反正在钱的事上,还是很考验人性,何况素昧平生,她真是没见过她,看房是她的一个侄女给开门看。
她在公交上,很开心,公交车只有她一个乘客,简直是她的专车,她很感激遇到好人。她相信她。没想到为这么点钱这样,从前有稳定的工作,出去吃一百五六十的早餐明知贵了也不觉得怎样,五六百块做了一个很不喜欢的头发,也没多可惜,现在尽管这样,也并没有觉得后悔,她看日记才知道,三年前就想到要辞职,也就是工作的第二年,她写:“三年后会辞了工作,会去看你一次,或者你已为人父,倒没关系”,她笑了笑:工作是辞了,但还是没勇气去看你。其实你也没为人父。
她没跟母亲说今天回去,但是她正巧发信息来,说她要回去问灵夕回不回,来的时候她倒说和她在那里住,她总是有点介意灵夕睡别人的床,她有洁癖。灵夕当然说回。
她去大排档做了一天,“拿那条毛巾擦桌子,脏得实在受不了”,第二天就不去了,她从前在学校食堂的一份工倒做了很长时间,也是她最有余钱的日子,她几次三番要跟灵夕父亲去工地,灵夕父亲不肯带她去,行李都收好了,跟着出门,吵起来,他自己骑车走了,她只有咒骂他。当然是别人转述给灵夕听,她已经在学校,她完全能想象那场面。他说是带去合不来,争吵。她母亲当然不这么认为,她认为是带别人去所以她不能去。灵夕已经不想管这些,她对这些心烦到麻木了。她确实也认为母亲有控制欲,和她生活有窒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