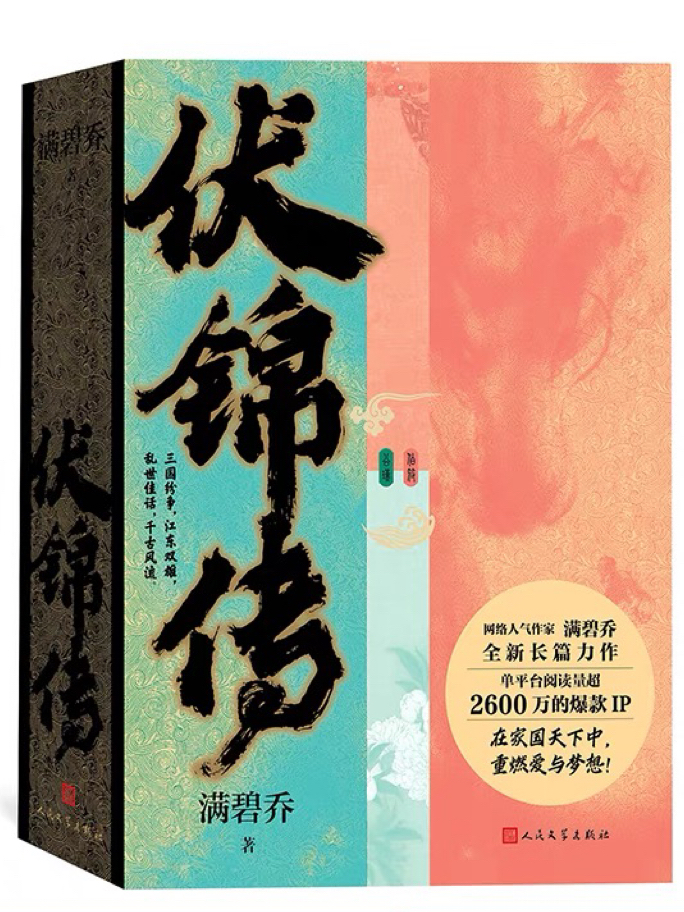宫殿的阁楼上,是朱红色的栏杆和柱子,金色的琉璃瓦封顶……而启睿,就这样大刺刺的坐在栏杆上,侧对着正缓步走来的刘蔓樱,靠在柱子上,修长的双腿随意的搁放在栏杆上,长长的衣摆落下,带着无限的惬意和优雅。
他嘴里嚼了一根不知从哪里摘来的野草,轻轻道:“缨贵人好闲情!”
蔓樱一惊,幸好这会子身边也没人,便是慢慢转过头,双眼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仿佛是有许多话想问他,最后又什么都没问出来。
启睿微微一笑,笑眯眯地瞅着她,整张脸上带着温和,往日的阴霾狠戾都消散尽了,大抵是因为有了一个温婉灵动的妻子吧,所以化解了他满身的狠绝。
她转身问:“殿下,别来无恙!”
“这么些日子没见,贵人倒是生疏了,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当初我们……”启睿竟是冷笑了一声,随即慢悠悠地吐字出口,似云淡风轻。语毕,他剑眉蹙起,不羁地朝着她挥了挥手,示意她能够过来。
瞧着蔓樱脸色无情地一变,他便是轻声细语的吐出一句话,黑眸转到刘蔓樱的脸上,顿时就变得慵懒而深邃:“细细一瞧,公主……又美了许多,不似以前骄横,倒是更加增添了几分妩媚之气,莫不就是传说中的狐媚惑主?”
“我是狐媚子,可魅惑的是谁?究竟是高高在上,一呼百应的皇帝陛下,还是……你一身铮铮铁骨的定王殿下?”刘蔓樱轻轻扬起唇角,眼神之中多了几分魅人的意味儿。
对于那明显的嘲讽,启睿仿若听而未闻,反之眼角之中竟然还带着笑意,“那何不妨再来魅惑一下试试,也不知道你的技术退步了没有!”他刻意将某些字眼咬得极重,随后翩然一跃,步履轻盈地缓缓往前踱了两步,黑眸深处明亮得有些异常,那眼神似乎是有恃无恐,甚至还带着征服,就如同他们在大魏初次相见时候的样子。
蔓樱听完他的言语,面无笑意地嗤哼了一声。“今时不比往日,那时候,你未娶我未嫁,不算苟合,现在不同,王爷娇妻在怀,蔓……缨儿已为人妇,再要是有些不光彩的事,那便是叫做,叫做什么呢?哦,对了用你们吴国的话说,便是要被拉去浸猪笼的,大逆不道!更何况,当时初涉情关,年少未经情事,现下经你这么一番苦苦纠缠,早已经疲惫了心眼!”不过短短几句话,蔓樱说得倒是极轻极慢,却也冷得全无一丝温度。
“那又怎样,本王从来都不将这些放在眼里!”他双目犀利起来,认真地凝视着她,双手压在她的肩膀上,“你是我的,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只能是我的!”
“蔓樱,你早就是我的女人了,我们在床帏之上是那样的契合,你都忘记了吗?”说着,启睿嘴角微笑的弧度扬得高了些,某种明亮的眸光,闪过幽暗的黑瞳,
刘蔓樱脸涨得有些红,心里五味杂陈,分明是有些淫邪的话语,却听着倍感哀伤,她有满腹辛酸想要一道说了出来,却发现终究是哽在喉间,说不出道不明,却也咽不下去。
启睿一叹,事到如今,情难自禁,也管不了那样多了,一把将她搂进怀中,闭上眼,头伏在她的肩头,呢喃道:“我走了多少日,便念了你多少日,此次回来说是给灵儿安胎,实则,不过是想见见心中的女子是否安好!”
蔓樱伏在他的怀间,摇着头,终于是隔着袍子去抚着他的肩背,哽咽了半天,终于吐出字来:“暮璃,你……瘦了。”
启睿向来理智冷静的脑子,很难得地出现了瞬间的空白。
“征战沙场,受尽苦累,又怎能不瘦?”还不等他回答,蔓樱便自己又嘀嘀咕咕了好多话,眼里,脑海,充斥着的是满打满的心疼。
我和你,一步之遥;我既无法上前一步,陪伴你左右;也无法退后一步,果断地离开你,而今能做的竟只能静静地看着你,默默地在心头描绘你的容颜。
他说:“不累,只是相思苦!”
她情难自禁,泪湿了白衣裳。他永远不会知道,自他走后,她里衣永远都是不变的白色,不是她忽而变了性子,变成文弱妃嫔,亦不是她为了虏获君心,掩去身上的红衣似火,只是……在为未亡人戴孝,祭奠她的挚爱之人,还有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恋!
多少次,她在梦中哭醒,多少次,她又看到他在背后呼喊她的名字,而她狠绝地不回头,又有多少次,她想起他们缠绵无尽……
“那时,你说,已经是最后一次了!”蔓樱似忽然想起了什么,只是淡淡道,却并不推开他的身子。
“醉酒的话语又岂能当得真!”他叹了口气,那不过是一时之话,由始至终,他就没有想过要放弃她。“我于你,从未改变过心意。”
“那你为何又要在皇帝身边安人,为何要让我前路纠结?”她自己都不曾预料到,竟然便那样直愣愣地将心中所想的话语脱口而出了。
自然,这样久别重逢的凄婉画面之下,说这般话大有焚琴煮鹤之嫌,可无奈,有些话茬子偏生就是止不住的,憋上那么一时半会儿的,愣是别提有多少难受的了。
蔓樱此时当是有些担心的,这话语仔细咀嚼,偏生又带了些争风吃醋的画面,惨就惨在,这争的不是他定王启睿的风,吃的也不是他身边女子的满瓶子醋。
果不其然,启睿有些不悦,“你既不爱他,我在他身边安几个女子又有何事!”
“你爱怎么做便随你,反正只要你自己高兴就好!至于我……只要乖乖坐好你的女人就可以了,什么样的大事情都只要相信你便可以!呵呵~”她颇有些无力地说着。
这话如若是从平常女子的口中说出来的,那兴许还是句不错的情话,是一个柔弱的女人对自己情郎的信任。
可说这话的人偏偏是刘蔓樱,偏偏是这个固执的女子,她说出这样的话语来可不是什么好意思,言下之意其实不过是在嗔怪这启睿太自作主张,只顾着自己。
“你……”启睿亦是无可奈何,只得吁了一口气,神色迅速恢复了平静,随后执起她的手,道:“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蔓樱朝着他投去了一计迷茫的眼神,却在见到他眼底的坚定之后,立即凝了心神。
在他面前,她十分明白,有些事情,只要他决定了,便无需想着去整改下了。
两人并肩走在半路,初夏的景色自身边擦过,分明该是极美的,却偏生显现出了破败之意,颇有些凄凉无力。
忽而,启睿带她进了一间颇有些旧的宫殿。
蔓樱迷茫,正要退步去瞧瞧那宫殿的名儿,却被面前的男子拦了下来,“不用去看了,这是我母妃原本的寝宫,我平日里也时常坐在这里,一般不会有外人进来。”
“嗯,这坏境倒也清雅!”蔓樱小心地瞧了瞧周边的景色,微笑着说。
“不是清雅,我母妃一直喜欢鲜艳的,只可惜,父皇登基后,只来过这里一次,还是为了别的女人!所以……”启睿却是摇了摇头,怔怔站了一下,又闷声道:“这里是冷清,一直都是!”
进了里头,启睿带她进了一间小密室,怎么进去的,蔓樱一时间倒也没有留心记住,只是知道,不同于一般的密室,都是在书架或者床底后头的,不过就是在其中那个最大气的房间之中左右走了几步,底下便多出了一间小屋子。
启睿拍了拍蔓樱的肩膀,示意她大可安心。
蔓樱不过玩笑了一声:“如此隐蔽,倒也是个偷情的好地方!”
“你啊!”启睿笑着摇了摇头,随即拉着蔓樱一道在主位上坐下,拍了几下大手。不消须臾密室中间便又裂开一块地,一个铁笼子缓缓上升。
蔓樱从没见过这种阵仗,当下便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但见两个铁面黑衣人手里压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人,一时间,辨认不出到底是男是女。
“这是什么人?”蔓樱指着笼中的人,不禁开口。
“既然不知,那便猜猜吧。”启睿不紧不慢,笑得高深莫测,深沉黝亮的黑眸中带着一丝令人费解的光芒毫不在意地应了一声,温文尔雅在这样的时间地点中都显得诡谲而狡诈,语气里听不出任何的喜怒哀乐。
蔓樱皱了眉头,一时间难辨情绪,只是定定地看着笼子之中,想要从那人裸~露在外的一点点肌肤上判断出他的性别身份。
笼中之人肤色也不知是受了惊吓,还是原本就是那样干净,只是惨白如雪,没有一丝人色。他猜不透现在主位之上的男子会怎样处置他,是斩首示众,抑或其他?
反正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哪条路,都预示着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恨只恨当日鬼迷心窍,受人诱骗唆摆,落得如今这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