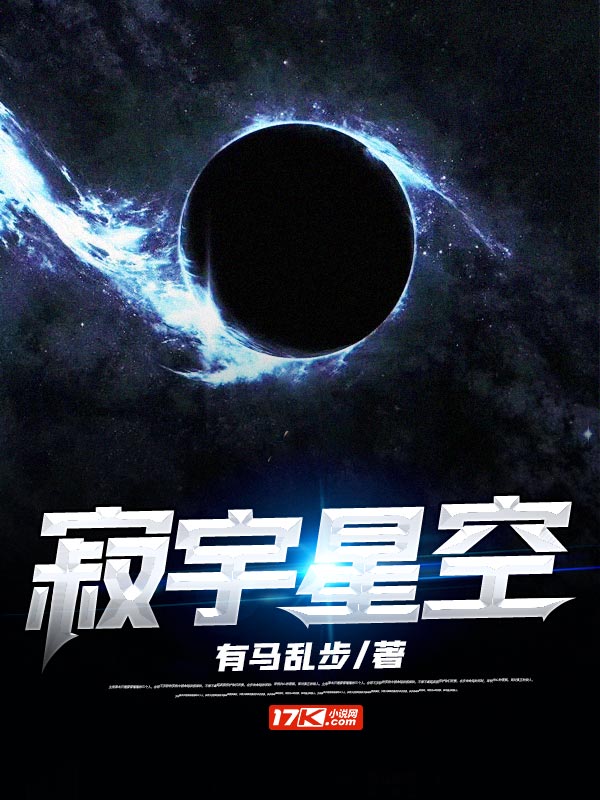至于再向沙湾里前进,便可见一小瀑上边有一清潭,一两寸的水长流不止,我们家便吃此处的水,潭上有棵小樱桃树,樱桃树一旁则是伐木者开通的运木通道,斜着向上一直可到山岭,向前去可再见一山间平坦之地,常有荆棘满途,每到春天,需要再开出路来,但这事往往由牛来完成,只需一天,便可吃出一条路来,那一路的蜜米儿树很多,也大多很老,一屋多高,生地一片一片,常有鸟儿松鼠流连其中。
在蜜米儿树的包围中,有一片坡地,往来由我家种着花生和黄豆,后来荒弃,很快便长满小树,牛儿偶尔光顾。再上去便有了瀑布,自一整块板岩流淌下来,二十几米的长度,往往将之显得光光整整,荒废的小路沿之向上,也不知去处。破天荒地,瀑下有一块草丘,操场大小,却不生别的草,仅苔草一类,严严实实盖在地面,地琵琶在上面秀起梅花来,倒显生动,再一路上去,八月瓜和樱桃生地很是紧凑,叫我摸不着头脑的是,最后的路却是变得宽敞了,横在半山腰,却足有两三米,可通汽车,左到沟边不见,右则延伸到森林中,慢慢消失,来而无源,去而无处,不知作用。
除了摘路边樱桃,我和爷爷还常常折那路,上山去采灵芝。科教频道的介绍叫我对其功效震惊不已,爷爷听镇上收拢这些药材,便同七叶一枝花一样,满山寻找起来,而我,抱着好奇,收集宝贝的心态,同他一起。
那树林显得幽森多了,杂草枯木四处,地面湿滑陡峭,倒是林中怪响不断,却不现身,叫人生恐,但拿着弯刀的我似乎并不是人,那时我觉得,我可以一刀把那鬼魂或者猫儿头杀死,像杀猪那样,然后搬回家,叫婆婆炒了吃掉,但我从未遇见过那怪叫的东西,是什么也就不得而知。
山中灵芝很多,同药房中的灵芝不同,生长着的灵芝更加美妙,虽然是通身漆黑或暗红发紫,不同于松箘那样通俗娇嫩,也没有松箘那般暗香,纯如一草木无味,但比之周身其他,可显天地神妙,与众不同。细腻光滑处和孔洞褶皱处各存韵味,纹路古朴。或才开如扇,小巧灵秀,或经年如伞,方得圆满。其斜向上生长的姿态有着同悬崖虬松一般的美妙,有的叠加生长,成为一体,张驰有度,活生生是另一株松,叫我迷恋不已。
那灵芝同蘑菇一样,年年生长,其中有不知多少年的,可有脸盆大小,这类我往往不舍得摘下来,便随其根下朽木黄土一同取下,回家培养,至于小些的,我便放过,袋中的多是手掌大小,可供出手。
同灵芝一齐生长的还有许多奇物,比如“刷竹菌”,那是一种有着松箘粉红色彩的蘑菇,却不似蘑菇样貌,形似刷子,将伞盖取而代之的是如同树枝一般,向上生长的枝杈,但互不干扰,各有生长空间,脆嫩无比,稍有碰撞,便是粉身碎骨。
在爷爷养羊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同牛一起到这山间吃草的羊群往往能够不经意间带我找到些山中的财富,比如一处樱桃,一藤八月瓜,一桩栋菌,我常常为这些意外收获而感到满足。
两岭交汇处是一座高峰,同珠穆朗玛相似,一面峭壁,其它被绿,在群山间,最为高耸,也无路可登,每至冬春,那峰尖的雪,总快人间一步落下,晚人间一分融化,在湘西还下雪的日子,它倒无足为奇,到我高中时,便不再下什么像样的雪,而那峰尖,不改从前,绿林在下,它白首顶立云间。
我常常对那群牛羊无法释怀,在我的童年中,小鱼,小狗,小羊,小牛,这些皆是我喜欢的,见过的动物。
在对鱼的时间里,我只是平静地看,每到一个地方,我常常询问大人们:“哪里有河?”
对于这类不同于其他小孩儿的想法,大人们往往很快给予满足,我通常去到不同宽,不同深的河边,蹲下,有时趴着,翻开小石头看看底下有些什么, 如果有鱼我就找个地方坐下来,细细等待观察,如果有螃蟹,我就把它放进我在河滩上刨开的小坑里,看着它在坑里冒起泡泡。
对于那些本身有鱼可欣赏的家里,比如刘凯望家里,陆爽家里,他们两家都出奇相同地把鱼放在长满青草蔓的石缸中,陆爽家里的鱼是他的哥哥陆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他们家后面有一个蓄水池,和宋丞家后面的一样,但宋丞家的蓄水池没有鱼,所以陆爽家的蓄水池就显得独具一格,我们常常在夏天和冬天来往拜访,也就是暑假和寒假的时候,陆爽家也在一处山谷,人们称为陆家湾,照大人说,那山谷里还有熊猴出没,这我自然没见过,但狼狗我见过,也被它们追过,人们都知道,陆家湾的狼狗是出了名的,那时那里很多户人家养羊,便不时有这家羊叫那家狗给咬了,叫赔钱,他们也和气,知道自家狗子咬羊,便不抵赖,如果是一群狗子作案,那就分摊,谁也没个意见,后来那里的人们就买来铁链,将狗子拴住,守住自家门户即可。
拜年往往是大人们的来往,小孩作为附属,跟随其后。在那汹涌的大山间还没有通水泥路的时候,我和我的爷爷,婆婆,姐姐,常常从那恰好可以通一辆汽车的土路上走过,随笨重脚掌而飞的已不是乡间的尘土,而是山间的石子,那山间的土路是蜿蜒的,故而有了直达的小道,叫来往行人踩得干干净净,但陡峭的大山也在这小道上,一展它的绵延。小道横穿土路,自山脚通向山岭,再从山岭下来,它们比之蜿蜒的土路,一起一伏,少有转折,显得很是干脆。在路上时常见对脸来人,后人追及,不管认得与否,人们总相顾言笑,晴天时人们走走停停,若背着背篓,也不将背篓取下,只是寻一可够着屁股的石头,借力蹭上靠着,男人拿头上草帽扇风,女人则取头上束巾扇风,谈些什么话来,一路不曾停过,至雨天则不作停留休憩,一气走完,这小道不比土路规整,泥坑水洼一路,常叫行人滑倒,朝前或朝后,滑行几米方才停下。
在走路上,我对于大人们是全胜的,走在前面的我,常常停下,等他们刚刚走到我跟前时,我便再朝前走好一段,又或是山间的小花小草什么的,山崖陡坎什么的,河滩池塘什么的,叫我为之迷恋,故也停下欣赏玩耍。
通向陆家湾的垭口修有两处吊脚楼,在公路的两边,另外有一片修竹傍在旁侧,我们去时,往往先叫他们家的狗子发觉,大叫起来,似乎有别家狗子响应,一时狗吠传天,那些户人家好奇地从楼上探出身子,是个扎着有蓝色格子的头巾的老婆婆,见我一人,便问:“你是哪个屋里地孩儿,你哪门一个人?”
我有些忸怩,小声说:“我嗲嗲婆婆到后头。”
她又说:“我屋里狗子栓到地,你莫怕,你只管走。”
我点点头,小心地从他家小院子前路过,穿过由群居环绕着的水田,再穿过一户人家的阳沟,便可见到下坡,一片的山被开辟出来,成了田地,人家散落其中,小路自田边蜿蜒向下,陆爽家在这些房屋的最上头,走几步,便可见到他家的青瓦,我飞快地朝他家跑过去,但他家的狗子向来灵敏,不多久便朝我叫起来,我便停下,对那屋里喊:“陆爽,有狗子!”
有时从那屋里走出的并非陆爽或者陆彪,而是他们的表兄弟,陆利,他们两家是相邻的,只隔了陆利家的猪圈,陆爽家在最顶上,而他们爷爷的家则在下头,吃饭也常常三家一起,到长者家里吃,而他们几兄弟自然也很是相熟,听到我的呼喊,他们常常一齐出来,很快将狗子驱赶开,对我说:“你下来,它不得咬你!”
他们三兄弟常常分享碟片,在我一一欣赏完他们家小鱼儿后,看碟片便成了我们最主要的娱乐项目,大人则聚集在他们爷爷家,围住火坑畅谈不止。
陆爽家的碟片以葫芦娃和奥特曼为主,我们往往吹嘘自己有别人没有看过的版本,也确实,在陆爽家里我看到了《葫芦小金刚》,在陆利家我看到了初代《奥特曼》,而他们本身,也愿意同我们再次观看一遍。
在陆爽家和他爷爷家中间,有一个牛棚,陆爽和其他小孩总在那牛棚上乘凉,我找他,便去那里,也爬上去,有时他爷爷把牛关在里头,我们便找来许多茅草,给那牛喂去。但陆爽的爷爷并不喜欢小孩儿们爬他的牛棚,常常并着怒气朝我们一众喊:“您几个溜牛棚,跶死起!”
听到这话的我们,只得不舍地走开。
有一次暑假,我在他们家住了许久,一日陆爽的爸爸也就是我的陆家幺幺,陆武清对我们说:“跟您两个搞几块钱,去芭蕉垭买东西儿去。”
我们答应,他又说:“走小路,就这条,叫陆爽带路。”
我们便这样出发,但我往往走在前头,但我似乎忘了陆家湾的狼狗,也就是在路过一户人家时,我才想起此事,我听到坡上吊脚楼里传出狗吠,还有一阵阵急促而微弱的脚步声,那无疑是狗子走出来的,我慌忙跳下田坎,趴在地上,而狗子只是不停地在那吊脚楼上叫嚷,并不下来,等陆爽来,我也便拉他下来,说:“那屋里有狼狗,等它回去了我们再走。”
他点点头,后来那狗子叫了一会儿,便回家去了,我探出脑袋,打探虚实,见无事便朝陆爽比划个行动的手势,我们悄声爬上小路,刚走一会儿,不想那狗子竟然发现了我们,我只得叫一声:“跑!”于是我们便同那狗子角逐起来。
但好在那狗子终究是念家的,追了不一会,便摇头犹豫一会儿,回家去了。而我和陆爽才得了逃脱。
长大后我并不在他家居住太久,他家三家的客人很多,我常常在陆爽爷爷家洗澡,去陆利家睡觉,或从陆爽家醒来,跑去陆爽爷爷家吃饭。
我于他们这个地方的最大印象就是摩托车,最先骑上摩托车的是陆利的哥哥陆荣,其他的小孩儿则是人手一辆自行车,常常在踏场比较着漂移。后来陆荣去打工,陆利只较我大两岁,最为年长陆彪哥哥便成了这车的主人,常常搭着陆爽和陆利行驶在公路间,那时水泥路恰好修到芭蕉垭,而他们只需骑行一段土路,走出陆家湾就可上水泥路,那时,陆彪才上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