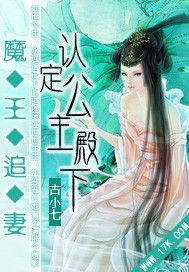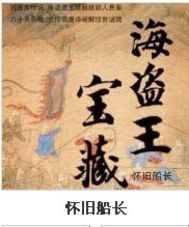在我的童年中,玩耍处不过山野田间,在华进哥哥还寄住在我们家时,我是那一群玩耍孩子中的跟从者。
那时,南方平常的大雨总让屋侧的岩壁冒出水来,那岩壁是我们家修屋场时开凿出的,那石壁所显出的一层一层的纹理,和张家湾中的如出一辙。每到春雨时节,泉水便从那壁上缝隙流淌出来,汇入水沟,排入田中。它们常常挂起瀑布,打在石头和水面,那似鞭炮的噼里啪啦之声,便常常在春夜响起。而我们的玩耍,则是寻一短棍,照那出水的缝隙小洞来回抽插,在堵住洞口不久,那水便大些,而我们比的,则是看谁的孔洞流出的水最大。流水的洞仅有三处,我和我的姐姐,宋丞、宋琪以及华进哥哥,偶尔还有陆彪哥哥和陆爽到来,往往没有位置给他们分享,便只能拿着小木棒在那岩壁上捅个洞,妄图它流出水来。就是这么一件无聊至极的事情,我们常常可以玩到春水消停。
那壁上是一丛巨大的胖竹,周围零散生着些紫竹,细弱地支在那绿从中,每至春天,便有酸蔗梗生出来,紫斑在翠绿的根茎上密密麻麻排布,一人来高,我的爷爷常告诉我:“干哒,就跑去扯根酸蔗梗,吃了就不干了。”
他虽然常常那么说,但我从未见过他吃那东西,而是喝背篓里携带的茶水。后来我去吃了那东西,翠绿里头是空心的,嚼起来,总是发出压碎竹子一样的清脆之声,自身的水分着实叫人解渴,但其酸却是叫人口水不止。
阳沟有一处洞眼,丢满了酒瓶,洞口不足一把椅子那样高,对于洞里的世界,我常常浮想联翩,认为山洞里,总归是住着妖怪的,为此,我不时拿着爷爷的手电筒趴在一堆玻璃酒瓶上,朝里头张望,有一天,我把酒瓶刨开,匍匐着进了洞去,里头四处滴水,却没有钟乳石笋,片状洞庭只有两三米高,自层岩中钻出的带些油污似的黄浊水流,汇聚到中央成为一片,有几根朽木支撑着洞顶,对面再无其它路径,不知道从前用来做些什么,听人说,很久以前便有了,这样的洞,山谷沟里也有一处,半人高,藏在沟边的树丛里,那里我早早便去了,也是一路的黄色浊水,里头有处折弯,不久便又没了去路,和屋后的洞似乎是一人所挖,不知用处,那浊水又是什么也无从知晓。
那沟中本无鱼儿,我放养了抓来的苗才有了那么一群。在此之前,唯有螃蟹和沙鳅两类,至于我爷爷和婆婆所传说的娃娃鱼和红色鱼儿则自始便不得其踪。
华进哥哥那一伙,总是相邀来这沟里抓沙鳅,之后便一锅炒了,和他们在大湾沟里抓的螃蟹一样,送来一盆,叫华进哥哥尝,在伸到我的面前,我拿起其中分不清部位的一块,像是吃一整块盐一样,慌忙吐出,而他们,则是抚在门框上哈哈大笑。华进哥哥在我家的时光在我的记忆中是很短的,他是我们表兄弟姐妹中最大的一个,总是领着我们玩耍,年纪小的往往被排斥在玩耍大队之外。
我在其中排倒数第三,宋丞和陆爽在我之后,而我,总在被带和被不带的边缘,这不禁再次让我领略到大人的特权,我常常对此羡慕不已。
从前在沟子里没有鱼时,我们表兄弟姊妹也会去那沟里抓沙鳅,有一次,我们去到了那长满芭蕉的小湾里,上去,有一处无鱼的大潭,我的陆彪哥哥,一马当先,跳入潭中,用着簸箕在垂于水中的杂草一通乱搅,当时我在岸上,当他把簸箕提出水面时,却大叫一声,说:“有刺锥儿!”
我同岸上的一众凑过去看,果然,那是一坨黑色的长满针刺的球形动物,拳头大小,和板栗球极为类似,但其针刺要长些,也不知道眼睛四肢嘴巴长在何处,在陆彪哥哥手中的簸箕中,一动不动,但那绝非板栗球。
见到这稀奇物的我们“哇哇”叫个不停,华进哥哥卷起裤腿就往潭里跳了下去,嚷嚷着:“那是害鱼的东西,会把鱼搞死,拿上去弄死去。”
在我们这一群好奇地像是小猫的孩子的簇拥下,陆彪哥哥担着那簸箕上了岸,陆彪哥哥边上岸边说:“找两根棍棍来,要粗点点的,嘞东西有毒!”
听到号令的我们四散而去,我也到一旁折了两根树棍,跑回去,递给陆彪哥哥,他看了看,选了我们其中最合适的一根,一根是我的,一根是华进哥哥的,我看着陆彪哥哥和华进哥哥两兄弟小心翼翼地将那刺锥儿倒在地上,拿木棒敲打,它却一动不动,毫发无损。
“要戳,打不死的!”华进哥哥说着要抢木棍。
“要找岩头砸,我去找。”
“不稍得,戳的死,戳的死,陆彪你快戳。”
不知道是谁说的这些话,叽叽喳喳中,我只记得这些。
后来那东西还是被戳开了,里头是一滩豆腐脑似的东西,不禁让我联想到脑浆,顿生肉麻。
那东西我再也没见过,后来在科教频道看到了“海胆”这一生物,竟与那刺锥儿一模一样,这叫我疑惑不已,海胆也能入这水沟?我对此,就如同对泥鳅和沙鳅之分一样,抱以极大的怀疑。
再向小湾上游行进,是大片种着百枝树的荒地,从前的人在此处种着番薯和花生,田边有几棵桃树,是我常常攀爬的地方,在田的最里头,石头渐渐变得巨大,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爷爷曾和人商量养一群羊,那是一群可爱的不行的动物,我常常和未出远门的姑爷在这湾中放羊,我也常常想骑到羊背上,只是它们的摇摆叫我生畏,我常常在那小湾里见到许多小动物,比如松鼠一类,也有些许动物死在那里,我曾在那沟中捡到过某种动物的头骨,并像科教频道中的研究者一样,推敲着那头骨的由来。
再上去便是悬崖陡坎,枯了水的瀑布两边,除了杂乱的藤蔓和挺拔的劲松,别无它物,那松是我所不认得的,和红皮松有所不同,那是黑色的,树干浑圆,少见,和那镇上“章子面馆”墙壁上所贴的黄山壁纸中的迎客松一般,显得饱满黝黑,看着莫名的舒服。人们常常来此处砍柴,不碰那松树一分,自远看,那松枝与云雾横向架在森林中,同其中的生灵,着实达到了恰如其分的和谐。
那小湾作为支流,不多长便不见了踪影,沙湾则还需向山中长去,一路是不长草的踏得紧实的沙路,在一片绿草灌木中开辟出来,沿着水流,蜿蜒进了群山最里,在那沟的两边岭上,是一色的古松,常常出入云间,一条小路向进山左边的岭上盘绕而上,那沙山是松松垮垮的,所幸有各色绿植缠绕住,才不叫大雨剥蚀而去,我们常常随着大人砍柴进山去,那山腰有一大块缓坡,叫李子树踏,说是古人曾居住于此,而能作证的唯有山下沟中的些许石器。
那片从树木间空出的地方长满了灌木杂草,其边缘生有十几棵桃树,长满白色绒毛的桃子不足半拳大小,常常在夏日的阳光下,挂满枝头。那荒坡皆是破碎的板岩,从中长出的灌木是画眉的家园,往日爷爷来此放牛时,看见一家,后来同我说,我便同他一道去看,那是一窝住在灌木丛下苔藓上的鸟儿,我们走近时那母鸟便猛地飞出,冲我和爷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们没有理它,自顾扒开灌木,把脑袋扎进去,没有羽毛的丑陋禽类幼崽张开了它们的大嘴,朝天仰望。我伸手去拿,爷爷说:“莫拿它,一哈就死哒,它娘要磕你,莫拿它。”
我便没拿,只是扎在灌丛里看着,不久爷爷牵牛去了别处吃草,我还那样看着,它们的母亲一直都没有离开,后来它缓缓靠近,回到巢中,像是一一请点一样,磕了磕它的孩子,便蹲下闭上眼睛,又不时睁开来看看我。
那是一只稍显肥胖的棕色画眉,通体棕色外,眼上如眉白羽正是其得名之处,那是从眼睛一直延伸过颈脖的白线,在我看来,倒是像一滴眼泪,在那鸟儿飞行时,自眼中涌出,染眼周一片,再随风向后,却不似人的眉毛,同眼睛区分开来。
那地方动物不少,偶尔见刺猬松树窜动,但其沙质松软的土地却也叫钻地峰很是喜欢,夏日里我每每到那,远远可听见地下有“嗡嗡”响动,及细细查看,可见些许长了老虎脑袋的蜂虫自地洞钻出,它们对人不大感兴趣,但如果途径那片土地,踩陷一块,那最好是提起裤子跑开,离开肇事现场。
有一条小路穿过荒地,延伸向对面森林,不知去处,也无人再从中走来,我们通常沿来时小路向上,一路高松伟岸,野草也少了起来,满地枯针落叶,却显得干净不少,利利索索。
过了梨子树踏的路少了弯,径直延伸向山岭,可看到头,两边的松树安安静静。
去那岭上是累人的,但到了最高处,也就是岭上,路便只有一条,就是沿山岭一线,狗子常常快人一步,跑到山岭四处撒尿蹦跶。
在无云的天日里,常常可见两边对岭,松树干间,枝间,针间,天地显得坦坦荡荡。
岭上小路常常显得棕褐色,同两侧绿苔区分开来,那里可见些蕨类植物优雅生长在松林间,只是常被狗子撒尿调戏。
小孩子并不学大人砍柴,也四处蹦跶,但不四处撒尿。常常去大人所告知的地方寻找蜜米儿和樱桃。再则是满山遍野地采蘑菇,这事常常早有预谋,并不随机办事,在规划好线路后,孩子们便钻进了森林。
至于蘑菇的有毒与否,全凭长相认知,凡色彩鲜艳者去之,长相奇特者去之,不可食名录中者去之,这样,也便只剩下松箘可采。
我常常为松箘的美感所折服,自然,味道也是一样,它们生长的姿态着实富有傲气,伞蔓朝天伸展的样子证明了这一点。每次看到一个,采摘一个,都无不叫人享受,如同抓鱼一样,在采摘的时候,我的眼睛,却已经扫向别处,在寻求下一个了,而这一个,我已经在接近它的时候欣赏完毕。
林间偶尔见到些群野鸡飞逃,大的在前,小的在后,狗子,则在最后,每次见到此景,我们常常张牙舞爪,“刷刷”地大喊,野鸡跑地更加迅速,狗子则屁颠屁颠地跑回来,一路明明摇着尾巴,却汪汪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