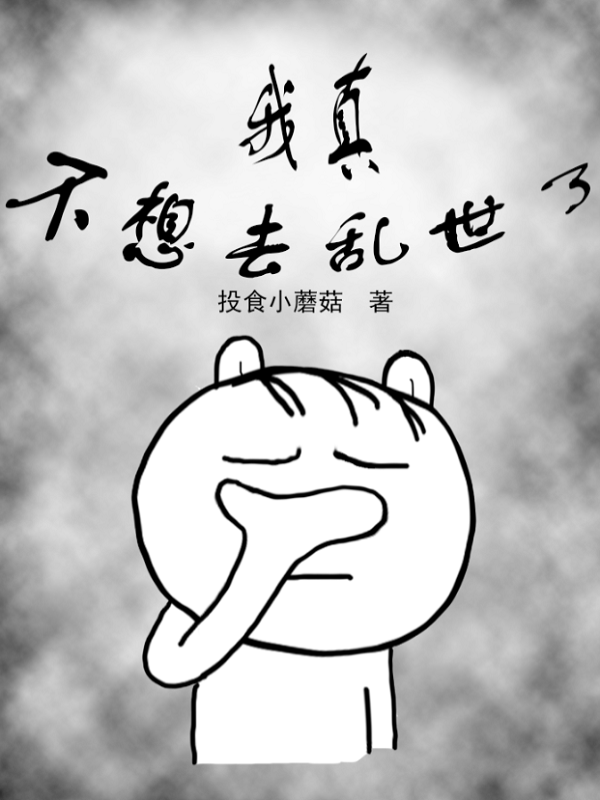大爷在我面前摆了一个拳架的起手式:双脚前后平行站着成三七步的样式,一手虚含腰胯间,一手微屈向前平举,指尖定在我抱着的护具上。
“记住,别顶,把气都放出来,别憋着气。”大爷先是嘱咐了一番,然后只见他身形一矮,后步一跟,以指化掌,把掌面贴在我胸前的护具上。
这一掌并不是击打上来,而是跟着大爷身体的形变贴靠上来的。接触的那一刻,我只觉得有一股力从大爷的掌心化开,把我包裹起来,最后在我背心合拢,把我向后拽去,直到我后背撞上了墙,那股力道才被消散掉。那一掌虽印在我前胸,却作用在我后背,那一刻的感觉并不是被人击打或者撞击,更像是感觉有人在我背后绑了一根绳子,把我猛地向后一拽,直接让我双脚离地向后飞了出去,直到后背接触到墙面,才止住这股向后倒的势头。另外,停下来之后,后背也没有明显的痛感,并不像是被人往墙上推搡,更像是自己往墙上躺倒一般。
这一掌之后,虽然没有任何损伤,我却靠着墙缓缓地瘫坐下去。因为,这种体验已经超越了我的认知。在被击飞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还留在原地,身体却被那股力道向后拽开,直到撞墙之后,灵魂才从刚刚站着的地方回归我的身体。被击飞的那一刻,我是完全无知觉,无意识的,身体所有的感官都清零,在撞击之后所有的感觉才回归。
“大爷,您是,这是个啥?”我惊魂未定,想说些什么,却语无伦次。
“起来吧。没伤着你。放心。”大爷负手而立,然后转身踱步回到酒桌做下,低瞄了一眼自己的双手,有些自嘲地喃喃说道:“几十年没动过了,看来是放下得差不多了。”
我回过神后,一个猛子从地上扎了起来,然后冲回酒桌边,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大爷,您这是啥功夫啊?这,这也,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一掌直接把我打得灵魂出窍啊!大爷,这您得教我啊!哈哈,这太厉害了啊!我说,原来电影里面那种一掌把人打飞是真的啊!太厉害了!”
“屁!”大爷不屑的啐了一口,“电影里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对对对对,您这当然是真的!是真的!”我连忙赔笑。
“像这种把人放出去的长力,没啥稀奇的。厉害的是,要把这股力留在人身体里面。”看我还只顾着开心,大爷开口把我拉了回来,“既要把人的架子打散,又要同时把人打伤,那种乾坤力才是真功夫。”
“你刚说长力,乾坤力,都是啥啊?”我有些不解。
“力,分长力,短力。其实叫法很多,也有叫长劲,短劲。叫寸劲的也有。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长力,就是能把人发放出去的力,走的是身形,身形能走通,长力就出来了。短力比较难,得把自身的筋骨练松,能配合着呼吸发力,才能把力打进人的身体。”大爷解释道,“长劲破人身形,短劲伤人于内。要能做到长短结合,随心而发,功夫就算入门了。一个动作里面能包含两种劲,乾坤相合,那才是真功夫。刚才我之所以能把你放飞出去,是因为你练过架子,本来就松,外加你没半点抵抗,我只要稍微一发力,你就出去了。没啥太稀奇的。”
“您这怎么发力,跟我还有关系?”我继续追问到。
“那是自然,你要是有抵抗,我就不能只发长力了。长力是通透的力,你不抵抗,他才能透过你的身子带着你走。你要是身上有力跟我对抗,我的长力就走不透,那就得带着点短劲进去破掉你身上的劲,才能把你放出去。今天只是让你对劲力开开窍,带着短劲伤着了就不值当。”
“那您说电影里面的那些动作?”我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是没拼过命的人乱想出来的。长劲放人,只有在对手放松的情况才可以。只要较上劲,动作里就得带上短劲。那电影里面,两个人都拉着架子,是飞不出去的。拉上架子动手,行家出手只会把你一下子打瘫咯,再把你放出去。哪有让你飞出去还能站起来的道理。”说着,大爷反手指了指自己,“我这也是几十年没真的动手了,不然也说不好,能不能控制住只用长力去放你。我那个年代出来的人,手都狠。兵荒马乱的年代,手不狠是立不住的。现在拍电影,只要一动手就能天昏地暗打上几十回合,那是表演。真的动手,出手不能有征兆,打上了就是一下,打不上就要撤,不能让人看清你的架子。两个人都把架子亮清楚了,就不好动手了。”
说起往昔的事,大爷明显是有些兴奋了,一边说着,手上也配合着动作给我演示。难得见大爷这么开心,我就把之前有的疑问全部托了出来。之前只要我问关于实战的问题,大爷总是避而不答。他说,练功要能沉下心,总想着动手,就是心里起了邪念,容易惹出事。
“大爷,为啥亮了架子就不好打了?”我问道。
“亮了架子,就有了防备。打起来就吃力了。真的动手,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招不得手,就得跑,边跑边找空挡再去攻。总之不能把自己的功架亮给对手看。亮了功架,那就是搭手,是切磋,互相较个技。跟你们现在那种擂台差不多。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搭手不会分胜负,是为了在对手身上找自己架子的不足。所以,也只有信得过的人才会搭手。若要是打擂,也是不亮架子,逮到机会就试一下,出手不留手,是死是伤就得看平时的功夫了。”大爷答道。
“那现在擂台上那些是真功夫么?咋跟您教的感觉不一样?”我继续问。
“怎么不是真功夫?上次电视上那个黑壮黑状的老外(大爷说的是我陪他看的泰森的比赛),短劲打得就很好。只不过他们那种不是拼命的功夫罢了,他们那种就是为了打给别人看的。拼命的功夫在短劲里得夹着长劲,用长劲领着身子去打短劲,这样劲才不会断。才能做到进退自如。只有身上带着长劲,在接触的时候才带开别人的架子,让短劲打得透;如果带不开别人的架子,也能裹着这股劲把自己拉开,不至于被别人伤了。不然就跟那个老黑一样,总是用短劲去破对方架子,两边硬碰硬,得纠缠上好一会。真到了危急时刻,这么纠缠变数太多。”大爷一边说,一边用个两拳头比划着。说到长劲破功架的时候,他一只手成掌,往另一只握成拳的手上一压,把握拳的手的手腕压弯,然后挺了挺被压弯的手腕,表示手腕弯了,就使不上劲了,然后以掌变拳,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敲了一下;说到把自己拉开的时候,他摊开的手掌往握拳的手拍去,但是没拍动握拳的手,拍打的手掌却随着手臂挥舞的方向划了下去,没在拳上停留,直接交错开了;说到硬碰硬,他则是双手握拳互为敲击,最后一个拳头把另一个拳头所在的手腕压弯了,然后拳头打在了另一只手的手背上。
“那按您这么说,打不过就跑,还真是个法门?”我问道。
“不然呢?站着挨打?”大爷反问道。
“这,这也有点太不光彩了吧”我表示不能接受。
“光彩?命都没了还要拿点脸面有啥用?我刚跟你讲的都是拼命的法儿。现在国家强大了,没人敢欺负咱们了,而且现在是法治社会,有警察了,也不用靠动手来讲道理了。我跟你讲的这些法儿,是希望你一辈子也用不上的。嘿嘿,不过按你说的那种光彩法,我也觉得不怎么光彩。在一群人面前互相抡拳头,最后抡下去一个,还站着的那个也是鼻青脸肿,这有啥光彩的?要真有本事,把人干趴下来,还得让所有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干的,这才叫光彩。”说到这,大爷欣然地笑了,想必是回想到了往昔的光彩。他不由得伸手去够酒杯,端到嘴边才发现没酒了。
聊得尽兴,我们都没发现,一瓶酒已经喝完。正当我打算就着这个开心的势头去开第二瓶酒的时候,大爷却摆了摆手,示意我不用开了。他说,“差不多了,今天开心,也算喝够了。这人啊,酒多了,话就多。你练了十年,也该给你留个念想了,该说的,不该说的说了一堆,后面的路得靠你自己去走。之前不说,是怕你走弯路,功夫未纯之前去动手,容易滋养心火,心火旺了,容易动邪念。你也不要怪大爷。”
“我咋会怪您呢,瞧您这话说的。以后日子长着呢,您带着我好好练。有您看着,我能出岔子么?”想到大爷对我开了口,就是要带我练真东西了,我自然满心欢喜。而且,一起走过这十年,我早把大爷当成了亲人,更加没有怪不怪这一说。
听完我的话,大爷并没有回复。他在椅子上呆坐了一会,似乎神色有些落寞。这份落寞也是一闪而过,等再起身的时候大爷爽朗的笑又回来了,他指着桌上剩下的那瓶酒说道:“这酒你收好,下次再带过来喝。”
今天这场酒喝的是收获颇丰,感觉大爷为我开了一扇门,透过那扇门,隐约已经能看到一大片宝藏。于是,我一直沉浸在大爷的话中细细品味不可自拔。只不过,我却忽略了大爷一直在用的一个词:“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