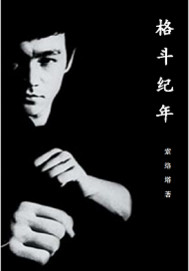由于季末害怕我的剑,我把它挂在了客厅的墙上。我们的谈话地点也改到了季末的卧房。南宫契还在我面前摆起了老冥警的派头,被我一顿猛怼也老实了许多。
说起窦茜蕾本也是个富商之女,家境殷实。它父亲为了巴结权贵把她嫁给一个侯爷的儿子,也就是秦寄善。谁料到这个秦寄善是个浪荡子,根本就没把窦茜蕾放在眼里。只是当成玩物,新鲜了几天就继续外面风流快活的日子。秦寄善还酷爱赌博,每逢输钱后都会到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家拿窦茜蕾出气。时间长了窦茜蕾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每逢回来都给他来一壶好酒。里面放些泻药或蒙汗药,根据需要控制药量。当然这种事她也不会亲自去做。平日里窦茜蕾对候府的下人都不错。谁有个什么事,都会帮一把,钱财啥的也都没少给。后来秦寄善继续他的风流日子。窦茜蕾久守空房难忍寂寞,到也觅得一个情郎。
事情是这样子的。窦茜蕾的父亲有三个染坊,五个绸缎庄和两个酒坊。窦茜蕾会经常的去酒坊给秦寄善打些刚出的好酒回来。可这次来到酒坊却看到一个皮肤白皙的男子,翘着二郎腿坐在板凳上,正一提一提从不同的缸里舀出酒来,往他那粉红色的嫩唇里送。看这男子生得俊俏,窦茜蕾不由得有点发痴。她看了半天,才回过味来。
“喂!你这么个尝法,我还卖不卖酒了。买酒欢迎,不买酒滚蛋!”
“怎么,不认识我。”那男子起身一脚踩在板凳上,掸了下紫色的衣衫。“我可是你家的大主顾,不怕生意跑喽!”他一脸坏笑的缓缓走到窦茜蕾面前托起她的下巴。“只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告辞!”说着便要向门外走去。
“喝了我的酒,就这么走了?”见这男子要走,窦茜蕾一把拽着他的胳膊说道。
这个时候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他一进门就满脸堆笑的把窦茜蕾拉到一旁小声嘀咕了一番。这中年男子是这个酒坊的坊主,跟窦茜蕾老爹好多年了。他告诉窦茜蕾这个人的确是他们家的大主顾,名叫钱冲,是飞鸢客栈的老板,而且据说和一位将军还有亲缘,故很难招惹。
“不让走,你想干嘛?”钱冲顺势一把将窦茜蕾搂在怀里,另一只手则随意挣脱,拿出身上的酒壶喝起酒来。
窦茜蕾挣扎了半天,也没从他怀里出来。“苏伯伯,把地窖中我放的那几坛好酒拿上来让钱公子尝尝。”
“那可是……”苏坊主话说到一半,被窦茜蕾打断了。
“尽管取来,我爹问了,我担着。”窦茜蕾看似欣赏般的对钱冲笑了笑。 “这下可以放开我了吧?”
钱冲这才不舍的松开了窦茜蕾。“早就听说窦老板有个漂亮的女儿,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只是便宜了那秦家小子。”
“苏伯伯,出来送下客人。看来钱公子不喜欢咱们家的酒。”
苏坊主刚把酒从酒窖拿上来,硬是愣在了原地。“在下多有冒犯,还请窦姑娘海涵。”钱冲向窦茜蕾作了个揖,又瞅了瞅苏坊主手中的酒。
“那过来吧!”窦茜蕾摆手让苏坊主把酒拿了过来,后面跟了六个人,每个人都抱着一坛酒。“这七坛酒,我想和钱公子打个赌,不知钱公子可敢否?”
“有何不敢。”钱冲看上去一脸自信的样子。
“这七坛酒存放的年份各有不同,倘若钱公子能猜出它们的年份,我双手奉上,并对其它酒给你打八五折。倘若猜不出,你进我家的酒都要付双倍的酒钱。”
七坛酒摆放整齐,钱冲一一品尝,所说年份竟与酒坊存酒年份丝毫不差。这不由得让窦茜蕾对他刮目相看。
“搬走。”钱冲一边吩咐人把酒搬走,一边不舍的盯着窦茜蕾,眼神中充满暧昧。窦茜蕾也被看得脸红起来。
“我这里还有一瓶好酒要送与公子,请与我到隔壁阁楼去取。”说着边带钱冲向外走去。苏坊主看出些端倪想要阻止,看情形也只好作罢。就这样两人有了第一次开心的接触。
娈西城的各个街道上都空无一人,西北风刮起一片片落叶携带着些许尘埃。街道上随处可见摆放着各样金帛首饰,粮食及各种日用物资。城中店铺和各家各户的门大多虚掩,有的露出个脑袋向外张望。也有大门禁闭,门外空空的。突的城东一声炮响,一个个身披重甲的骑兵随风而至。这群人的装备看似正规,实则乃是城边栖龙山的土匪。此间天下大乱,有道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官军新败,方圆几百里附近数城再次为栖龙山占据,也算得上是一方天下。这些土匪进城与一般的土匪不同。他们有秩序的清点各家送出的东西,对于不足的继续索要。对于闭门抗拒的自是要劫掠一番。像这样的每年要有三次,时人称之为“纳三税”。每家还要送出人质。即便是官军也是这个做派,百姓也习以为常了。这样先是头一拨骑兵清点财物,后一拨车队负责运往栖龙山。其间一个脚蹬长靴,身穿金甲,头戴黄色毡帽的人骑快马从人群中飞奔而过,像是有另外的意图。他身后跟了十多个亲随,在城东的一户人家停住了。大门被狠狠的一脚踹开,只见一个像是官家模样的中年男子急匆匆向后院跑去。
“窦百万,还记得四年前的承诺吗?”那人一进门就高声呐喊道,说话间长长的八字胡须也跟着一抖一抖的。
窦茜蕾她爹窦青裕听到消息从里屋出来,见到此人吓得直接就瘫坐在地上。这让他想起四年前官军攻城把栖龙山的土匪赶了出去。有一个土匪躲到了他们家,强逼他收留。此人长得浓眉大眼,身材高大,高挺的鼻梁正中还有一颗黑痣,就正是眼前此人。他一眼就相中了当时只有十六的窦茜蕾,告知有朝一日定来迎娶。
“老爹,俺叫俞远瞻,俺现在发达了,这方圆好几百里都是俺的了。快让你女儿跟俺走。”这俞远瞻看上去和窦青裕也差不多年纪,也都有个四十多岁,这口该的到比翻书还快。
“嫁给秦候爷的公子了。”窦青裕说话声音有点小,头也低着,在不停的摇着头。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曾经如丧家犬的逃匪,如今能混得这个光景。
“你说什么?”俞远瞻把窦青裕扶了起来,冲还在一旁吓得发抖的窦府官家道:“还不给你家老爷搬个椅子,你这官家怎么当的。”
俞远瞻的一个亲信附在他耳边嘀咕了一番。俞远瞻立即带人转身就走,还回头瞪了窦青裕一眼。“吩咐下去,窦府财物一律不取,回头让那个官家去做人质。”
“今日有幸一见大王光临寒舍,真是万分荣幸。快快里面请。”俞远瞻刚到秦府就见一个身穿红袍,胡子花白的老者从里面迎了出来。此人正是镇西候秦信礼。说是一个侯爷,到他这一代也就剩得百亩良田和一些房舍,空留一个头衔,已不在有昔日的荣光。
俞远瞻没有理他,直接带人冲进了院子。一声令下立刻集齐了秦府所有的人,除了女眷凡遇稍有抵抗者一律杀戮。俞远瞻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窦茜蕾,只是却挺着个肚子。
“怎么这他妈……”俞远瞻气得只想骂娘,话到一半又给收了回去。
“大王,纪半仙算过,你好像命中就该有这么个女人。”俞远瞻的一个亲随提醒道。他也确实记得半个月前纪半仙给他说过会有个孕妇来到他身边,可保他富贵永驻。听到此他不由分说走入人群抱起窦茜蕾就走,却不料被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给抓住了衣角。此人头顶一条蓝色的丝带隆起长发,肤色白皙,眼中满是血丝,紧抓着衣角以显态度决绝。
“等孩子生下来,你再……。”
秦寄善还没说完就被俞远瞻一脚踹翻在地。“给他们留一百两银子,其余的你们知道怎么做。”
“得令。”手底下十多个亲随,齐齐拱手,便开始行动,门外清点财物的人闻讯也闯了进来。在一片哭喊和砍砸声中,俞远瞻将窦茜蕾抱上马车,一路向城外方向而去。窦茜蕾几次哭闹,想跳车逃窜,都被俞远瞻给拦了下来,只在她耳边说了句:“再不听话,我杀你全家。”窦茜蕾立马安静了下来,眼眶中满是泪水,嘴上打着哆嗦,一声也不敢吭了。
“你叫窦茜蕾吧!你也别怕。既然俺说娶你,就定不会亏待与你。跟我去个地方,给你和你爹几样东西,也算是我给的彩礼。”俞远瞻见把窦茜蕾吓得不轻,便连忙安慰道,同时命令车夫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下官翟冀参见大王。”翟府门口一个翟冀翟知府穿着半拉官服跪在门外,看上去相当的恭敬。
“翟冀啊!税物准备的怎么样了?”俞远瞻一手牵着窦茜蕾,对着翟冀趾高气扬的说道。
“已准备妥帖,请大王过目。”说着翟冀就要站起身来介绍。
“谁让你站起来了吗?给我跪着,我自己看看。”俞远瞻随意翻了两下。“这东西可是有点不太够啊!”
“我的东西即是大王的东西,可随意拿取。”
“这还差不多,起来吧!知府还是你继续当,税物可是不能少的啊!”
“那是,那是。”翟冀跟在俞远瞻后面一个劲的点头。
“听说知府大人你有一件黄金貂皮,还有和田玉枕与珠玉算盘都拿出来吧!”
“这……”翟冀欲言又止。
“知道黄金貂皮是你传家宝。”说着俞远瞻抽出一个亲随的佩刀扔在地上。“我这把刀也是祖传的,给你换啦!”
翟冀表情难堪,随即又强颜欢笑捡起刀道:“好刀!好刀!东西我这就给大王取。”
黄金貂皮是貂皮中的极品,据说只有从粟特人那里才能买来。窦茜蕾出生富商世家,虽珍稀物品见过不少,而黄金貂皮还是第一次见到。当那琥珀色的貂皮披在她身上的那一刻,她看着那明亮的颜色,摸着那柔软的质地,感受着突如而来的温暖,她那委屈的心似乎屈服了。
“下官恭送大王。”打开轿帘看了一眼翟冀跪伏在地上,心想这俞远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俞远瞻留了一个心腹守在城中,自己带着窦茜蕾、人质和秦府各仆人、杂役一干人等伙同万余人押送着所掠财物一同回到了栖龙山。在栖龙山环绕间有个山谷叫龙口谷。过了龙口谷往里是一片相当大的开阔地,俨然在里面矗立着一座小城,就是当时传说中的娈右城。在城的中部有座宫殿般的建筑,被叫做凉王宫。它有着朱红色的圆柱和琉璃彩瓦,门窗雕龙画凤皆出能工巧匠之手,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居住的地方。除了要和俞远瞻同床共枕以外,仆人佣人也都是从秦府过来的人也到没什么不适应的。不久窦茜蕾便产下了一个男婴,取名冠伯。
转瞬三年,俞远瞻的地盘在这三年中愈来愈大,拓地千里有余。朝廷派人过来加封他为凉国公、镇远大将军。他也乐得接受,无非就是朝廷拉拢安抚他,利用他打击其它不顺从的势力。俞远瞻一高兴便准许窦茜蕾回娘家转转。
窦茜蕾独自走在娈西城的大街上,尽管走马灯式统治更换,娈西城还是那么的热闹非凡。拨过杂乱的人群,窦茜蕾来到自家的酒坊,看到大门紧闭,一个穿得脏兮兮的男人,一手拿着酒壶,一手使劲拍打着门,高声叫喊着,声音嘶厉听不出说的什么。才三年,没想到秦寄善就混得这副模样。
“你在这里干嘛?”
“你管我。”秦寄善一看是窦茜蕾顿时泣不成声。“茜蕾……茜蕾让他们给我一壶酒吧!我……”话还没说完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苏伯伯,开下门我是茜蕾。”
苏坊主打开门,看到秦寄善在外面,一脸嫌弃的样子。“少主,您怎么招他啊!您现在可是王妃,不是他老婆。”
“给他壶酒。”窦茜蕾用命令的口气说道。
“可是少主他半个月都没给酒钱了,而且老爷也没少给钱接济他。他现在就是个无底洞,惹不起啊!”
“我说给他壶酒!”窦茜蕾加重了语气。
“好,好,好,给他。”苏坊主摇着头很不情愿的给秦寄善打了壶酒。
“走,跟我回家。”
“没家了!没了!”秦寄善一边喝酒一边往窦茜蕾身上靠。“夫人,还是你对我好。”
“给我找辆车,把他送回秦府。”窦茜蕾躲在一边,看着倒在地上的秦寄善到有些同情。
“秦府?自从那次变故后,老侯爷就因病去了。剩得这些家产早被他败光了。去年秦府也让他卖给了一个姓吕的人,现在是吕府。
“备车,去吕府。”
窦茜蕾帮秦寄善赎回了秦府,又给了他些钱财。并告诫他:“你要是想让孩子没你这个爹,就继续作。”
“茜蕾,你可不能帮秦寄善那小子啊!”刚进家门窦青裕就急匆匆的跑过来说道。
“我心里有数,爹。”
“最后一次了,可不能再帮他了,免得大王怪罪。”
窦茜蕾点了点头。
虽然一别三年,那个人还是让窦茜蕾久久难忘。在家没呆几天她就来到了飞鸢客栈。看着在莺歌燕舞中左拥右抱的钱冲,窦茜蕾扭头就走了出去。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卖香囊,有些好奇边走过去看了一下。
“姐姐买个香袋吧!”这个小男孩长得白白胖胖的,开口一笑还露出两颗洁白的门牙,看上去相当的可爱。“俺娘锈的,放了好几种香料可香了。不信你闻闻。”说着便递过来一个。
窦茜蕾付了钱接过香囊感觉里面似乎有异物,打开一看在香料间夹着一个小纸片,上面写着:“不是不想是不敢,城南小树林见。”这一见只是干材烈火又一次燃烧起来。
栖龙山上篝火旁,俞远瞻把刚烤好的肉递给窦茜蕾一块,自己也割下一块大口大口的嚼着。突然窦茜蕾啊的一声惨叫起来。俞远瞻上前一手掐住她的脖子,像是酝酿了好久,喘着粗气道:“秦寄善,你帮他也就算了。扶不上墙的家伙,我不跟你计较。他钱冲是个什么货色,你给我戴绿帽子!”
窦茜蕾张开手一根人的小指掉落在地上。“你掐死我吧!活着没劲。冠伯也挺喜欢你,好好善待孩子。动手吧!”
“你再跟他勾搭,我就砍断他的双腿。”俞远瞻松开手恶狠狠的威胁道。
冠伯七岁那年,南凉的游牧民族犯边。俞远瞻携窦茜蕾移师娈南城。这一呆就是四年,期间生下一子,取名亚仲。后来在回师途中不慎遗失,在乱军中被践踏而死。这使得俞远瞻从此一蹶不振,疆域也大大缩水。不得已也只好和南凉缔结盟约,暂时修好。虽然后来打败南凉,一雪前耻,但终究没有摆脱颓势。
冠伯十五岁那年,北凉游牧民族来攻,进逼娈西,娈西城告急。冠伯建议俞远瞻将城中百姓转移至娈右,以少量兵力出城摆阵迎战。北凉军果然上当,还没等阵势摆好,就冲了过来,遂诈败引北凉军入城过半,关门伏兵四出,歼之。另外派娈右城精兵一万抄敌军后路,北凉军首尾不能相顾大败亏输。经此一战俞远瞻对冠伯刮目相看,更是信任有加,当做继承人对待,遂晋封冠伯为镇西候,进驻秦府,管理娈西城的大小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