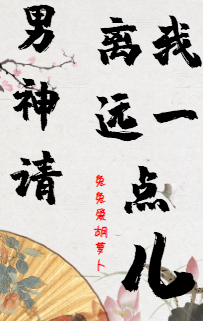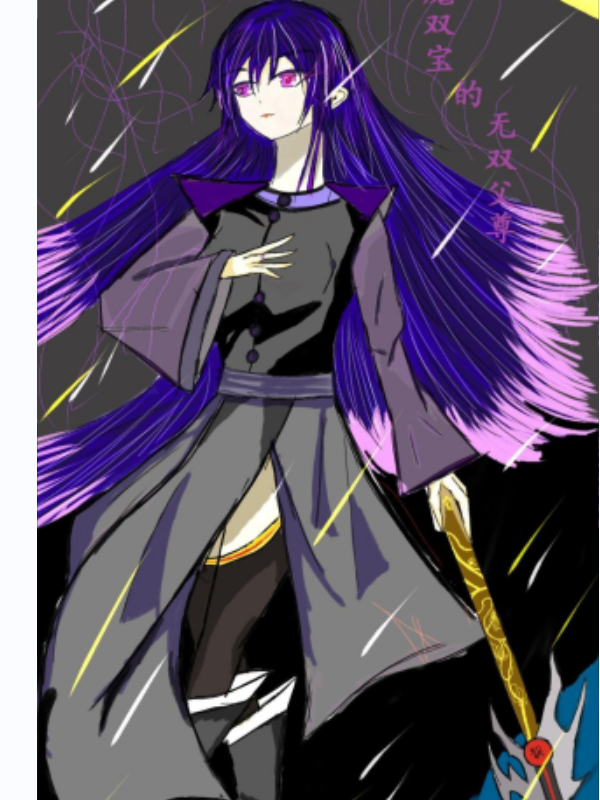孟修竹晚上听羊岭南讲解“镇岳功”的修习法门,白天或独自揣摩,或与梁闻道切磋“会群仙”的招式。自从听了中原正派与魔教的纷争始末,对这段往事更感兴趣,休息间歇,便不露痕迹地向师父套话。梁闻道年轻时便浮浪无端,又过了十几年浑浑噩噩的生活,少与外人来往,论心计筹谋怎及得上这个深沉谨慎的徒弟?将当年自己所知的情况,大半都透了出去,却没听孟修竹提起她自己知晓的半个字。
孟修竹察觉出来,师父因为师娘之死,连带着对魔教的李紫霄等人恨入骨髓,即使已经过了许多年隐居宁静的日子,仇怨之情,竟不稍减。羊岭南却怪他拘泥于私情小爱,终身不得解脱:
“冤家宜解不宜结。当年之事,确是魔教先蛊惑收编了我们的一些弟子,但大家伙杀气腾腾地奔上积圣山,扬言就此灭了六合教,也做得过分了些。大战之中,双方各有折损,谁的爹,谁的子,谁的徒弟,不都没了么?又不是单他死了老婆。这十七年来却相对平静,李紫霄蛰伏不出、纹丝不动,自顾自过他的富贵日子;李汉霄出走西北,立天狼教,除为旧怨整过一次西岭派,和咱们中原各派也无甚冲突;李崇霄流连风月场,那也不用多说。我本以为他魔教众人,和我一般都看开了,心想就当十七年前是个噩梦,大家都不去触碰,再过几十年淡忘了便是。谁知道他们竟杀了叶欢这个小姑娘,率先挑起争端。我可真是看不懂了,难道李紫霄还执着于父仇么?冤有头债有主,又为何要从叶欢开始?我老头子,还有北程家一个个的,倒还活得挺滋润。”
这番话孟修竹自然不敢学给梁闻道听。从前羊岭南也照此劝解过他,他每次一听,脾气就炸了,要死要活地发疯好几天,咬牙切齿地宣称一定要报仇,却又死守在玉女峰上不下山。这也是有理的:积圣山一战后,魔教越发加强守备,又凭着天险,真是插翅难登。就算不管不顾地去了,多半连正主李紫霄的面儿都见不着,便已去了地府。师父练了一辈子武功,怎么甘心死在一群小喽啰手里?孟修竹猜他的疯癫之症一直反复发作,就是因为满心悲苦无法排遣的缘故。
入了六月,华山上朝阳派众人开始准备奔赴太行山,参加苍岩派新掌门就任典礼一事。孟修竹接到程之遥的来信,邀她和聂兴怀在北上途中的方山一会。孟修竹一向爱独来独往,即便是门派的集体出行,也要千方百计寻个由头,避开众师伯师叔和师兄弟的大部队,独个儿先走了之。这次便也拿了程之遥的信当令箭,顺理成章向羊岭南告辞先行,走时照例操一番心,替梁闻道将玉女峰上的粮食和各种用品都打点好了。
六月初九时,行程已近冀州。孟修竹独自走在街上,盘算着今晚戌时之前,差不多能到方山。眼见前面点心铺子中转出来一个女子,头戴斗笠,还用帷幕遮了个严实,一张脸被挡得密不透风,可是老远一望,便能看出她身段窈窕,奇特的是腰间稍粗,似乎缠了好几圈粗红色的腰带。待走近几步才看清,不禁更是惊奇:那红色的却哪里是什么腰带,乃是一只火红皮毛的狐狸,身形修长,乖乖地缠在她腰间,前爪和后爪搭起来,正好绕了那女子腰围一圈,正在闭目安眠。
这女子一身丝绸衣裙虽不算华丽得惹眼,但近看却很精致,上身是纯白色,到了腰以下就从浅蓝渐变为湖蓝色,再到下摆的紫色,灵秀出尘,衬得她宛如九天下凡的仙娥。正打量间,那狐狸也正好睁开一只眼来,斜睨了孟修竹一下,又再闭上,一副懒洋洋的神气。那女子握了把剑,脚步轻巧,但是不会武功,孟修竹便想,那剑可能是她带来防身的。她一个人闲庭信步地走,遇上卖些小玩意儿的摊位,似乎和没怎么见过似的,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停下来把玩一番。
两人擦肩而过时,孟修竹闻到她身上一阵淡淡的馨香,初时似是梅花的清芬,后来萦绕在鼻端的,不知怎的竟变成了一缕勾魂摄魄的魅香。她原是不格外注重旁人相貌身材的,谁知本来已走过了那女子好几步,竟忍不住再回头仔细端详她,虽然看不见面目,但只觉这女子全身上下,处处都长得极是出众,盈盈细腰,只堪一握,腿直背挺,仪态优雅,十指纤纤,白嫩非常,只这一个背影,便让人浮想联翩,直是生平从所未遇的佳人。
孟修竹想起笑方说他姐姐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儿,心里颇不以为然,似是眼前这个女子,怕才是人间难得一见的绝色:单从身姿上来讲,不知还要生成什么样子,才能比她更美?
晚上,孟修竹自知到得迟了,说不准聂兴怀和程之遥早就打来了野味。只好满山地寻找火光,果然遥遥便望见了一道直烟,奔了过去。聂程二人坐在石头上,正在对着炭火烤野兔。聂兴怀朝程之遥笑道:“你瞧她,故意的,又来白捡便宜。”
孟修竹看聂兴怀精神气色还不错,看来叶欢之死并没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一颗心放了下来。三人有说有笑,互道别来之情。说起苍岩派更换掌门一事,都觉一般的稀奇。孟修竹没提归山途中所遇温叔一行人,聂兴怀说自己不久就回了天河山,也刻意避开了谈及叶欢逝世之后的事。只程之遥为了活跃气氛,兴冲冲地道:“上次分别,我在南程家多留了些时日,倒是看了另一桩摸不着头脑的好戏。哎,这兔子可以吃啦,外酥里嫩,谁先来尝尝?”
聂兴怀一指孟修竹:“给她吃,我先喝够酒。”孟修竹老实不客气地接过木棒,咬了一口肉,赞道:“好手艺!你说是一场怎样的好戏?”程之遥搓了搓手,“聂大哥,你带来的好酒,快给我一些。”聂兴怀掷了一只酒壶给他,顺手烤上了一只野鸡。
“之玫这小妮子,比武招亲没找到合适的人,南程家的长辈又轮番上阵,劝她打消野心思,乖乖嫁到巡抚的家里去——当时之所以讲定这门亲事,就是因为南程家太缺官场中人的支持了:虽说从我这代,他们的子弟就已经弃武从文了,但是科考的成绩却一直不尽人意。南程家搬迁到亳州这三十年来,聂大哥应该有所耳闻,一面培养族中子弟读书,一面也在任家的牵线下,做一些生意,维持开销。聂大哥回天河派以后,任家主管家业的长子任兴斌突然造访南程家,说要给他们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叫什么李公子的搭线,拜访一下程家。
“后来那李公子便带人来了,我也在一旁随着,嗬,这李公子年约二十多岁,品貌当真是万里挑一的出众,一看便是高门大户涵养出来的贵公子,真是风度翩翩,称一句谪仙下凡,绝不为过。他先表达一番歉意,冒昧来访云云,礼数周到。接着开门见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孟修竹初始听到“品貌万里挑一的出众”,立刻便想到了笑方。随即晃了晃脑袋,这是自己离开亳州后没几天发生的事情,那会儿笑方还被困在海岛的山腹中呢,绝不是他。只听程之遥接着道:“原来他是想出访一座海岛,但是恐有波折和阻挠,因此想请南程家派些身手好的子弟,随行保护——他原话当然不是这么直接,而是给南程家戴了一顶又一顶高帽,听来倒像是来求南程家庇佑,而不是给他做保镖打手的。
“那李公子还说,‘我知道南程家人才遍地,子弟如芝兰玉树生满庭阶,无论读书、习武还是做生意,自是都顺遂无碍的。只是架不住有些官员,缺乏识才的智慧,白白令好些明珠蒙尘……’言下之意,南程家子弟未曾高中,倒是主考官不识货的问题了。”
孟修竹心道,这李公子说话拐弯抹角,一句话掉三个书袋,故意卖弄才学似的,当真令人讨厌。
“这番言论立即戳到了南程家的痛处。他们原不想再卷进任何江湖纷争了,本拟一口回绝,立即送客,但这李公子将话头转到了仕进和科考,吊起了大家的胃口。于是便留他午宴,席间,他推杯换盏,大谈官商之事,妙语连珠,我瞧南程家的各位长辈,似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对他极为推崇。这一趟生意虽然没谈成,但是两家结下了情谊。你们说好笑不好笑?我从前久在云岚派习武,闲了就满江湖地飘荡,还是头一回知道,一个大家族想要立足,原来需要这么多弯弯绕绕的门道。”
聂兴怀笑了笑:“不容易,不容易,都不容易。”孟修竹发问道:“这李公子会武功么?”程之遥道:“我特意留心了,他和常人一般无异。”孟修竹眉头微皱,这李公子想要带练家子去一个海岛做什么?难道也是去找笑方的么?他又姓李,可是全然不会武功,那便不是魔教李氏兄弟了吗?
没想到聂兴怀也问了一句:“什么?他不会武功的么?他是哪里人氏?”
程之遥茫然道:“你们总不该信不过我的眼力吧,再说,南程家那许多人,也都瞧见了。他确实只是个寻常商人,讲的是官话,没有半点地方口音。至于他的个人情况,我们也没有多打听。”
聂兴怀从怀中掏出一只锦盒,打开盒盖,孟修竹见里面的红缎面上,躺着三颗皓白的野兽牙齿。聂兴怀幽幽叹道:“欢儿出事以后,众位宾客得到讯息,大多数都多留了几日,我们也趁机把新婚贺礼退还给了大家。可是有个送礼物的人,一直没露面,代他送礼的人,事发第二天一早也立即走了。这便是他送给我的。”
孟修竹眼皮一跳,脱口道:“凛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