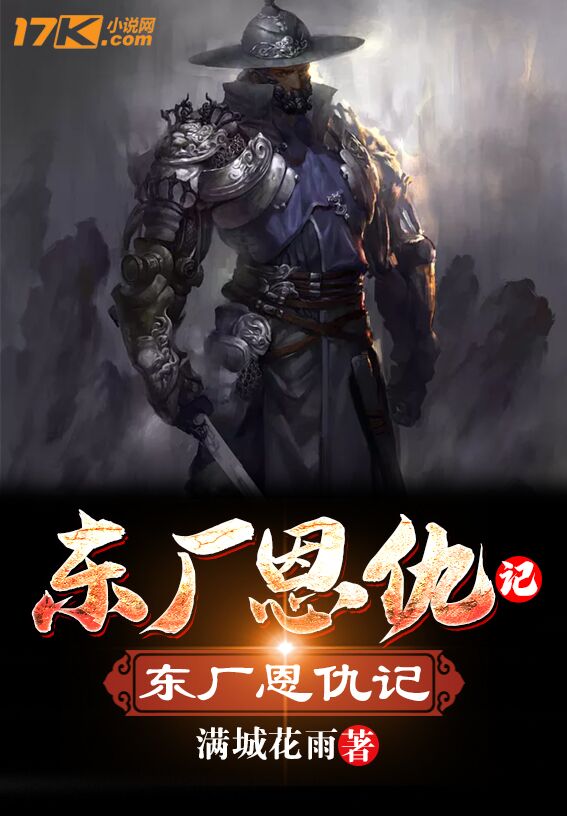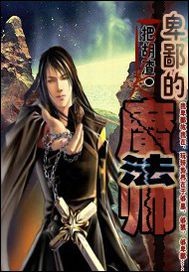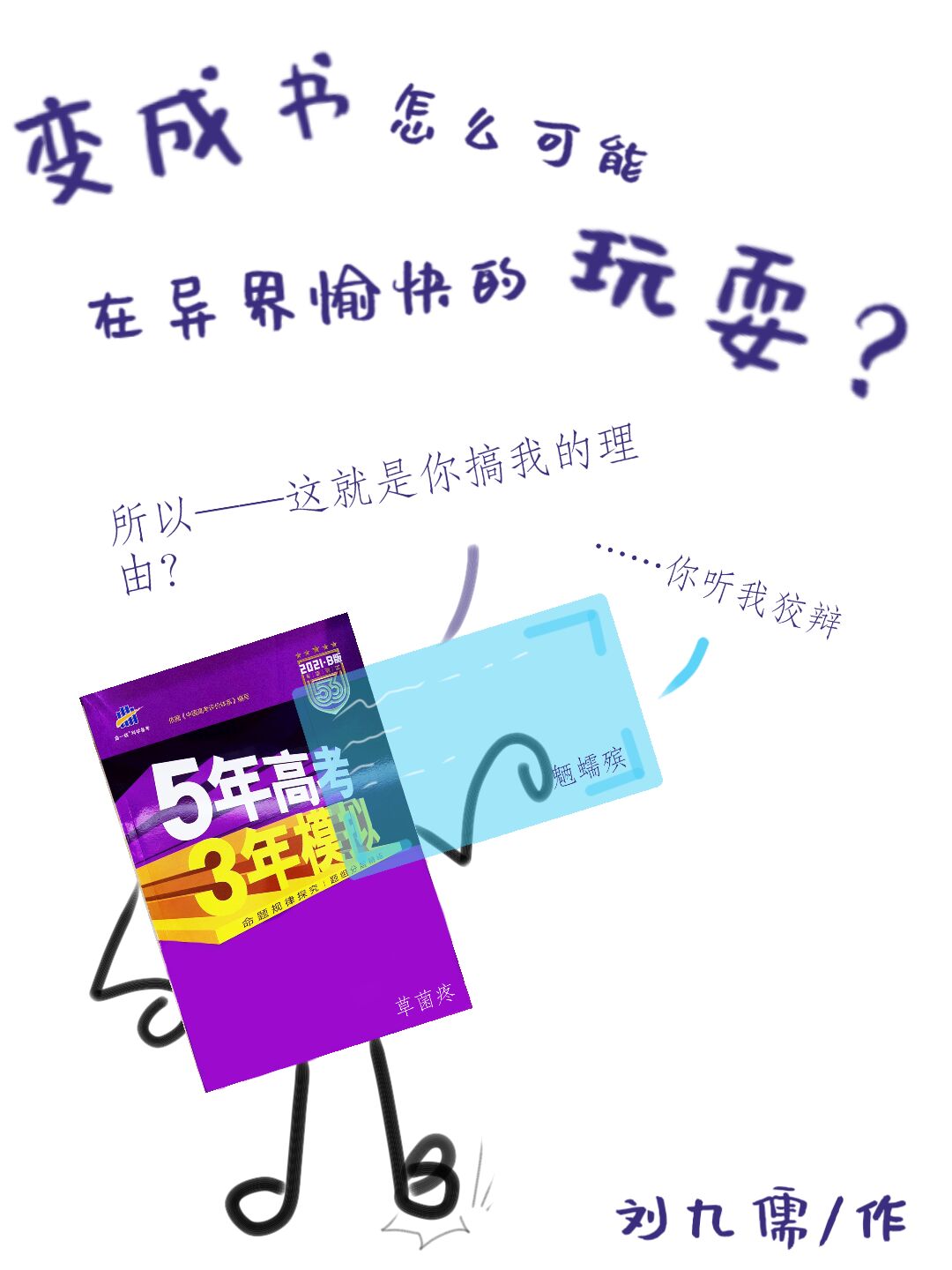登上玉女峰时,天空已显出点点星光。走入熟悉的竹林,除了微风拂动叶子的轻微“沙沙”声,孟修竹还是感到了别样的声息。
背后一剑刺来,孟修竹侧身一避,随手出剑,不等手臂完全伸开,已经变换步法,躲开了那人接连攻来的三招。拔剑出鞘,冷光映得夜里亮了一瞬,就冲这空当,已看清了来人的架势,随即沉着摆开阵仗。两人运剑奇快,昏暗中只能大体瞧出对方的轮廓,至于间隙的破绽,则仅靠听声辨招,往往剑尖递到身前数寸,才能反应过来,然后随机变化,出的每一剑,都是在死伤边缘行走,着实凶险万分。
数十招一过,孟修竹不但支撑了下来,还隐隐有劲力渐长之势。对面那人叫道:“不打了,不打了!”两人同时收剑,孟修竹跟着那人走到靠近屋棚烛火处,看清了师父梁闻道笑容满面,精神劲爽,看来的确如吴谓所说,已无甚大碍。
梁闻道捋了捋胡须,笑道:“不错,武功和应变又有长进。年轻就是好啊,老胳膊老腿比不得,要不怎么说‘拳怕少壮’呢!话说这一趟下山,你和程家的人交过手吗?我瞧你刚才这几招,不像以往那样凌厉,似乎有点儿虚虚实实的味道。”
孟修竹老老实实地答道:“我在亳州见过程家大小姐之玫的剑法,也和程之遥拆过几招。想不到就是这么一点儿经历,也没逃过师父您的法眼。”
梁闻道点点头:“倒不是我见多识广,只是对于程家的武功,我实在是太过于熟悉了。”言罢长叹一声,出了会儿神,孟修竹心中一凛,不敢接话。好在梁闻道自己调整过来,又笑问道:“程之遥那小子的武功如何?可还配得上和你齐名么?”
“灵巧有余,韧性不足。”
“灵巧有余,韧性不足!嘿嘿——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般,早早地进江湖历练,在生死场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不过说起来,这小子已经够可以了,程家的武功,这几代随着他们往仕途方向转变,讲究文雅好看的毛病是越发突出了……须知武学乃是斗技,无论练到何种境界,伤人、自保才是根本之道,一味地强调外在姿势的雅观,那是故作潇洒,将自己的命交到对手手上,这他妈不是扯淡吗?得亏他爹程见秋还是有些见识的,当年力排众议,送他去老哥们儿高秉心那学武,就是不想浪费了这小子难得的天分。”
孟修竹又把飞羽蹿上比武擂台的事说了,梁闻道哈哈一笑:“如此说来,你还得好好谢谢程之遥这小子了!想不到区区一个晚辈,也知晓了我和南程家的过节。”嘴上笑着,神情却又透出几分落寞。
孟修竹不知怎么搭腔,师徒二人又是一阵沉默。梁闻道终于忍不住了,又问她:“后来你没去南程家,是么?可曾听说那边的情况怎样?唉,当年我走的时候,这位比武招亲的程之玫大小姐好像还没出生。”
孟修竹对南程家了解不多,凭着记忆以及程之遥的介绍向他描述了一番。
“得了,这个程之玫大小姐还是乖乖地嫁到什么太守巡抚家里吧。女儿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要我是程家老爷子,无论这丫头怎么央求,我可断断不会举行这‘比武招亲’。江湖中人,漂泊四海,就算暂时安定下来,骨子里总是刻着师门的恩情,存着难凉的热血,到底不会是安安稳稳过日子的良配。”梁闻道发表了这一大串言论,原以为自己说得够了,却还是被什么东西堵在了心口,谁料身旁的徒弟久久不开口接话,终究没崩住,低声呜咽了起来。
孟修竹倒见怪不怪,只是陪着他蹲下来,沉声道:“师父,别想了。”
梁闻道哭得更厉害了:“我这辈子就没办过什么对了的事。年轻的时候浪荡江湖,游手好闲,你师祖怎么管教也不听。遇上你师娘,说离派就离派了。好嘛,既然入赘到南程家,就守着你师娘好好的吧,偏要去凑攻打魔教的热闹,你师娘抛下家里人追到积圣山的时候,已经有了孩子啦,可是她临死才告诉我……你说,我梁闻道凭什么有这么好的媳妇啊?我就不配人家死心塌地地待我好,是不是?所以老天爷要把她收回去?”
孟修竹叹道:“师娘是为了护着你,被魔教的大公子李紫霄害死的,你之后苦练武功,让我也始终记得打好根基的教训,不都是为了咱们有朝一日再遇上魔教的人,能再和他们拼上一场,保全自己、给师娘报仇么?”
梁闻道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嚷道:“你瞧你,半句哄人的话也不会说。哪像你师娘,大家闺秀,又温柔体贴,又肯陪我练剑……不过这都怪我。你是我一手带大的,人家瞧不起我,说我对朝阳派有二心,大户人家的上门女婿做不成了才又腆着脸回来求师父收留,连带着也对你不好,我又逼得你紧,教你长成了这般冷淡深沉的性子。呵,我就说我这辈子没干成过什么好事……”
“不是的,师父。我早听师祖说了,你们从积圣山回来,路过蕲州我们孟家庄,你见我前面有四个哥哥,家里实在无力供养,我连饭都吃不饱,你才应了我爹娘带我走的。我知道你一个大男人,独自把三岁的小丫头拉扯大有多难。你把一身本事毫无保留地传给我,让我能堂堂正正地行走江湖,选择过我自己的人生,不至于留在村子里,十三四岁就被随便卖了,来换哥哥们的彩礼。单是这一层,不论将来我活到几岁、死在谁的手里,我都……”
“当真?你当真没怪我?当真觉得我教你习武是对你的好处?”
“不错。”
“嗯,我也这样觉得。”
孟修竹粲然一笑,叫了一声:“师父!”
梁闻道吸溜了一下鼻子,正色道:“我也是看你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分和兴趣。其实武学之道,进无止境,能不能报仇、打败多少敌人,那都是附带着的。单说武功本身,就十分有意思啦,练得多深,从中悟到的快活就有多深。”
“是。你是大武痴,我就是小武痴。咱们互相切磋、共同进步,一齐登上武学的顶峰。”
梁闻道终于破涕为笑:“名义上我是你师父,其实咱们可是哥俩好。尤其是这些年你长大了,能替你掌门师祖分忧了,为人处世都比我要成熟得多,倒更显得我一把年纪都活在狗身上了一般。哎,你下山之前说要去参加聂兴怀和叶欢的婚礼,我还头一次想呢,要是小武痴哪天有了心上人,想要嫁出去了,我找谁比剑去啊?”
孟修竹想到聂叶二人的情缘纠葛,还有大喜之日的血溅洞房,不胜伤感,又联想起师父和师娘的阴阳相隔,深觉世间男女情爱一事,其实麻烦和痛苦远远大于欢喜和甜蜜,心下不禁升起一股悲哀。
梁闻道瞧她脸色不好看,也顺势叹道:“我一直待在玉女峰上不下去,你们河洛七豪,除你之外,其余几人我都没见过。但从前听你一一讲来,我也真心只瞧得上聂兴怀一个。这年轻人确实是人中龙凤,豪杰中的豪杰,比我多了一倍沉稳,比你多了三分潇洒。可惜叶欢这姑娘没福气,没有和他做夫妻的缘分。你也记着,要是没这缘分,还要去强凑强留,只能过刚易折,把自己原定的命数也削减了。”
他顿了一顿又续道:“哦,我忘了,你说过你只信你自己——你说是不是人一旦老了,就老是什么命啊运啊的牵扯不断?当初那股子凭着自个儿本事闯天下的劲头,和年轻一块儿,都被狗吃了。”
孟修竹截住他的话头,说了声:“师父,我一直没吃饭呢!”
“啊?你千里迢迢好不容易赶回来,你师祖只留你喝了几口茶?还好我今晚做得多了,还够给你盛一碗的。”两人走进木屋,孟修竹瞧见从小用到大的铁锅木碗,还有矮矮的小饭桌和小凳子,心中感到一片平静。
胡萝卜,扁豆,炒碎了的鸡蛋,混着米饭,一碗已热了至少两顿的大杂烩端上桌,孟修竹提起筷子,却吃得比船上的大鱼大肉还有滋味得多。梁闻道一边看着她吃饭,一边不自觉地笑着。
这几间小木屋里没有瓷碗。当年梁闻道在积圣山痛失爱妻后,回到亳州岳丈南程家,被辱骂了一通,赶出家门,差点要自暴自弃就此了断之时,昔日师父羊岭南终究不忍徒弟沦落无依,允他跟随朝阳派众人同回华山。谁知梁闻道路上就发了疯,被拖着走到蕲州的一个小村子孟家庄时,精神才略微复原。
羊岭南为了给他一点活下去的奔头,便向村里最穷的人家提出收养一个男孩,顺便也减轻他们的负担。可那家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只巴不得让他们把小女儿领走。梁闻道带着女孩儿回到华山,本来和众人一起住在朝阳峰,却遭到了师兄弟的排挤,一气之下,领着徒弟搬上了玉女峰,见峰顶有一片绿竹林,遂给徒弟取名为“修竹”,自喜还是沾了闺秀老婆的光,只因记得听她从前念过杜甫《佳人》一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梁闻道心结始终难解,疯病也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发作,有时期年才发一回,有时相隔数十天就有一次。羊岭南遍请名医也不能除,朝阳派余人倒暗赞自己有先见之明——他独个儿搬去玉女峰,即使发病也耽误不了旁人什么事。孟修竹小小年纪,却不得不早早承担起看护师父的重任。梁闻道一疯就大叫大嚷,乱摔东西,瓷碗给摔碎了十几个之后,孟修竹才想出招数,跑到山下集市的木匠铺,请师傅打了两个木碗,又陆陆续续将小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换成石头的和木制的。有时朝阳峰上的弟子瞒着羊岭南,故意偷懒不往这边送粮食,也是她顶着烈日,攀着陡峭的石阶,一袋米一袋面扛回来的。
师徒俩互相照顾,互相切磋,已经走过了十七个年头。梁闻道自三十岁的壮年男子,如今已接近知天命的年纪,孟修竹也从小小的一团,长成了英挺玉立的大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