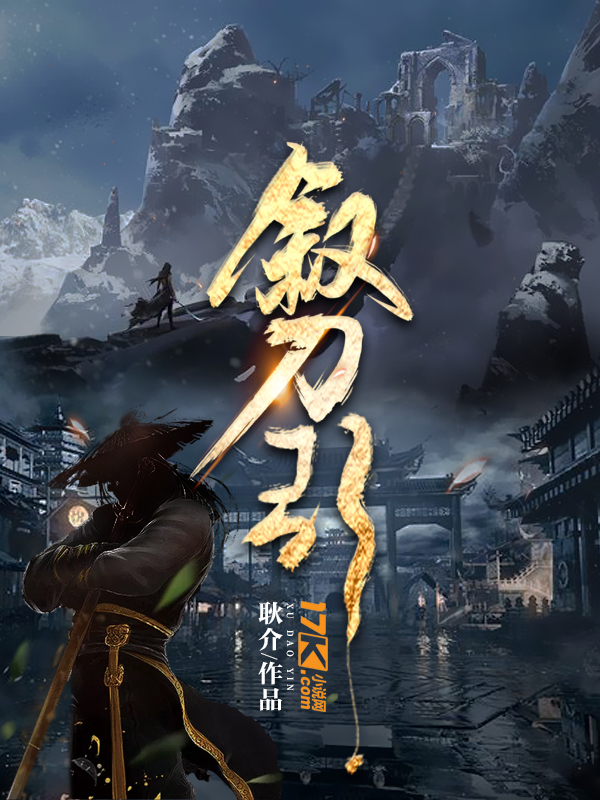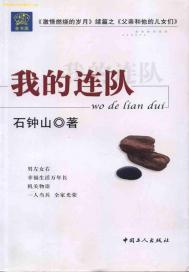华山脚下,有良田三千顷,其中大半是朝阳派的田产。南部快要进山处,有一草场,放养了大批骏马。草场入口是几间草棚,住着看管草场的萍丫头。
萍丫头的爹,原是个猎户,姓秦,因恶霸欲强娶女儿,便携女逃离家乡,三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染上了重病,临终前将女儿托给了华山朝阳派众位。姑娘留了下来,让大家都叫她萍丫头。后来萍丫头嫁给了养马的小伙,生下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可是不久,小伙也得病死了,她不愿被人当寡妇,宁肯又重新做回了孤身一人的萍丫头,只是生育后腰身变粗,再也不复少女时窈窕的身段。
孟修竹一路乘快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正巧碰见萍丫头在棚外的井中汲水,孩子坐在门口的小木凳上,吃着手指头。孟修竹老远唤了一句“萍丫头!”跃下马来。
萍丫头放下提桶,抱起孩子,笑着迎上去:“姑娘回来啦!我又是第一个知道好消息的——快上山给大伙瞧瞧吧,大家都可惦记你啦!”
孟修竹本想伸手掐掐孩子白嫩的脸蛋儿,突然想到自己握了一路缰绳,手还没洗,只好缩到背后。将马匹交给萍丫头,拾起包裹,踏上了进山的险道。
华山每座峰上山下山的路,她都走过,这条连接着山下和主峰朝阳峰的道,她更是行过无数次,每一截台阶,每一处风景,都能数出一段旧事。
来到这里之后的事,她几乎都记得。她记得自己陪吴谓师兄走下这条山路,望着他北上太行学艺的背影,久久不愿离开;记得收到他寄给掌门师祖即将回山的信后,就每天走到山门前,晃悠着等他归来;记得师父命她绑着沙袋背着剑,负重在最险峻的地方攀爬跳跃,练习身体的劲力和平衡;记得她遍求师伯师叔无果,只好自己下山寻木匠铺,给自己和师父打了两个摔不碎的木碗;记得她十三岁第一次独自闯荡江湖,把剑紧紧抱在怀里,紧张又兴奋,差点在半山腰扭到了脚踝……
对于常人来说,“华山自古一条道”,爬到陡处,如堕云端,背上汗瀑如雨,不敢扭头看一眼来路;对于孟修竹来说,却是轻轻巧巧地就登上峰顶,走进山门,穿过偌大的练武场,再经过一片小树林,就是掌门师祖清修的禅房。
一路上众弟子见到她,不甚相熟的,侧头望一眼,便继续练功;平素偶能说得上话的,就停下叫声“师姐好”。孟修竹遇上督促弟子习武的师伯师叔,也只是冲他们点点头,略尽晚辈的应有之义。只有左亦煌练剑练得满头大汗,喝水时撞上她过来,怔了一下,问道:“师姐,你总算回来啦!那帮人找过你麻烦没有?”
孟修竹回了个极淡的微笑:“不碍事。”
左亦煌挠挠头,看着师姐清瘦的背影,想多问些什么,却也知道此刻的她,是结了霜冷然挺立的竹子,不想说的话,谁也问不出别的。正待多休息一会儿,却又被自己师父莫益谦拉回去练剑了:“小子,苍岩派那边可没人向我这样逼你吧?少了苦练,哎,那就是不成,基础不牢,要吃大亏。”
孟修竹踏进掌门师祖的屋子时,就听老人家在里面朗声笑道:“来来来,一块儿尝尝我新泡的茶叶!这可是新开封的第一壶,茉莉花茶!”入眼便是银发白须的掌门师祖盘膝坐在硬床上,正往榻上矮几的茶壶里冲热水,师兄吴谓侍坐一旁,含笑望着门口的她。
孟修竹这才有了一种“回家”的踏实感,几乎一瞬便脱去了行程中艰危争斗的疲乏,欢欢喜喜地搁剑,净手,也坐到榻上,祖孙三人相视一笑,共同等着焖在壶里的茶叶,慢慢散发出沁人的清香。
不过看到眼前这把青色冰裂纹的茶壶,她自然就想起了在笑方的船上,那把不知名贵了多少的纯白色冰裂纹的壶,那想必就是师祖嘴里常常念叨的“难得一见”的官窑名品吧。
像之前每次回山,总要先来拜见师祖、述说见闻一样,孟修竹简要谈了所遇温叔一行人的行状和经历,一直说到了被迫上船、同赴海岛一节,却单单略去了见到“少爷”一事,完全把自己和他这个人相处的所有,摘出了故事之外,只说上岛之后,和温叔等人失散,未曾发现其他古怪,最后一人搭船回到了中原。
她也说不清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也许是始终因自己轻易救出并放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甚至可能和魔教有重大牵扯的人,暗中有些懊恼。她不知道讲出来,师祖会不会质问她,对待这样身份敏感的人物,怎可轻信其言、放虎归山,索性就不讲了。她想,如果以后一旦发现笑方有任何勾结魔教、危害本派的蛛丝马迹,她一定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重述一遍,决不能因自己怕担责任的一点隐晦,铸成大错。
其实她在回山的路上,已经开始留意和笑方所讲的他自己的家世相符合的消息。每到一个客栈打尖儿住店,她都要向店伴或其他商客打听,有没有女人当家的豪族商户。倒真被她问着了一家,据说北方津口的首富姜家,就是大女儿未出嫁,一手操持偌大的家业已逾十年,抚养已故的父亲姜老太爷晚年留下的几个尚还年幼的弟弟。明面上看,姜家以渡口码头货物运送起家,如今已伸手到钱庄、赌场、客栈、酒楼、药材等许多其他产业,生意遍布沿海多个港口,虽然暂时还不清楚其余的银钱来源,但这样的情况倒和笑方一行有不少吻合之处。
于是在孟修竹心中,就暂时把姜家列为了重点关注,她想,如果笑方真的是姜家的人,其实是这个疑团中,最令她放心的谜底。
孟修竹一说温叔和良叔的相貌和武功家数,师祖羊岭南一拍大腿,立刻就想起来了:“那温叔是咱们派的盛寒柏,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生得腰圆膀阔,很壮实。不过他不是我的弟子,是我三师兄的高徒。魔教积圣山绵延数百里,号称‘三峡九险十八关’,当年咱们的盟军,在行进途中就中了埋伏的,大有人在。我记得他掉下山崖的时候,我三师兄还十分痛惜,强忍着眼泪继续走了的。”想了一会儿续道:“那个良叔嘛,我就不大清楚了。毕竟那次结盟攻打积圣山,我们和苍岩派中的许多人,还是第一次见面。”
孟修竹低头沉思,暗暗把这个盛寒柏的情况和自己对温叔的所见所闻作比较,发现和笑方所说大体不差。羊岭南从枕头下摸出一封信来,搁在桌上,向孟修竹努努嘴:“前几天从太行山刚刚寄过来的,新鲜热辣。我和你大师兄,还有你几个师伯师叔捧着商议了一宿,也觉得苍岩派这次,实在过于奇怪了些。”
孟修竹怀着好奇拆开信封,见是苍岩派掌门路远写给师祖的亲笔信,除去开头问候身体康健云云,只讲了一件事:今年六月十五,苍岩派将在太行山恭候中原各大派的领袖和弟子,参与他们新任掌门人的接任典礼。至于由谁来担当下一任掌门,信中却只字未提,落款则是路远、林友得和袁述三个人共同的名字。
“什么?”孟修竹饶是心里有了准备,见到这样的消息,还是吃了一惊,分析道:“苍岩派在十七年前积圣山大战中,损失可谓惨重,掌门路远师伯这一代,当时就只余下了十来个人安然回山,到如今更是只剩了三位耆宿。飞羽这辈的新一代弟子,武功在江湖上有些名头、得到了众人认可的,只有和我们同属‘河洛七豪’的凛冬。可是他才和我一般年纪,刚刚二十岁,听说性格又孤僻,喜欢独来独往,连门派中三位长辈都难见着他,旁人更是摸不着脾气,极是不好相处。他怎能接任掌门?可若不是他,其余弟子皆名气不高,武功平平,谁又能接得起来?路远师伯、林友得师伯和袁述师叔,是突然一齐出了什么事么?正当壮年之时,怎么会早早做出这样传位的决定?可是瞧这信写得从容不迫,倒似水到渠成、早已商量好了一般,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羊岭南无奈地摇了摇头:“你提的这一连串问题,我们商议了许久,一个也答不上来。左亦煌那小子回来说,他在苍岩派住了两年,其间什么大事也没发生,更加没看出来他们要有更换掌门人的意思。只是在比武前夕,才突然得知了他们单方面取消交换弟子会武一事,由谭宗正陪着下山,去到亳州,把他交托在你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