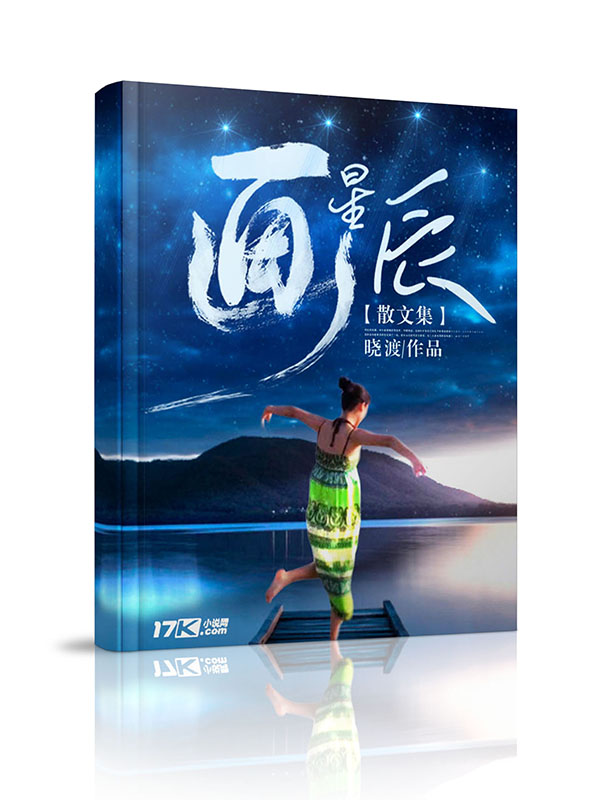孟修竹跃出那窄口,忽觉双目刺痛,立刻闭眼等了片刻,这才缓缓睁开。这时已是清晨,天光乍亮,成群的鸟儿在山林中吱吱喳喳,教人心情也为之一爽。孟修竹忽然想到,洞中那人长久待在黑暗中,白天出来怕是要暴盲。她不知去哪寻温叔,便依然沿着河流上山,打算先去山顶看看这个岛整体的情况。相较于沿山坡上来时所见的丛林密布,山顶只有一片稀疏的矮草,显得有些荒凉。
中间有一个坑洞,比寻常水井的五六倍还大,周围的草生得不太规整,似乎是被人踩出一条小道,孟修竹朝坑洞里看了看,深不见底,正想捡块石头试试深浅,一个念头突然生了出来:万一这洞便是那人在山腹中所见的开口,我这一扔石头,兴许正巧砸死了他。起身望向自己上山所走的路,虽然被密林挡住了,但估算着从那河边石缝到山顶,二三十丈的垂直距离总该有了,确实是个天然的牢笼,谁也脱困不得。
又想到:这洞若是投食之处,怎么连个看守的人都没有?绕了一周,却见坑洞旁边竖了块简陋的牌子,孟修竹伸手稍稍一掰,便将那牌子从泥土中扯了出来,见上面分作两列刻着“祈福德正神,佑风调雨顺”,又是一奇。
站起身来极目远眺,这岛四周皆是茫茫大海,一望无际。孟修竹心里一惊:温叔的船呢?揉了揉眼睛又看,海波澹澹,并无一舟一船。孟修竹虽然知道船是故意和岛隔着一段距离,但绝不至于大晴天在山顶上连远处一个小黑点都看不见,心下有些发慌,又俯视岛上的景象,见山脚下阳坡一面是一大片寻常的民居,旁边是农田,隔山相对着的阴面那一侧似乎是一些较为简陋的茅屋,占地比民居小得多了,挤挤挨挨地簇成一团。孟修竹眉头一皱:这岛上守卫的日子,怎么看起来比供养他们的农民匠人还不如?除了山下的这两片建筑,就是海边的碎石滩和山坡上连片的密林,也没看见什么岗哨、塔楼、操练场等等常见的守备要地,仿佛是一个普通的人居岛。
她正奇怪间,听到另一边传来许多人的脚步声,山顶空旷,一览无余,便匆忙躲进自己上山经过的密林中。当先是两个带刀的汉子,一个左颊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一个身材矮小。孟修竹在船上的几天,早暗中将那些护卫和船工的模样都认全了,这两个人没见过,料想是岛上的守卫。
那小个子走近坑洞,“咦”了一声,捡起地上的那块牌子道:“鹏哥,你瞧,昨夜那帮贼人连土神仙的牌位也掀了。”那刀疤脸接过牌子,重新插回土中,口中念念有词。孟修竹运起内力,才勉强听得清他说的是:“土神仙啊土神仙,那帮贼不识好歹,冲撞了你老人家又逃之夭夭,您快去和海龙王说叨说叨,下暴雨翻了他们的船,替咱死了的弟兄们报仇!”
这时又有一群人上山,却是一群农民打扮的老弱,挎着篮子,脚步沉重拖沓,看来不会武功。带刀的那两人退在一旁,冷眼看着他们走到坑洞前跪下,为首的那老汉点起白蜡,插在泥中,哑着嗓子大声道:“土神仙,咱们代表全村一百六十口人来拜你啦!这些年来,咱们五日一飨,哪有一次敢忘了你老人家?为什么还要派那些人大半夜来咱们村子闹腾呢?难道您是不满意,想要改成三天一飨么?”说着把篮子中的食物取出,一样样地抛入坑洞,一边念叨着:“多吃些吧,多吃些吧!”接着他后面的人也从篮子中取出肉类、面食、蔬菜等,扔到坑洞里。
孟修竹看得分明:这真是奇了,难道他们一直以为里面住着的是什么土神仙?简单的祭拜仪式结束,带刀的那小个子道:“行了,老家伙,今天又该你们交粮了,对吧?太阳下山之前,送到我们的茅屋那里。要是再晚了,哼哼,不如我就请土神仙尝尝人肉好不好吃?”
那群农民搀扶着下山走后,那小个子收起凶神恶煞的表情,换上一张谄媚的脸,对刀疤脸道:“鹏哥,昨晚那几个疯子抓了刀哥他们几个,非说要找什么少爷,这个破岛只有大爷,哪有什么少爷?他们不依不饶地缠闹,几乎把整个岛都翻过来了,难道这岛上真有什么秘密?是不是山里埋着宝藏呐?”刀疤脸拍了拍他脸,笑道:“你小子,净想些什么好事?咱们一群流放的犯人,待个一年半载就回去了,要是真有宝藏,哪能派咱们来守?”
“那为什么上头死命强调这个岛不许人进出?”“那帮贼不是问了么?你还问?那不过就是最初的一群人闲得慌,无聊编出来的玩笑话。不过说出去也确实有几分道理,要是没古怪,为什么不准进不准出?”他自己说着,也有点想出了神。
孟修竹见那刀疤脸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拉着小个子准备下山。“鹏哥,鹏哥?”小个子摇了摇那刀疤脸,“昨晚那些人上岛后又跑了,虽然咱们剩下的人合伙发誓绝不报给上头知道,可是被那老头儿砍死了的人怎么交待?”刀疤脸照着他脑袋拍了一巴掌,“说你没脑子,果然不错。这人想死还不容易?病死的、淹死的、摔死的、噎死的,多少种死法?等上头派人来验,尸体早烂了,还能看出来是刀砍的、剑刺的?”“鹏哥,不过这也挺好的。刀哥他们一死,您不就成弟兄们的老大了么?”“哼,当老大就一定好吗?昨晚遇见倒霉事第一个死的,不就是老大?”
两人声音渐远,终于听不见了,孟修竹一路理了理头绪,下山去海边的碎石滩转了转,找到昨夜登上小岛的暗湾,果然不见了那小舟的踪影,温叔一行,竟是走得干干净净了。在海边对着翻滚的白浪怔了一会儿,才从密林一侧回到河边的窄口,进去后,听见洞中那人靠近几步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抛下我走了。”孟修竹听他声音中满含着委屈和恐惧,知道他被囚数年不闻人声,别看表现得正常,实则精神已经濒临崩溃,心下蓦地一软,温言道:“我没抛下你,温叔可抛下我走了。”
将出去所见一一说了,补充道:“这岛上的看守只是一群在这儿流放一段日子的犯人,之后上头会接一部分回去,换上新的犯人。他们只是得到了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岛离岛,却不知为何而守,闲得久了便编出些故事,正巧被温叔得到了消息,以为你就在这个岛上。看来昨晚双方着实掰扯了好一会儿,还交过了手,你的人连村子都挨家挨户去搜了,怪不得耽误了三个多时辰。后来实在找不到你,瞧那些犯人也不像撒谎的样子,明白过来消息有误,温叔便连夜带队走了,想是又赶着去别处寻你了。”
那人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罢罢罢,他们这点头脑和我姐斗,终究差得太远。连这岛上的守卫都不知道他们守的是什么,就算又打又杀,又能审出些什么?令岛上没一人知道我的存在,却还能将我关在这里不饿死,想出个土神仙的名头,我这好姐姐可真是煞费苦心了!”
他走远几步去拿些什么东西,递过来道:“你饿不饿?刚刚上面扔下来的,我拿泉水冲过了。哈哈,难道以后真的要改成三日一飨了么?”孟修竹接过,咬了一口,尝出是个新鲜的野菜包子。
那人又道:“你也别太埋怨温叔了。一来呢,他急着赶去和其他管事碰面,到别的地方寻我,二来嘛,他对你那么客气,说不定早有人看不惯了,又料到了岛上的这些三脚猫功夫的犯人奈何不了你,这才抛下你走了的。你要是还生气,我以后替你罚他?”孟修竹无奈道:“我没生气。可是这样一来,你要怎么出去?附近即使有农家,未必也能凑起许多根长绳结起来,把你从山顶的坑洞中吊上去。”
那人哈哈笑了几声道:“这个法子看起来简单,却容易牵扯到太多人,难道要你不停敲门,去借绳子吗?本来我确是在发愁,可是我既然成了土神仙,就让他们瞧瞧神仙下凡是什么模样。”突然跳起来大叫道:“你看,今天的光来啦!”孟修竹抬眼一看,果然见到一束淡淡的光线从上方坑洞口照了进来,估摸着时辰,显然还没到日中。
那人幽幽地道:“本来呢,人应该能依据有光的时刻长短辨出是到了冬天还是夏天。可是我在这里太久了,每天见到的都是差不多的光景,今日只比明日变化那么一点儿,还怎么分辨什么时候长,什么时候短?”他颓然坐倒,又啃了半个面团道:“一开始还数着日子,每天在壁上划一道刻痕,后来就厌了,觉得做什么都无聊,中间因为心里烦、或者阴天下雨断了没数的,也再没心思去接上了。洞中日夜虚度,乾坤颠倒,真可谓不知岁月几何哉!”
孟修竹道:“现在大约是巳时,季节嘛,已经立夏了。河边的树林生得很繁盛,嗯……”她自亳州婚礼叶欢被杀之后,整个人一直浑浑噩噩的,除了想着魔教的凶手,就是考虑苍岩派的反常行径,碰上温叔一行人后,又一直小心谨慎地跟着,精神总是如此紧绷,忽然发觉已经很久没注意周遭景物的变化,因此说了几句,再去想暮春的景色是什么样的,竟尔一时语塞,说不下去了。
两人沉默了一晌,那束光慢慢下移,终于照到了洞底,只是照射的范围有限,洞里还是漆黑一片,只有那个光柱是温暖的、透亮的,中间还隐约可见细小的灰尘在光中飞舞。两人贪婪地盯着这道光,似乎怎么看也看不够,孟修竹之前从没发现日日可见的阳光竟然有这等惊心动魄的魔力,便如是上天开了一只眼。
她本来抱剑斜倚在石壁上,突然轻轻移动脚步,走到了对面,那光柱便隔在了她和那人之间。借着光,看清了对面那人正背靠石壁而坐,一条腿曲着搁在地上,两条手臂随意搭在支起来的另一条腿的膝上,着玄衣束玉带,衣衫虽微有陈旧破烂,却十分干净整洁,头发长而散乱,满脸虬髯,双眼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