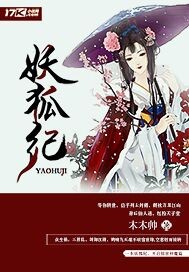知儿————!
凄厉的嚎叫声震动了整个山峰,把山顶上方的厚厚云层撕开了一道大大的裂口。裂口中,如墨的黑暗里面,有几点闪亮的星光。
银亮的星儿还未来得及眨眼,又被疾速合拢的厚云挡在了天外。
血战中,年轻的将军铠甲早已四分五裂,不知碎在何处。如血衣着身的复仇使者,手握金光耀眼的黄金&弓,黄金之箭发出几近白炽的光芒满弓而发。
伏在丈夫身上的女子,真元离散之时,渺渺迷离的光晕中,有一个美丽的指环从女子身上所散发出的光辉中凝聚成形,炫出七彩颜色,缓缓飞离女子身体,飞向虚空之门。
指环触到虚空之门的框内虚空的时刻,虚空之门突起肉眼可见的虚空波动,指环无息没入其中,虚空之门随即爆闪出刺目白光。
之后白光渐渐息暗,波动渐渐平息,终又复于平静,重归虚空。
门没有拒绝她,接受了她。
有歌声从门的另一边传出,美妙悦耳。
美妙的歌声中,有一道金色的光芒飞向将军的对手。他伸手,却不是要打落那只黄金之箭。
他伸手抓向那飞往另一个世界的指环。身子却僵在了原处,黄金之箭贯穿了他的胸膛心跳的地方。
他的口中发出的最后一个字尾音拖得好长,仿佛绝望的呼号。
耳中传来美妙的歌声,不似人的口中所发出的杂音。那美歌者,……好像虹灵。
金芒渐淡,金箭化为晶尘,无声弥散在沉闷的空气中。
这一幕,是王后所看到的生死相搏,三成三的结果……
天地间的某处。
一个女子倚靠着门框,头枕着门框的棱边。美丽双眸中,晶光微黯。似有深深的哀怨,似在深深地期盼和思念。
远方的人儿啊,你何时回家?
有一个女子,孤枕难眠……
你的笑,如蜜甜入心底;
你发怒时的表情是那么英俊;
你的坏是一那个女子开心的密钥;
你常常弄疼她,痛到她咬住你的肩膀,可是她没有拒绝你的力量,那是她快乐的源泉。因此,她喜欢上了夜的美。
她想你,好想好想。所以,她恨你。
哥,回来吧,
回来吧……
无论你在天的哪一边,
妹妹在家等着你……
……
银河的另一条旋臂的边缘。
有一道存在而又不存在的金白光芒从何处发出。在亿万星辰中执着穿梭。向着七万光年的远方。
远方,有一个女子,枕靠门边,还在等着自己的哥哥。
七万年的旅程,可否换回你不变的容颜?
七万年的等待,你,是否还在原来的地方?
那只射穿仿佛永远无法穿透的铅云,又射穿银河的黄金之箭,七万年之后,会落在你的脚边。
濯绫,箭身上有你的名字,当你看到那两个字,会否认出我……
……
迷多把越离和他的妻子送到公主身边。这样,公主便不再寂寞。那一个美丽的指环戴在公主的无名指上,这样,她再不可以属于别人。
何处传来美妙的歌声?……
是虹灵。愿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公主,和她的心上人……
国王没有治罪梭连?伦,数年后,首相与第二副首相谋逆成功,第一副首相被送上断头台。第二副首相坐上王位。首相继续担任王的首相,与侍立在先王座下一样,只是不再有副首相。
梭连?伦带着王和王后逃出王宫,不知去向。
迷多和密儿,娜丝迪、还有瓦加依,守在公主的宫殿外拼死抵抗,只为守护画中人。直到耗尽最后一滴真气和法力。
蜂涌而上的叛逆者把四个连自尽的气力也没有的女子凌&辱至死,仍还不肯甘休,就像被仇恨和恶欲支配了的污鬼,仿佛无休止地疯狂抢食着再没有声息的纯洁躯体……
王宫大换血,先王的宫中所有人都被斩首,或者被允作军妓。
先王所有遗存下来的东西都被新王收聚起来付之一炬。
只有一幅美人图画被保留了下来,那是一双美丽的女子背影。新王数次想要毁掉那幅画,却每每举棋难定,无论如何说服了自己,每次偏偏要亲自动手。然他就像被画中人惑乱了心志一般,终究没有办法下得去手。他因此迷恋上了这幅画,逐渐沉迷,最终深溺其中而无法自拔,以致雄心日萎,终于无心朝政疆土。
敌国趁机崛起。某年,某月,某日,覆灭了奇异国,进驻这美轮美奂的王宫。
攻入王的寝宫时,王正久坐榻前,对画失魂。王被一剑斩首,死时双目迷离,目中光亮渐黯,只是光中无神,就好像,他多年前的某一天就已经死了。
新王入主宝座,除陈入新。先王的首相被净身,仍侍立在王的身边。
先王的一切都被除灭净尽;唯有有先王的一幅画,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新的国王面对画中女子那一双美丽的背影,举棋不定。他下不了决心……
……
连续的时间线上。
慕容蝶语有了身孕。宇日逐星不得不把她送到她的母亲身边。
女儿出现在母亲面前。出于母性的本能,她把目光移向女儿的小腹。纤柔的腰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可直觉告诉她,今时,已有所不同。目光再次移向女儿的脸时,里面的温柔已更浓了几分。就像一个母亲,深情地望着怀中吮乳的小婴儿。
慕容蝶语再受不了母亲眼睛里面的柔光,默默无声地投进母亲的怀抱。
这一刻,她又成了母亲怀中的小婴儿。宇日逐星默然站立在一旁,不敢出言打扰,也不敢弄出什么动静。……那是对一个母亲温柔泪水的亵渎。
这一刻,他甚至不敢在脑中想自己的妹妹。那将是对她无言的伤害。他的目光忠实地移向妻子的后背,迫使他的心不得不柔和下来。
双刀姑娘没有来示威,她不在。或者,她还没有回来。
慕容蝶语狠不下心把他留下来,也不忍心把他留下来。尽管,她什么都不必说。
夜幕下,夜风微凉。夔啸山顶撒满白月光。
慕容蝶语和她的丈夫并肩站在月崖边,默默无言。
原本,她可以靠在他的怀里。他应该把妻子横抱在自己的胸口。她没有这么做,也没要他这么做。那会成为他的牵绊,会把他的心跌得粉碎。
慕容蝶语不自觉地把手护在自己的小腹上,轻声对他说:“你去吧,有我娘在,没关系的”
宇日逐星听出妻子声音中的决然与不舍,他却不知道该对自己的妻子说些什么。他不敢转身拥抱自己的妻子,甚至不敢转头看她一眼。
慕容蝶语好怕,好怕丈夫会突然转过身来抱着自己。好想,好想丈夫会突然转过身来抱着自己。好怕他会突然离去,这样,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好像就此变成了一个不真实的梦。
月光之下划出一道白色亮线。
宇日逐星走了,突然飞离而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却带走了她好多东西。他没有说对不起。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不配……
……
数月之后,宇日逐星再回到夔啸山。
慕容蝶语的身孕渐重。这一次,她的丈夫不得不留下来陪她。她没再坚持,因为他定了心意,而她,真的渴望他能陪在身边。她需要他,陪在自己身边。
黑夜已深,山中幽静,夜鸮幽远孤鸣。
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眉头紧皱,身子一阵阵抽动,汗水已湿透衣衫。
慕容蝶语躺在他身边,只能眼睁睁看着,却什么也做不了。
那痛苦,属于他,若是没了,他就死了……
一次又一次,慕容蝶语的心,被那漫漫长夜撕碎,千万次的问,为什么?为什么让我遇见你?……
可是,又如何忍心说于他听。
相遇,是缘。
痛苦告诉我,我还活着。
肚子里还有一个你,但愿多年以后,他不会遇见一位落难的姑娘。或者,她,不再被人救起 ……
我用尽半生的温柔
改变了你的心
却解摸不到你的灵魂
我将生命和它的美托付给你
伤了自己的心
仍不曾后悔
如果可以重来
我愿成为你的路人
擦肩而过
再不会走进那扇门
今生有终
终如烟云消散
我知道
来世
已是永恒……
已是清晨,慕容蝶语还没有醒来。伊人憔悴,因为有泪痕。一只小手护着小腹,不知里面有个小小的谁。
宇日逐星跪在床边,双手捧着她的一只手,轻柔地亲吻着。
“难为你了……”,他说。
声音细不可闻,不知何时,泪已悄然滑落……
从何时起,一只温柔的小手,为他抚去脸上的泪水,“难为你了……”慕容蝶语睁开眼睛,默默凝望着他的脸,轻声对他说。
声音之轻,轻如耳语。
……
慕容蝶语临盆。
宇日逐星坐在床边,双手紧紧握住她的一只小手。她的手死死地攥住丈夫的拇指,攥得他生疼。赤着身子的妻子浑身都是汗水,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而曾经生下她的母亲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承受着那份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痛苦,什么也做不了。
她以为自己可以强忍着疼痛把孩子生下来,免得丈夫心疼难受。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不要!……啊!不要——!”她再也承受不了那产难的苦楚,大声号叫起来。
宇日逐星心中绞痛,把妻子的头抱进怀里,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使她稍稍好过一点。
“救我!……求求你!……救我!……啊——!”她胡乱叫喊着,剧痛使她彻底丧失了承受能力。宇日逐星心里大大地慌乱,眼看着母亲在妻子分开的双腿间忙碌着,却看不出她到底在做些什么。
剧痛之下慕容蝶语把自己的手臂塞向自己张大了的小嘴里。疼痛使她狠狠地咬了下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
下身的痛楚似乎稍稍分摊到了口中一点点,于是她死死咬住那只手,渴望着那无法忍受的痛苦能从嘴里传导出去,哪怕一点点也好。
她的嘴里因为有了堵塞物,只能发出‘唔唔’的哭声。
“看到她了,用力呀丫头!”
母亲的鼓励让她一惊,一瞬间脑海里面闪过一个小婴儿的模样,下意识里她吐出口中的那之手,才发现那只被她咬出血来的手不是自己的。一闪而过的甜蜜突然加添了些许气力。她张大了小嘴,叫直了声音,使出了全身上下每一寸地方所蓄积着的力气。
一股无孔不入的极痛袭遍全身,她几近昏厥。再不敢用力,她大口大口地往外呼气,想把身上的痛苦都从嘴里吹出去。可是无济于事。
凌乱的头发缕缕贴面,显出一种邋遢的美。撕裂的疼痛让她恼火万分。
“娘是大骗子!大骗子!”她呜呜大哭,转而捶打丈夫胸口,“ 你无耻!你坏蛋!大坏……啊!啊……”
又一波剧痛来袭,迫使她住了口。堵塞物重新回到嘴里,那股剧痛又有了些许转嫁的门路。
无意之中,她从丈夫的目光中捕捉到了异样的痛楚。那一份深不见底的痛楚,一下子抵消了她身体正在遭受的苦楚。
她仿佛在另一个时空中读懂了丈夫眼中的痛,那一个极短的时刻里,丈夫眼中深深的痛,在她的眼中,转化成深深的恨意。
痛有多深,恨会更深!
她想要吐出丈夫的手,可那只手塞得太紧。她抓住丈夫的那只手,想要扯开。剧痛袭来,除了牙齿上还能用力,肢体上根本使不上半分气力。
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再不是因为疼痛。那疼痛仿佛变得可以忍受,她痛苦呻&吟,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强烈的恨意扯裂了她的心,有血从她的齿间流进嘴里。
那血,是亏欠的味道。深深的亏欠……
哇!哇…… 婴儿呱呱出世。在一个母亲恨意满满的坚强中。
宇日逐星本能地为妻子擦拭汗水,她却推开了他的手。她原以为自己可以理解他,可是她失败了……
母亲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女儿搂着她自己的孩子昏昏沉沉地睡着。宇日逐星只能站在床边稍远的地方,呆呆地望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目光中充塞着痛苦和复杂的情绪。
触手可及的妻子变得好遥远,遥远到遥不可及……
母亲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又重新把目光投注在女儿和她的孩子身上。她伸手理了一下女儿鬓边的发丝,低头亲吻女儿的脸颊。
夜已沉默,女儿还在沉睡。那小婴儿好像醒着,正闭着眼睛吃饭。
也不知这小家伙的眼睛是大还是小。坐在床沿上的母亲这般想着,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女儿的脸。
小孩子的父亲还在原处站着,没有动,也没敢动。他已无所适从,又不敢擅动。视线也不敢长时间停留在妻子身上。
长夜,是一口烹煮人心的大锅,锅下架满了烈焰熊熊的劈柴。这一个仿佛独立于时空之内而又在时空之外的密闭时空中,时间蜗行,几乎完全停止运行。可是作用在身心上的痛苦煎熬却像加速了时间进程一般,那强烈的程度呈指数倍不断增长,而那飞速流逝的时间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然那永远看不到尽头的时间,相对于身心的痛苦,却又像静止了一般,让人在渺茫的希望中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处不断抓狂。
天,亮了……
他不知道天已经亮了,他已适应了光线明暗的自然调节。天为什么会亮呢?天亮的意义在哪里?天是为谁亮的?日头出来,到底是为照在谁的身上?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到底该做什么?
我到底该怎样活下去?
我到底应不应该活下去?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他千万次地问自己,对着自己的深心,问着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的不同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的问题。也许,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承载着一座山。也许,他的心底深处有一个黑渊,源源无息地向外喷涌着痛苦的泉源。
别问‘我是谁’?也许,痛苦是你的名字。而你,就是痛苦的实体。
慕容蝶语的母亲起身走到他面前,示意他尽上做丈夫的本分,便错身出到门外为女儿预备身体所需。
宇日逐星犹豫着移步向前,却发现身体已僵硬得像被弃置了千年的铁人。四肢已经不受意念支配。就好像这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适应了好一会儿,酸麻的身体才慢慢协调。
来到床边,他踌躇着伸手,想要摸着床沿坐下。
“出去”慕容蝶语背对着他,冰冷地说。
他的身子一僵,小意地继续把手伸向床沿。企图以此抛却自尊的举动,看她会否因此便不忍心……
“出去!”慕容蝶语的声音尖细而冷厉,似还带着哭腔。那一股强烈的流露出来的怨恨情绪,像极了一个被丈夫背叛了的痴情女子。
他听出了这两字里面的决绝。
转身前,他的目光被小婴儿的微小动作吸引了一下。这小家伙的小手还没有鸡爪子大呢。突生的怪念促使他的唇角不自禁地翘了一下。就像是谁在自己灼痛的伤口上轻柔地涂抹上了一指冰凉的药膏。
他看不出这小孩儿像谁。或许像她的母亲,却又看不出哪里像。他不敢想是不是像自己,怕惹动妻子的怒气。他也没办法想象,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虽然他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儿。
这一丁点儿的小东西把他的心揪痛了。妻子赤&裸着身子,薄薄的被子盖住了她的下半身,只显出美丽的曲线。妻子嫩白的背仿佛放射出不可亵渎的灼烈刺目的白光。他畏惧那白光,对那白光的敬畏迫使他不由自主地把脸转向门口的方向。他僵硬地逃出门外,躲在门侧白光照射不到了地方。
好多会儿,慕容蝶语的母亲从另一侧走近房门,手上端着些东西。她住脚,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婿,欲言又止。她感觉这小子就像是被人嚼干了水分的甘蔗渣,一脸的灰败,如同人得了不治的病症。甚至在潜意识中,她大胆地预言:这小子终有一天会死在这未知之症上。这让她心里好不舒服,也非常担忧。
他垂头耷脑地就那么杵着,没有注意到她已一脚跨进门内。
一声叹息从门内飘出,飘过他的身侧,飘散在山野风中。
“娘~”一声委屈的呼唤传入门外之人的耳中。
慕容蝶语伏在母亲怀里呜呜哭泣,哭的好伤心。
母亲坐在床边,把女儿搂在怀里,轻柔着手给女儿擦拭脸上的泪水,不住地亲吻她的额头。
“傻丫头,可不能哭坏了身子,不然这小家伙可就没饭吃了”母亲任由女儿哭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忍不住说道。
“没饭吃才好!”女儿转头看了一眼安稳睡在身侧的小东西,手背抹着眼泪,嘴厥得老高。不过她的眼睛出卖了她,那一双略带惊慌之色的眼睛好像在说:娘是跟你说着玩的,你可不要当真啊!
那一个娘字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说出了‘口’,那感觉突然变得有些陌生,甜丝丝的,带出好些喜悦,像一股温润的水流,涓涓而来,冲淡了好多好多的恨意。
娘也懒得揭她,就让她撒撒胸中的闷火也好。
“喝汤吧,一会儿就凉了”母亲对腻在怀中的女儿催促道。
“娘~”女儿压低着声音唤道。
“做什么?”母亲微微皱眉,不知她贼兮兮地张着一双水灵大眼,到底想要干么。
“我要吃奶”不等母亲有所反应,女儿便开始伸手扒扯她的胸襟。
“做什么!”母亲惊慌失措,一把攥住女儿小手,慌慌张张地转头看向门外,“要不要脸了你!”惊魂难定中,一颗心几乎跳出了嗓子眼儿。也不知那门外的家伙听到没有,但愿这小子耳背,什么也没听着。
母亲慌了神,想要逃离魔爪。
“我饿!”女儿不依不饶,继续手上动作。
“不要脸呀你”母亲极力压低着声音嗔骂,死攥着胸口衣襟,注意力却都集中到了门外。她感觉身上的衣物都被女儿给扯了下来,而门外那家伙的眼睛却好像隔着屋墙也能透视进来。脸上一阵阵发烧,定是红了。
那小子千万别这个时候突然闯进来。
胳膊没拧过大腿。娘是那只无助的,螳臂般纤细的小胳膊。
她的脸红得像未来的晚霞,非因女儿,实是门外还站着一个,……一个男人。她羞到不敢睁眼,敏锐地觉察到那无声而来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沉闷的紧张气氛,几令她喘不过气来。
她根本就忆不起曾经给女儿喂奶时自己的身子到底是什么感觉,反正不是,……这种感觉。
还好女儿不是太坏,生涩地啯了几口,也没吃到奶水。忽觉意味索然便放弃了。她如获大赦,慌张着理整被女儿扯乱的内衣。一时流下委屈的泪来。
“你不要脸,……呜呜,欺负人……呜呜”她抹着眼泪呜呜地哭着,像一个被人欺负了的小姑娘。女儿还在怀中,她没舍得把这坏坏的小东西推开,许是怕摔着她。
“人家哪有嘛?好了好了,别哭了”女儿给她擦了几下眼泪,“娘喂我喝汤吧”她笑嬉嬉地说。
她轻轻把女儿推离自己的身子,抹了两把残泪。起身给女儿盛汤。
慕容蝶语深情地望着眼前忙碌着的女子的背影,听着她那美妙的屈声。一时忘记:这一个美丽的女子,是我的女儿,还是我的娘亲?
母亲盛了汤,端到女儿脸前。她习惯性地把盛满汤的小木勺回撤到自己唇边,试了下汤温。稍稍有点烫,她轻轻吹了两下,把勺送到女儿嘴边。
人总是习惯遗忘,可是为什么,许多年前的习惯性动作,却是那般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明明已模糊了喂她的情景,可当那久远的时空情景再现时,自己却仿佛还在那时空当中,并未曾离开过。
女儿一边乖巧张嘴,一边扑闪着蝶儿一般的长长睫羽傻兮兮地盯着母亲的脸。并不担心那汤会不会烫着自己。
“娘是不是有眼屎啊”
“娘~!人家在喝汤呢!”
“那你自己来吧”
女儿嘤嘤呢呢地扭着身子,十二分的不乐意,好像另一个时空中的小小的自己。
门外的那个人,还在原来的时空,不知快乐为何物……
“她让你进去”慕容蝶语的母亲跨出门外,对他说了一声便去了。
宇日逐星勉强抿了一下唇角,对她微低了下头便转身进到屋内。他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她还是恨他的,至少她是如此这般对自己说的。而且还是重复不断地在提醒着自己。
他站到床边时,那小东西就哇哇地醒来,才睡了不大一会儿。约摸着又饿了。妻子抱起那个小不点儿喂奶,一双眼睛就盯着丈夫的脸,寒光闪啊闪的,就是脖子仰得有点儿酸。
宇日逐星知道妻子在说什么,双膝跪在脚踏上。不管怎样,至少妻子平视着他,脖子会好受些。
慕容蝶语说服自己扬起手,哪怕只打他一个耳光也好。就一个耳光,就一个……
终于,妻子的手落在丈夫的脸上。无声无息地落在他的脸上,好像一个痴情女子恨意绵绵的吻。
“为什么”她说。和她一同说话的,还有她的眼泪。
明明知道为什么,可她还是问了。
他没办法回答,所有的回答都是错误的答案。
“你就不能假装眼里看到的是我吗?”
“至少在我最痛苦的时候,……骗骗我”慕容蝶语再说不下去,伤心地低声哭泣。为了怀中的孩子,她苦苦忍受着心中的伤痛。
丈夫抓住妻子无力垂落的手,重新贴回脸上。妻子不忍心再看丈夫写满了深深亏欠的脸,把头侧向一边。
妻子的心孤单无助地流着血和水。他除了起身抱她,还能为她做什么。
他坐在床上,妻子躺在他的怀里,妻子的怀里躺着一个小东西。小东西很乖,吃饱了就睡。
“他长的好像你”妻子幽怨地说道。她的眼睛审视般地注目在那张小小的脸蛋儿上,眼中尽都是温柔和甜蜜。与之相逆,她的心又开始阵痛,就像产前宫缩,她下意识地把两种痛混淆了,才发现仍然很不一样。心里的痛,更绵长,也更深沉。
产难的痛,让她在恐惧中渴望生命。而心里的痛,却让她在绝望中只想要得到安息。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她的痛,……是完整的了。
女子的母亲倚靠在门外的墙壁上,脸上流淌着两道温热的清泪。她在偷听,或者偷窥。她的心,就是女儿的家。她没有力量思想智者的哲学。她只是一个母亲,她不要去想什么德与行的问题,她只要做这坏坏的小东西的母亲。这丫头,总也不让她省心……
当时间仿佛已经静止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所处的时空会变得无限大,无边无际,永远也看不到尽头。可是时间,终究是相对存在的一个所谓的维度而已。在永恒中,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存在过的存在而存在的没有实质的虚空的存在罢了。只是人的非永恒性赋予了它相对存在的实质。而非永恒性的本质,又注定了相对存在的虚空性。唯有虚空中的数学运算,永远不会产生增效。或者什么都不会产生。作用在虚空中的数学结构和运算模型,看似有了结果。终究不过是欺骗自己和别人灵魂的仿佛艰深晦涩而又玄奥难懂的虚空把戏而已。
心的痛,好难承受,因为你还在相对的存在中存在。那痛仿佛永恒不灭,但是它总会成为过去,变成一场虚空。
数月之后,小家伙断了奶。慕容蝶语把他交在母亲手中。她要和丈夫一起走。去寻找他的妹妹。丈夫愿意放弃,留下来陪她。她不愿意。
她宁愿陪着丈夫在痛苦中活着,也不要他在痛苦中等死。
她割舍下自己的骨肉,如同把自己凌迟。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的自私都是美丽的,美到不容亵渎。
母亲怀里抱着女儿的儿子。原本,她以为他是个女孩。见面时才知道这小家伙是一只小茶壶。就像远古时候人们用来烧水的茶炉,那下面安装了一个小小的水龙头。
慕容蝶语又回到丈夫的背上,就好像从未曾下来过。她向着还在眼前的小家伙挥手告别。可那小家伙就是不肯哭,还叽叽地尖细着声儿大笑。
她好想大哭,可这没良心的小坏蛋还在笑。她又急又气,真想把这小坏蛋的小屁股揍成两瓣。
“去吧”母亲抚摸着小孩儿的小脑袋瓜,让他靠在自己的颈边睡着了。
“娘,你好狠!”听到这两个字,女儿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恸恸地哭泣起来。
远天升起一道白光。
白光中,妻子啃着丈夫的肩膀呜呜痛哭。她想念自己的孩子,好想好想。就像母亲想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