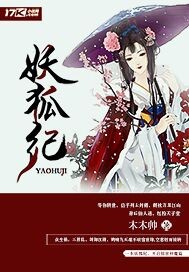奇异之国,七彩虹。
白云绵绵,如丝如絮。如七彩虹山的围巾。
山巅云端,不再有虹灵的身影。七彩虹还穿着那件以翠绿为主题的彩衣。有一条小溪从山脚好远好远的远端流过,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就像在唱着一首永远也唱不完的优美旋律。那旋律无限,永不循环。溪边有一棵彩虹小树,她每天都会换一件不同主题的彩衣。因为曾经有一个姑娘因此而喜欢和她在一起。
有一个姑娘,穿着一件在王宫中从不曾穿过的,与彩虹小树同款的彩衣。坐在彩虹小树的七彩树荫下,双手抱膝,头埋在双膝间低泣。
好久好久,小溪还在唱着那叮叮咚咚的歌,彩衣姑娘还在低低哭泣。她的背后,是公主的七彩虹。
有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站在她的身后,几番伸手,想要握住她的肩膀。不知怎地,他犹豫了,一次又一次地,慢慢缩回伸出的手。
多少个日日夜夜。彩衣女子坐在彩虹小树下哭泣。多少个日日夜夜,男子望着她颤抖着的肩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承受着内心的撕扯。他眼中的憎恨日益浓重,好想冲过去把她抱在怀里,紧紧地抱在怀里。
可是她的公主不在了,她又能从谁那里得到安慰。
“迷多……”英俊的男子齿间唤出她的名字,最后一次伸手,想要放在她的肩膀上。那一双纤弱的肩头却像烈火一般再一次地让他的手不敢靠近。
细碎的火花纷落如雨,在男子站立之处火树银花一般显现片时。男子却已消失不见。
半空中,一匹赤红飞马咆哮嘶鸣。一位英姿威武的将军,一身亮银战甲,烙刻着繁复精美的红蓝相间的流畅花纹,一张脸面白英俊,不着头盔。明金色长发浓密及腰,发腰处束着流星结。
他在空中回望了一眼小树下孤单哭泣的身影,决然而去。英姿飒爽的将军再没有回头,他知道她还在哭,一直哭。他看见了,比在她的身后看得还清楚。他看见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一只红蜻蜓,他看见她的眼泪流进了脚边的小溪。他看见她的心都哭裂了,有血和水从里面流出来。他还从她那破碎的心里面看见了公主;公主在笑,笑着向她招手。
“迷多~,别哭了啦”公主在她眼前摇手,甜甜地安慰她说,“那家伙又不是故意的”
“还说不是故意的,你看”迷多嘴撅得老高,挽起袖管,指着红红的手臂给她看。
“好了啦,来我帮你吹吹”公主一边揉一边轻轻地给她吹那一小片红痕。“还疼不疼”
“疼!”迷多气鼓鼓地说,狠狠地剜了那家伙一眼。
“好了好了”
“不!就疼!”迷多不依不饶,“谁叫这坏蛋摔人家那么狠!”
“我哪里狠了,你看”他心里发虚,撸起袖子,露出老大一块淤青。一脸的憋屈。
“活该!谁叫你摔我!”迷多破泣为笑。不过适才只见哭相,没掉眼泪。
“密儿,下次让梭连将军做你的陪练好了”公主瞅了她一眼,‘无奈’地说。
“不要!”迷多的舌头打了结“我是说,不……,他……,他万一伤到密儿怎么办!”
“没关系,将军千万莫要手下留情,我没关系的!”密儿坏笑着斜乜了她一眼,故意拔高了声调。
“不是……,我是说……不……”
迷多涨红了脸。公主和其她三个姑娘甜甜的笑。梭连伦将军直挠耳朵,突然好想冲过去抱她……
飞马展翅,角指前方,如梭如风,如光如电。他笑了,甜蜜地笑了,笑出了泪水。
夕阳笑,笑出金红色的光辉。在他的身后,有炫幻的晶光,散射着七彩光芒,被风吹散在空中,飘向来路的远方。
……
平原中部,古越城。
越离坐在画板的旁边,手里握着画笔,陷入苦思。
画上的女子,名叫真溪。是一位公主。曾经,公主是越离的妻子。
这幅画,是一幅肖像画。还差最后一笔。可是他忘记了,这最后一笔,到底该画在哪儿。是她发间的一根发丝吗?是她的眼瞳中闪过的那一丝忧伤吗?还是她腮边缺了一棵小绒?他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然而,他忘记了。因为他的妻子消瘦而又憔悴,这扰乱了他的思路。
知儿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也不知站了多久。放在身后桌面上的茶水早已冰凉,凉得就像极北冰原上的冰山。她不敢去碰他,也许只须轻轻一碰,他就碎了。
那一位叫做卧鹿慕羊?真溪的女子,她那美丽的双瞳里面,充满了深深的思念和忧伤。那思念的后面,掩藏着深深的不甘。不甘的深处,是那片没有未来的痴恋……
手上的画笔,是无数支锈蚀不堪的残剑,笔锋就是被烈焰烧到炽白的豁刃。每一笔,都割在心上,没有深情的伤,只有深深的愧疚和悔恨;在那犁耕般的伤口上,留下焦糊的烙印。
没有泪水,因为泪水都从心上的裂缝中漏干了。
或者再看到你,便已动了情。那情,却没有未来。没有拥有,为什么会失去?明明是一场梦,心却因梦而伤。
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把这双手,送给孤独的牧羊人。这样,他便可以用它抱起那只切慕着溪水甘冽的洁白羔羊,让她躺卧在可以安歇的溪水边。他,便不再孤单……
可怜的知儿,还站在他的身后。静静的,静静的,甚至听不到她呼吸的声音。她那双可怜的小手互握在一起,握得那样紧。她的心拧在了一起,像一方被拧紧的手帕,拧出了好多好多的水,多到都从她的眼睛里面满溢了出来。
他没有看到知儿流眼泪,他不知道知儿在哪儿。这一刻,知儿不在他心里面,也不在他的思绪里面。他把她藏在了不知名的暗处,忘记了那地方在哪儿。
不知何时,有一个阴影一般的剪影,完全遮挡住了知儿的身影。
是那一个叫做梭连伦的年轻将军!
不知何时竟已出现在了知儿的身后!她却浑然没有察觉!
而他的视线,从出现在房间里面的那一刻,再没有离开过真溪公主的脸。
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那种男人的泪都蓄在了膀胱里。有情的男儿才多有泪水,因为他的名字叫梭连·伦。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公主,从来没有。
见过的,只有迷多。
公主的眼睛,让他的心中涌出杀意,如东方瀚海的浪墙,无法阻挡,无处躲避。他原本只要那画匠一生守护在公主的身边,可这一刻,他改变了主意。
这个人,该死!!
有轻薄的烟雾,缕缕丝丝,灵巧像蛇。无声无息地从四面八方伸向知儿和越离。那细丝般的烟雾,悄无声息地钻入知儿的鼻孔。可她却毫无所觉,此刻,她的身子,只不过是一具躯壳。
知儿缓慢地闭上了眼睛,昏厥了过去,倒在了年轻将军的臂弯中。
越离抬起拿着最后一只画笔的手,笔锋几乎便要触到画布的时候,他犹豫了。如丝的毫锋虚悬在公主的眼瞳深处,那里仿佛是一片永恒的黑暗,他永远也不可能触得到那一丝光明的未来。
那黑暗,是公主的思念。
那痴恋,是公主的未来……
他的手悬停了片刻,颓然失力垂落。
小院的上空有一个飞马方阵,数百精骑,身披亮银战甲,战甲上刻满了繁复精美的红纹。拱卫着一个由五面光栅与一面黑晶组成的囚笼。囚笼前端牵出一道赤红光线,连与一匹通身散发着赤红光芒的飞马身后。
将军飞身上马,随后囚笼中一片碎银闪光,现出两个人形,是一男一女,已陷入昏迷之中。正是知儿和越离。
飞马拖笼,向上爬升脱出方阵,复又弧线折转向前,进入平飞状态。
巨啸嘶鸣起处,劲风割面如刀。
一马,当先。
方阵改换追随阵形,迅速进入最佳移动攻防阵位。
一路向夕,飞驰而去。
天穹之中巨啸嘶鸣惊心,犹如天马行空!吓落了夕阳,吓得天顶之上有几颗亮星直眨眼睛。
……
奇异国,七彩虹。
彩虹小树下,彩衣女子还在哭。
空中传来一声飞马长嘶。一匹散射着赤红光芒的飞马拖着一只发光的囚笼,高高掠过彩虹小树上空,向着七彩虹山巅直飞而去。
七彩虹山巅。
一片广阔的天然平台上,有一座多级台阶的巨大方形石台。其上中心位置竖立着一座丈余高的奇怪木架,木架横梁上吊着一只梯形三角刃口的怪刀,寒光锃亮,远远看去就像一面长条形镜框,框内的镜面被斜向削去了下面的绝大部分,只有一小部分镜面还悬留在木框之内的顶端。镜框底部也是一条木边,只是木段中心位置有一个半圆形豁口。豁口前面放着一只大木盆,一只布满暗红斑块的脏兮兮的大木盆。
飞马囚笼从天而降,落在石台脚下。
年轻的将军飞身下马,抬头向石台上的木架处深深望了一眼。转身向后径直走向囚笼。当他走过飞马那力感十足的身躯,飞马忽地人立展翅,嘶鸣声起处,一片细碎的火雨星光突然凭空将其笼罩其中。
微风中,星光弥散渐淡,飞马已消失不见。
只余下仿若从遥远的天边传来的仿佛不真实的天马嘶鸣声声,若有还无,渐渐湮没在掠过耳边的风中。
那一位年轻的将军从笼中取出囚犯,将这兀自在昏迷中的一男一女挟在腋下,就像挟着两个燕麦捆。而这一刻,这一位年轻的将军,双眼中流出了泪水。
那两行泪水,
分别叫心碎和仇恨。
他拾级而上,脚步沉稳。可是他的身子却在颤抖。甚至隔着那威武而光耀的盔甲也能看得出来。
来到木架边,他毫不犹豫地把右手中的男子放在镜框之中,使他的脖子正好卡在那半圆形的凹槽里面。
……刚好合适。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昏迷中男子的那双女子般纤柔的手。抬起微微颤抖着的右手,按上了木框上的机关。
斜刀飞落的瞬间,空气仿佛为之一颤。随即化为死寂一般的宁静……
他微微偏转脖颈,弱弱看了一眼左手中的女子。眼神中掠过一抹挣扎的痛苦之色。
“我本不欲你死,可是我宁愿你死在我手里,也不愿看着你死在你自己的手里”
泪,再次滑落。只有一行。是为这怀中的女子而流。
“但愿你们,能见到她……”他说完这话,就把知儿的脖颈放在了半月形的地方。他抬起右手,想要按下那一个框上的按钮,可是他又犹豫了。突然间他不知该何所适从。
正在此时,白云之下有一道细小的彩虹飞架而来,穿过云雾的那一刻,他看到了一张惊恐失措的脸。
是迷多,脚踏彩虹之桥。她的双眼,绝望地停注在那面散发着寒光的镜框中。
彩虹桥,斩断了梭连伦最后的挣扎。
下一刻,他的手,坚定而决绝地按上了框上的按钮……
知儿————!
绝望的大叫声中,淳于正罡从噩梦中惊醒。一身衣物被冷汗浸透。
原来,自己还在一棵大树上。
是噩梦把他唤醒。
淳于正罡茫然不知所措,木人般转头四望,却不知自己在寻找什么。
“知儿……”他手按胸口,大口喘着粗气。这一刻,他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也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他的脑中不断地重复着斜刀落下的画面。那般的真实,他的鼻孔中充斥着血腥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知儿被放在刀口下面。
“知儿——!”淳于正罡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了起来。空中的飞鸟受到连番惊吓,惶恐不安地鸣叫着乱飞乱窜,在自己巢穴周围起起落落不敢归巢。
那斜刃的利刀斩断了他的心弦。也斩断了寻找玥儿的线索。他再也感觉不到玥儿留下来的本就微弱的气息。他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他的心被那梯形利刀吓住了,在惊吓中消融如蜡……
“走!”匪大飞掠而下,如雄鹰掠水般单手勾起躺在草丛中的女子,速度不减,直向西南而去。
其余三匪不敢迟疑,紧随其后,齐齐升空而去。
只留下一个曾经有生命,如今早已冰冷的物事,静静地,静静地,躺在草丛中。
淳于正罡痛苦摇头,忽地抬头望向西南方向。无意识的意识中,他看见百里之外有数只猛禽向远方飞去,利爪中抓着猎物。
那猎物,像一只肥嫩的羔羊……
痛苦中,他几乎是下意地做出选择——箭矢般从树冠中射出,划出一道痛苦的弧线,与梦醒之前的自己,分道扬镳……
百惠把手中的佩饰放回原处,跃身飞到林梢之上。不经意间回头,西北方向好像有星光一闪而没。
夕阳至美,已近黄昏。或者,……那是一颗坠落北方的星。
玥儿的气息越来越清晰,而百惠和千柔的心却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没底。
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远。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走多远。然而,开弓或者有偏转,却没有回头箭。
有两道白光划破漫天夕阳红,如满弓射出的两只白色光箭,射向西南,再没有回头的可能……
奇异的国度,国王的王宫。
“陛下,梭连将军擅离职守,实有谋逆之嫌”第二副首相痛心疾首地道:“且不论有否里通外敌,未得陛下谕旨,擅携亲卫离境,实乃欺君重罪,陛下!”
最后那陛下二字听入国王耳中,实在是让他烦闷到要死。他又如何不知那梭连?伦到底犯的是什么罪。他又如何会不知道梭连伦为何会犯下如此欺君杀头之罪。
凡事皆有因,他是国王,更是一个父亲。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国王,因为他是一位好父亲。女儿的死,对他打击太大,若非有国家扛在肩上,只怕他便因此就垮掉了。
“卢卡诺伊”国王肘撑着王座扶手,闭目捏揉着眉心平缓着声音道。
“陛下”第一副首相跨前一小步,躬身候旨。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陛下”卢卡诺伊恭敬地道:“臣以为,欺君之罪罪无可恕。不过此事多有蹊跷,事出必有因。臣以为应当严加防范,静观其变,早早做好应对之策,否则,因乱生乱,反而会适得其反。”
“那梭连伦呢?”
“水落石出之日,若果真罪名落在实处,应当凌迟处死,以儆效尤!”第一副首相义正辞严。
国王挥了挥手。卢卡诺伊退出去,着手此事。
“冯布里克”
“陛下”第二副首相跨前一步。
“事关重大,你去帮帮他吧”国王温声道。
“是,陛下”冯?布里克低头,目光中闪过一丝恚怒。
……
平原中部,古越城。
古越城是一座小城,依山傍水。建筑风格偏纯朴古拙。只所以如此风格,并非今人效古,而因此城实实在在便是一座古城。不过是古城今居。
力与美的完美结合为基调,规整的灰晶岩为主音。处处彰显着岁月赋予它的厚重与古朴之美。
没有人知道是谁建了这座城,也没有人知道自己房顶上那一片片坚如铁石的檐瓦到底是什么材质,又是从何而来。
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也没有人知道关于它的一切。一代又一代的城民们只知道:曾经,这座坚如铁石的固城,只在一夜之间便人去城空。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一夜之间便被遗弃?还是说有什么可怕的存在,只在一夜之间便把所有人都掳了去?
拂去记忆上的蒙尘,才发现,尘封的记忆,原来是一片惊悚人心的空白。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们早已淡漠了那片似乎根本不存在的历史。没有记忆,也谈不上忘记。那是属于别人的曾经的记忆,不属于自己的先人。
古越城,是今人的古城;古人的遗梦。
梦中未曾相遇的人儿,还在城中。逐梦的人,又在哪里?
故人去,茶凉如冰。只有逐梦人梦中无缘相见之人还在原处。梦中的眼神,依然深望着早已不在眼前的逐梦人。
梦与现实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为何梦中的眼神,会再一次出现在眼前,就像再一次走进梦中?
“知儿——!”
他呼唤了一个与逐梦人和他在梦中也没有遇见的人无关而又密不可分的名字。
这一刻,梦与现实,或者现实与梦,在他的脑海中重合在了一起,再不能分得清楚。
再一次地,那闪着寒光的梯形利刀沉重落下,避无可避!
他悚然惊出一身冷汗;他不知道:桌上的茶,究竟凉了多久!他不敢想,那利刀早已在现实中落下,或者还在梦中正无休止地重复着起与落。
毕生的功力,掘尽的潜力,一身真元。只在此刻,便已催持到了极致。就如滚滚浓烟中突然爆燃的釜底禾秸,终于充分地,完完全全地,燃烧了自己。
一道极绚烂的耀眼炽光从古城不曾被人在意的偏僻角落升腾而起。弧线折弯,遥遥指向梦里烙刻在记忆中的木架……
从未曾亲耳听到过的晴天霹雳炸响,爆闪着不真实的云雾。震耳欲聋,小城也随之轻颤。
上古的传说,便在今日,城民们的耳中见证!甚至,人们耳中仿佛又同时响起了才被刻意遗忘掉的天马嘶鸣声!
人们对着那霹雳声远去的方向行注目之礼,以为天降异兆,各人怀搋臆想,惊而惶惶……
“走!”匪首怒吼了一声,口中溅出带血的飞沫。
四匪升空。打来处来,往来处去。肩扛着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馍。那馍太重,差点把四只饿兽砸死。可惜,砸偏了。
万幸,砸偏了……
再不敢怠留,再不敢懈慢。催尽余力,但愿早早甩脱一次又一次抛向自己的夺命套索。
匪首伤势最重,几乎已至生与死的临界点。非是敌伤,却因敌伤。虽因敌伤,却差一点自害己命。二三四贼伤势不同程度,却基本没受什么内伤,纯粹皮肉损伤,碍不着什么事儿。
已距战场三百里。
贼伙数次变线,折线逃离。以免给人引路,被人端了老巢。
在一个几乎便是迂回线路之时,众贼惊见天生异象:侧前远方天际似有绚丽彩云流转,似缓还急。
流转的彩云,似是一个巨大的幻彩漩涡。漩涡的中心是一片正圆形的深邃幽远的暗蓝。
纯蓝欲滴。仿佛有一股神秘的无比强悍的离心巨力,将天穹撕了开了一个巨大的圆洞,露出天穹背后更加纯澈,更加深远的深蓝。而那仿佛无限深远的深蓝背后,又仿佛是无边无际,无穷的纯质黑暗。
是异宝离开人间的异象!贼首震惊定睛,心中突生此念。已被催持到极限的内力,无由流向圆睁的双眼。身体在惯力的作用下像一枝满弓而放的羽箭,呼哨前射,而没有自主控制意识。
有一道极细微的旋转上升的亮线,忽明忽暗,好像两个散射着美丽光辉的宝物,互依互牵,正升上神秘天洞。
看不真切,已是目力极限。贼首突地心生渴念:好想看到那宝物的真容!只想看到那宝物的真容!如若可行,愿用生命为价,买得那一眼真知!
直娘贼!匪首心中毒咒一句,意念中揍烂了自己半边脸。
当他愿用生命为价这一个意念生发之时,不知怎么,他的脑中闪过两把宝剑的倩影。
倩影袅袅,绰影娉娉。潜意识流中,心生遗愿:唯愿那双剑,或者至少其中一位,愿意刺穿自己的胸膛,如此,便死而无憾了……
直娘贼!!贼首再骂。再又揍烂了另半边。这一句,他骂出了恨声,其他三匪正皱眉遥眺着远天异兆,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怪叫唬了一跳。
“日了狗了!”贼首又吐污言,恨得牙根直痒,“老子天生就是他娘的畜牲!”骂过并不解气,又在肩上女子的臀上恶毒地搦了一把。
半昏半迷中,女子身子吃痛,无意识地抽搐了一下。
“走!”不知已是第几次,贼头儿又暴喝了一声,满腔子的怒火。
“今儿还真是日了狗了!”三贼也看出大哥反常,脑袋何时被肚儿里的骡子又给踢了?
肚儿里的骡子是四贼互相调侃时的暗语,意指很不合哥几个邪恶性情的怪念。那可他娘的纯粹是弱者才会有的思想表现。
这一次,众贼走了直线。还躲个鸟啊!搞得爷爷像他娘的缩头乌龟!
“大哥,你说那升天的异宝会不会是两把宝剑?”尾贼目现迷惑之色,不知是不是瞎猜到了什么,还是突发奇想。
“若果真如此,爷爷我宁愿就死在那宝剑之下,倒也不辱没了爷爷一世英名!啊哈哈,哈哈……咳!咳!”二贼自嘲,却不料结界内居然还呛了风,差点没咳岔了气。
“老二!你格老子的黄豆吃多了吧!想好事儿的死鬼咋就没捎上你啊!”贼三心里对八字远没有一撇的好事儿被老二臆想中摊上而大大地不平,嘴巴上醋溜溜阴损了一句毒的。
“够了!”匪首远远飞在前头,心里大烦,脸也不转,一头扎向前方夕阳下仿如无边无际的迷蒙之中。
贼二撇嘴,贼三贼四则对着大哥的后臀用手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左手拇食二指指尖相扣,捏成一个小圆,右手食指在那捏成的小圆洞中进进出出地捅了几下,嘴唇咬牙张翕,嘴里也不知是否是在咕哝什么鸟语之类,若果真是的话,只怕二贼一个指爹一个指娘了。
他娘的鸟嘴张得都不一样。此时若有唇语大师在旁读出,指不定这二贼又掘了自己大哥家的祖坟几回。
……
无月夜。
星光下,蓝苍山上空掠过一片乌压暗影,高远黑暗处,似有劲风呼啸。
飞马战队暗潜入国境,战马噤鸣,飞速平缓,飞翼进入半滑翔状态,就着气流颠簸之势升降前进,降噪潜行。
几乎不易察觉地,大片暗影中心位置向下脱出一个小小的黑影,直落而下,进入崇山密林。
山的那一边,是一个奇异的国度……
“启禀元帅!梭连将军的亲卫团已入境!”
边境防御工事内,一将军模样人物,身着全身铠甲单膝跪地禀道。
卢卡诺伊挥手示意那人站起。微转下头,对身边一同站着的冯布里克说道:“布里克老兄,你怎么看?”
冯?布里克并不转头,只是双眼平视前方状若思索。
不易察觉地,他的眼中滑过一抹轻蔑的怒意。
“梭连伦狡若荒漠之狐,大人切莫掉以轻心”冯布里克思索片刻,略略郑重了一下声调,双手仍负于身后。
卢卡诺伊仿若受教,郑重点头。向那人挥手,那位将官便从二人眼前退去。
一座高大巍峨的黑色山峰。
巨峰通体灰黑,突兀嶙峋,仿佛一个恶鬼般的巨人,孤独伫立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荒石戈壁上。
整个天空昏沉压抑。云层翻滚不休,如狂怒的巨兽,欲挣脱关锁着它的坚固牢笼。看得出,云层极厚。似有极其烈灼的超炽日光普照其上,热力透过云层传导至地面,温热干燥而又沉闷。奇怪的是云层上下翻滚却并不水平流动,好像也无法散开,灼烈的日光也穿透不了它。
山巅是一个巨大的平台,像是有人用大能力把山尖削了去。看上去离天空中的云层很近。当你仔细分辨,又发现它又非常高远,却没有空旷开阔之感;在强烈的压抑感之中,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什么力量压缩成了虫蚁一般大小。
平台上是一个看上去同样巨大的又相对小的多的石台,高十数丈,四面阶梯,呈平顶金字塔形状。平台正中心有一道虚空之门,高约两丈,阔一丈二尺余。
虚空之门就像一道密钥,插入这天地间唯一突出而又突兀的匙孔中。
门的下方站着五个人。
“他一定会来的”王后对怀里正伤心哭泣的迷多轻声安慰。
“不要!不要……”伏在王后怀中的女子好像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低低啜泣着屈声喊道,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其余三个女子围在王后身边,团团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潜入国境之内的飞马战队趁着深暗的夜色,沿着国境线向南飞行,极力地掩藏着行踪。而那一个脱出的黑影却沿着来路折返,复又出了国境线,沿蓝苍山向北飞行。
飞马战队就像一个巨大的悄无声息的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绝大部分细碎成片的隐藏在更暗处的铁沫。好似蓝苍山中的食人鱼灵敏地嗅到了猎物鲜血的味道,同样无声无息地潜追不舍。
几乎就在食人鱼群完全改变了游向的同时,那一个向北飞行的暗影再次潜入国境,迂回深入,星空之下,向着既定的方向如魅而去。
黎明前的至暗之时,夜空更高远处,一道更加鬼魅的暗影极速掠过蓝苍山,箭矢般射入异国国境线的上空,如入无人之境。
东方渐亮,淳于正罡循着梦中线索的指引,落在了七彩虹山顶。
山是梦中的山,又不似梦中的山。山顶没有梦中的石台,更没有斩人首级的木架。目力所及,只有一片奇花异草的海洋。
捕捉到熟悉的气息,一路追踪,终于,他在山顶的某个奇花异藤的峭壁前停了下来。
挂在峭壁上的异藤奇花就像一面从天而降的瀑布,气势磅礴而又美丽非凡,犹如天外仙子倾倒向尘凡世间的花瀑。
淳于正罡无心欣赏美景,毫不迟疑地挥手一刀,横向切断了眼前五彩缤纷的花瀑藤萝。
藤萝如断瀑坠落,后面露出一个小山洞,入眼好似嵌在山壁上的一道不规则小门。山洞幽深,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知儿!淳于正罡心里大叫着女儿的名字,一头扎进那幽深黑暗之中。
恍惚中,似乎飞行了很久,又似只不过眨眼之间。突然前方有亮,感觉的无缝衔接处,眼前一片豁然开朗。
入了山洞,又出山洞。
眼前洞外,已是另一番天地。
身后的山洞嵌在一个巨大的岩体上。那岩体像一块巨大的墓石。巨墓周围是无边无垠的类戈壁。只所以称之为类戈壁,是因为这片广阔的大地却如戈壁一般荒凉,粗砾不平的地面微有起伏,就像湖面上的无风微波。然又与戈壁有很大不同:空气温热闷压,灰云翻滚涌动,却没有风沙;大地上到处满布着大小不一的石块碎砾,但却颜色各异,好像这大地便是一片被揭去外衣的矿脉,各种不同的矿晶裸露在空气之中。由于没有风沙侵蚀,石块石砾棱角分明,显然也并未受到雨水冲刷。
这是一个让人倍感压抑的不毛之地。看不到日光,始终如一的昏沉,不明不暗,似乎也没有昼夜交替变化。
远处,有一座突兀的黑色大山,狰狞怪戾,像一只七头十角的恶鬼,孤独沉闷地伫立在远方靠近地平线的地方。就像是支撑着厚云的柱子。
嗖!
这便是淳于正罡第一眼看到那座黑山的本能反应。
如电飞射,直指峰顶平台!
平台的石台上一发光的长方形巨框之下站着八个人:五个守在门口,三个与她们相对。三个人中,其中的一个正是梦中看到的那一个年轻的将军。而他的腋下,挟着两个人,低垂着头,不知是被制住了气脉,还是正陷在昏迷之中。
那是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子。
“知儿!”
这一幕映入眼帘,淳于正罡大叫一声,随即口鼻之中窜出鲜血。内力的催持,已至体躯血肉承受极限,极快的速度,已使他的身心处在了崩溃的临界点。
“让我进去!”年轻的将军对着守在门口的五个女子吼道。
“不要!”迷多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两只小手无助地捂住自己的脸,“我求求你,求求你!……”才一发声,她已声嘶力竭,却早已沙哑到再听不出是她的嗓子所发出的声音。
“梭……”
“让开!”年轻的将军打断了王后的呼唤。王后和其她三个女子踏前一步,又被他喝止住了脚步。他的双眼满含着泪水,视线再不能离开跪地仆伏着的女子半分。
身后传来异样感觉,年轻的将军回头看了一眼。极远处天际线上有一个黑点儿正快速而来。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随手把臂弯中的男子抛掷在地上。
那男子被摔醒,只觉头昏脑涨,如大醉初醒,勉力跪地撑身,神志却一时无法清醒。迷多越发害怕,额头枕在坚硬的地面上苦苦哀求。
可是他的心早已坚如磐石。
你的公主走了,你的心就碎掉了。
一同碎掉的,还有另一个人心中的饶恕……
她走了,可还会回来吗?……你的心呢?
天起了凉风,微风拂动将军的几根发丝,发梢指向跪在地上的男子。
男子费力摇了摇头,视线逐渐清晰起来。
眼前的景物,似曾相识。
是曾相识……
真溪……
他的双眼突然闪亮,脑中显现出早已烙印在心底里的柔美容颜。
有血,从嘴角流出。胸口微凉,仿佛心,破了一个洞。
好凉快啊!他不禁感慨。耳边传来女子的哀鸣,似乎她是在叫喊着:不要!不要!……
他感觉好遥远,恍如梦中的声音。
真溪微笑着向他走来,幸福的微笑着,张开怀抱,拥他入怀……
第九个人出现在了将军身后,他目瞪口呆,眼前一幕使他不能言语。
将军轻轻放下另一只手上正陷入半昏迷状态的女子,使她的身子伏在已躺身在地的男子身上。因为,那是她的丈夫。
那一个男子静静地躺在地上,胸口处有血,还在流,可是他在微笑。直到那幸福的光,凝固在了眼瞳深处……
他的无名指消失了,
连同那一个七万光年的指环……
女子悠悠醒转。有几个人正围在自己身边哭泣,是几位美丽的女子。只是她的意识还没有恢复,又大又亮的眼睛却没有神光,迷茫而又木然。
手上忽有湿湿的感觉传来。她木然低头,眼中映出一片殷红。
好像是一个伤口,还在流淌着鲜血。
她本能地用她那一双好小好小的手去捂那伤口,不料鲜血却从她的指缝中一道道流出。她茫然转头四望,似想要寻求帮助,可其中有三个女子掩面跑开了。没有跑开的两个女子,其中一个跪在了她的旁边,双手捂着脸痛哭了起来,她的手上全是血。
不知怎么,她的双手总也按不牢,因为那伤口还在流血,越流越慢。
她又转向还站在身旁的女子。目光相触的瞬间,那女子偏过了脸,看向另一边。有两行泪还挂在她的脸上。
这时她听到了打斗的声音——有人在拼命!
她浑若无觉,再次低头看向那遮掩在自己双手之下的伤口。木偶一般地转过脸,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然而那脸上的幸福,竟是那样陌生……
你是谁?她问了一句。
那人没有回答她,因为他在微笑。幸福的微笑。
身外的打斗声愈加激烈,几已进入生死一招的白热态。而身周的女子们除了哭还是哭。
哥~?是你吗?她盯着那张陌生的脸,小意地问。双手茫然无措地在那伤口处胡乱地抚按着,而她却不知道自己的双手在哪儿。
情不自禁地,她低头吻上了早已冰冷的唇。她感觉那唇是热烈的,是销魂的。好像哥哥的唇。
眼泪滴落在他的眼睛里,仿佛又有了光亮。好像他幸福的哭了……
一吻有多长?
或者,是一个女子的余生。
“哥,等等我”她在他耳边轻声低语。伏在哥哥的胸口,再没有动。
一吻有多长?
或者,是一个女子的一生……
……
嫣知泪
泪如真溪
心心若即
心心越离
嫣知泪
泪如真溪
心心相近
心心相印
嫣知有泪
泪如真溪
心有所属
心有所依
嫣知有泪
泪如真溪
越即越离
越离越即
嫣知泪
泪如真溪
真溪如泪
真溪如妹
嫣知泪
泪如真溪
嫣知柔水
嫣知柔美
嫣知有泪
泪如真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