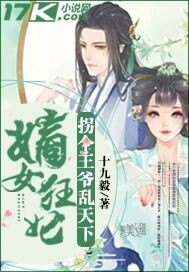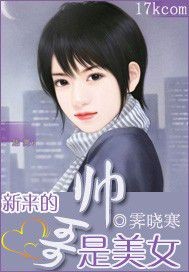折腾了一夜,又加上淋了雨,孟鹤妘一上车便靠着车壁昏昏欲睡。
裴伷先拧干了湿漉漉的衣摆,一抬头,正对上孟鹤妘略显苍白的那张睡脸。
连日来的奔波,她大概是累极了,眼窝下生了两圈黑云,少了平日里的灵动,平添了几分柔弱。
“公子!”木石在车外唤了一声,裴伷先几不可查地皱了下眉,伸手拖住孟鹤妘歪倒下来的身子,顺势将她揽在了怀里。
木石搭在车帘上的手一僵,不敢置信地看着车厢里抱在一起的二人。
裴伷先耳尖微红,薄唇微抿,不着痕迹地将孟鹤妘往身前带了带,阻隔了木石的视线。
这就护着了?
木石脑子里嗡嗡直响,仿佛看见自家养了好些年的翡翠白菜被一只憨头大耳的猪给拱了。
“是宫里的马车。”
裴伷先微怔,低头看了眼怀里的孟鹤妘,小心翼翼从一旁拉过抱枕垫在她身旁,而后起身下了马车。
马车停在西市的一处宅院门前,这是张公早些年的院子,入了内阁之后便一直无人居住,这几日正好腾出来给裴伷先暂住。
门前停了辆八角吊顶的马车,两个小黄门站在门前,一见他出来,连忙上前道:“裴公子,爷已经等你多时了。”
裴伷先撑着伞走到马车前,隔着车帘朝马车拜了拜:“圣上。”
“起来吧!”马车里传来男人沙哑的声音,一只略显枯瘦的手微微撩起车帘,露出一张蜡黄的脸和衣领下的一脚明黄。
“朕以为,你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
裴伷先低敛着眉,没说话。
“使臣的事,你可有眉目了?”高宗揉了揉眉心,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裴伷先道:“还未有眉目,不过看起来是胡禅的手笔。”
高宗眉头微挑:“你此前来信给张平说瓦特有异动,让朕对瓦特使臣多加防备,没想到果真一语成谶,只是……”高宗微微一顿,“朕若是继续装做中毒不起,怕是对朝政不妥。”此前他与张平商量,将计就计称病罢朝,引幕后之人现行,没想多时隔多日,对方竟然毫无作为,这实在有些反常。
“圣上不必着急。”裴伷先说道,“用不了几日,对方怕是要现形了。”
高宗大喜:“你可是有良策了?”
裴伷先微微点了点头,目光若有似无地看着不远处的马车,虚掩着的车帘里,一双狡黠的眸子正死死地盯着这边。
高宗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不由得轻笑出声:“听说你在益州带了个丫头回来?”
裴伷先面色一僵,眼神暗淡下来。
高宗的声音渐渐冷却下来,若有似无地看着裴伷先,淡淡道:“既然她不是云霞的孩子,那另一个孩子……”
高宗的话没有说完,喉咙里一阵发紧,他轻咳两声,一旁的小黄门连忙冲过来,从手里的食盒中拿出一块糕点递给高宗。
高宗结果糕点,一把塞进口中,还未来得及咀嚼便咽了下去。
小黄门怕他噎到,连忙又送上了水壶。
裴伷先面无表情地看着高宗将整只水袋里的水一饮而尽,未了还打了个饱嗝,一股腥臊的味道扑面而来。
喝完了水,高宗便有些昏昏欲睡,仿佛忘了刚才的话,招呼车夫急吼吼驾车离开。
随着那辆马车的离开,偌大的巷子里再次安静下来,木石有些担忧地走过来,看着马车离开的方向不安道:“公子,圣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裴伷先若有所思地看向远处巍峨的宫闱,许久才淡淡道:“这京都,怕是又要不得太平了。”
————
跳河的那位乔老爷终究是没救回来,打捞上来的时候,人都死了,脸被河水抱得想发面馒头一样,离着老远都能闻到一股子腥臭味。
孟鹤妘站在人群里看着家属簇拥着衙门口的衙役把尸体抬走,经过她时,下意识朝抬尸体的担架看了一眼,一只被河水泡发的手从担架里划了出来,透着一股子死气。
“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热闹?”木石从旁边的铺子出来,手里拎着胜记的蟹黄包,面色不太好看。
孟鹤妘回头看了他一眼,一把抢过他腰间的荷包。
“哎,你干什么?”
孟鹤妘一乐,把荷包收进怀里:“我去对岸逛逛,你且先回去吧!”说着,一阵风般跑上拱桥。
木石有心想追,又怕蟹黄包凉了不好吃,只好拎着食盒往回走。
对岸桥墩旁的孟鹤妘见他离开,抖手晃了晃荷包,一猫腰窜进永安茶馆旁边的巷子。
昨晚她见库乐就在巷口站着,猜测他多半是住在巷子里,果不其然,穿过两条小街,在一家药铺门前见到了正与掌柜的鸡同鸭讲的阿瞳布。
“给他治风寒的药。”
阿瞳布诧异地回头,没想到会看见她。
“滚,滚滚公主?”
孟鹤妘挑了挑眉,从荷包里掏出银子递给伙计让他去抓药。
“库乐病了?”
阿瞳布抿了抿唇,转身想走,被她一把揪住衣领,黑着脸又问了一遍:“我问你话呢?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公主,长能耐了?”
阿瞳布挣脱不开,急得额头直冒冷汗:“我,并没有,是公子他……”
“他不让你告诉我?”以库乐的温润性子,瓦特使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确实不会让自己卷入其中。
阿瞳布紧紧抿着嘴,死活不开口。
不多时,伙计抓了药回来,孟鹤妘拎着药往他怀里一塞:“你走不走?要是不走,回头库乐病死了,我看你还跟谁表忠心。”
这话果然有用,阿瞳布连忙抱紧怀里的药,深深看了她一眼,扭身往药铺东边的巷子走。
库乐选择的住处很不起眼,在一家书院后面,平素里若是穿着汉服带着幂篱出门,倒是不会惹人注意,只会以为是书院里的书生。
阿瞳布推开门,一股子浓郁的药味扑面而来,库乐面色苍白地坐在院子里的石桌前翻看大盛律,旁边的地炉上咕嘟咕嘟地烧着药壶,苦涩的药味随着蒸汽弥漫了半个院子。
“回来了啊!我把……”库乐一回头,卡在喉咙里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孟鹤妘哼了一声:“昨晚在河边见到的人果然是你。”
库乐放下大盛律,扯唇笑了笑:“我没想到你会看到。”
孟鹤妘抿了抿唇,走过去一脚踢翻他脚边的地炉子:“我要是不来找你,你是不是就算病死也不会见我?”
库乐脸上的表情一僵,低头要去收拾地上的炉子。
孟鹤妘心里窝着一团火,冲过去一把拉住他的手:“你打算怎么办?一个人救使臣?”
两个人心知肚明,他这个时候出现在京都,无非就是为了使臣一事,一旦使臣的罪名订了下来,大盛和瓦特少不得要开战,这对葛丹来说,实在是灭顶之灾。
库乐抿唇不语,苍白得脸上透出一股无奈:“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孟鹤妘嗤笑一声:“你怕是不知道,母亲真正的孩子就在使臣里面。”
库乐面色一白,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孟鹤妘叹了口气,一把将他按回椅子上:“你听我说,使臣的事,怕是还有内情。”
库乐苦笑:“但是没有证据,我这几日在城中多番打听,当日参加宴会的三人除了木樨之外,还有斑布和科尔隆。当时提议给大盛皇帝献雪耳猕猴的人是科尔隆,酒也是从他桌子上拿的,这是铁证。”
孟鹤妘没想到不过几日的功夫,他竟然已经打听到了这么多。
“这案子现在落在了刑部,裴伷先可能会帮邵一白来查。而且……”她略微一顿,把张公这件事儿给瞒了下来。
库乐面露狐疑:“他怎么会来京都?据我所知,他是戴罪之人,若是无召进京,那是杀头的大罪。”
孟鹤妘若有所思地看着地上的小地炉子,阿瞳布已经把它翻过来,正撅着屁股点火。
“这件事儿你就不用管了,重要的是,要想查清使臣的案子,只有他能办到了。”
库乐抿了抿唇,抬头看她:“有一件事儿,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孟鹤妘狐疑地看他:“何事?”
“我想见裴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