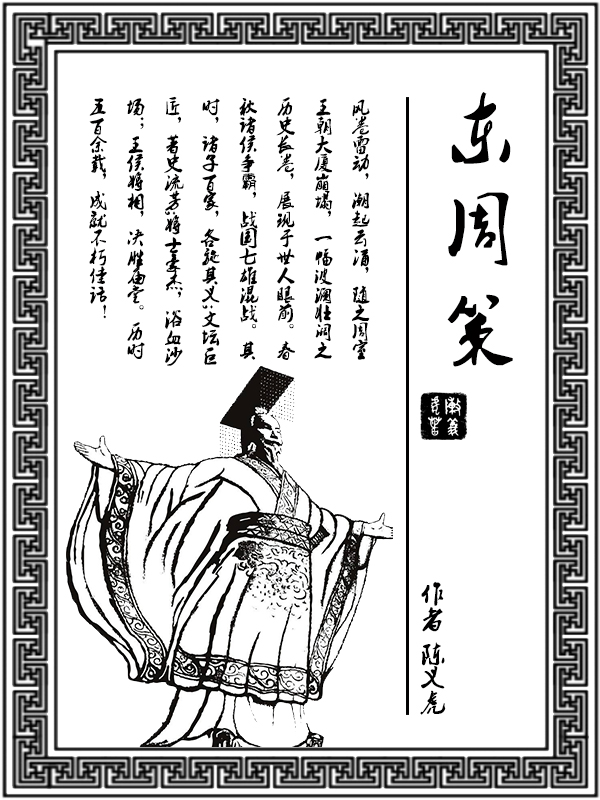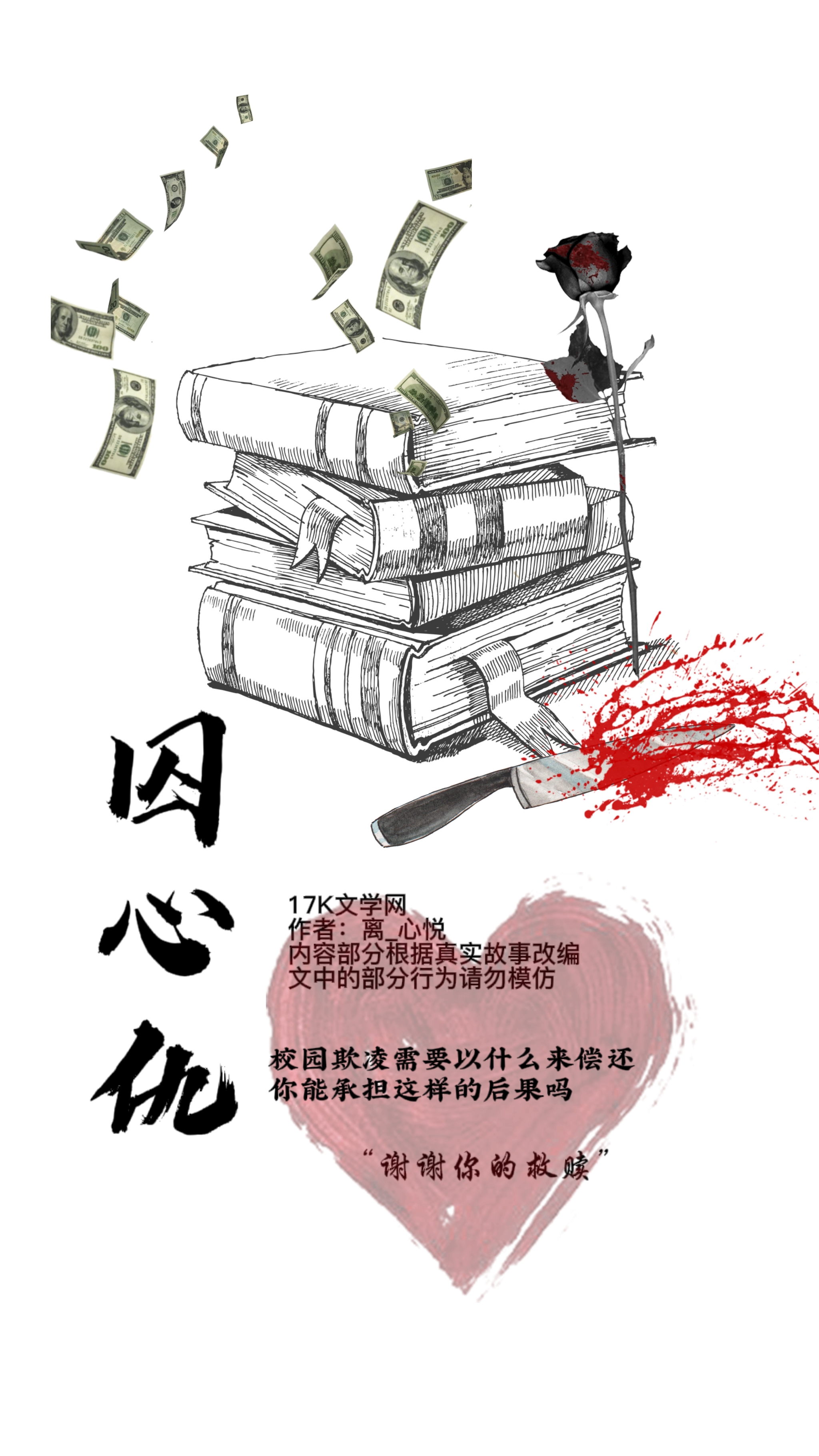陈奇和马三被送走。衙役、捕快、狱卒和仵作只得呆在县衙内,不得外出。如有特殊事项需要出差,必须向四大护卫报备。
成康把镖局老板带了进来,跟在后面的还有县令大人的小舅子。酒楼老板一看,脸色更难看了。县令大人的师爷也被带进来。之前寻他不着,几经搜索,终于被四大护卫找到。他进来后,迅速与县令大人交换了眼神,彼此都读懂了对方眼中的信息:这次棘手了。
此时,大堂内的人员是这样分布的:先克和贺文坐在一起,四大侍卫站立左右,对面是县令大人、师爷、“醉仙楼”的掌柜、镖局老板、打手马三、县令大人的小舅子葛成。贺文全神贯注,神情戒备。他的手不时往腰上摸,那里有把佩刀。下一步就要将县令大人的伪装彻底撕开,他担心他们会放手一搏,对先克不利。
空气中的凝重,被沉默的双方,打造得愈加浓厚。在座的人,尤其是站在对面的几个,有种快要窒息的压迫感。仿佛千斤重的石头压在他们胸口,差点喘不过气来。
“掌柜的,本帅想和你确认几件事。”刚才人多,有些事情不方便说,所以才将一干人遣走,方便慢慢问话。先克说道:“请你据实以告。”
掌柜点头如同捣蒜。他预感事情不妙,可是这位将军的口气又让他心存侥幸。由于先克的用词非常轻巧,他的神情稍微放松了些。
先克接过贺文递过来的账簿,说道:“我们查过你的酒楼,有人反映,菜价全凭你们张口说了算。点的时候说是按斤论价,结账时候却是按只算账。过去也有不少像余风这样耿直较真的客人,在你的酒楼与伙计发生过争执。当然,最后都屈服于你们打手的淫威,不了了之。”
“酒楼菜价都是明码标价,有人嫉妒我们生意火爆,所以含血喷人。”酒楼掌柜大声辩解。反正酒楼的收入主要是靠衙门的开销。那些不好彩的撞到网里来,吃了一次哑巴亏,再也不会来了。余风已死,死无对证,他只要不认就对了。
“哦?”作为一只挡箭牌,想不到掌柜竟如此尽心尽职。先克说道:“掌柜的如此说,倒像是本帅故意冤枉酒楼了。”先克暗想,掌柜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禁语气讥诮。
“小的不敢。”堂堂大将军,掌柜哪敢得罪,只得解释道:“怕是将军初来乍到,被有心人误导了。”
“的确,口说无凭,可能会冤枉好人。本将军这次刚好有证据。”先克接过贺文递来的几张布条,上面写满了酒楼好几笔收付的内容。
原来,于掌柜派去卧底的伙计,把这几日酒楼做的几笔生意的收款明目都记录下来。上面清楚的写着,某某菜推荐给客人时,说是多少钱一两,结账时却要按根、按条收钱。或是报价和实收相差好几倍。这些差价,普通菜相差还不远,肉菜的差距之大,简直令人咋舌。
酒楼掌柜接过布条,上面字迹虽歪歪斜斜,却是清清楚楚。哪月哪日,什么菜,几个人消费等等。他反复思索,这几日确实有这么几笔消费,菜品也对得上。可是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呢?
“掌柜如果没有异议,就是默认存在欺诈客人的行为。那就不是本将军被人误导了。”掌柜还没来得及再辩解,先克话锋一转,盯着县令大人,拿起一本账簿说道:“这里是县衙与“醉仙楼”的往来账目。上面显示,一个月,衙门仅吃饭一项的支出,就高得吓人。”
先克继续道:“‘醉仙楼’的花销如此昂贵,为何还被指定为县衙专属的用餐点?本帅粗略算了一下,光县令大人一人,在酒楼吃饭喝酒一个月的花费,相当于请人给全衙上下所有人做饭买酒,一年的开支。如此奢侈浪费,平陵百姓如何供养得起?”
师爷一听,脸色大变,头埋得更深了。
“可能是有些账目没有核对清楚,一时疏忽,故此弄错金额。下来之后,定会严厉约束下属,不再犯此类错误。”审余风案时,县令大人已经大汗淋漓。本以为他们只是盯着刑讼之事,没想到他们竟盯上了“醉仙楼”。
刚才他们竟拿出了酒楼欺诈的证据,不知道下一秒,他们又会冒出什么新证据。县令大人简直如坐针毡。此刻脑袋已经混乱,只能硬着头皮,胡乱搪塞。轻描淡写,应付完当下再说。
“疏忽?弄错金额?如此巨额的开支竟会弄错?”先克不容许县令大人逃避,他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请问县令大人,“醉仙楼”的掌柜是谁?”他指了指自称掌柜的那位,摇摇头。“本帅要问的是,真正的掌柜,而不是被操纵的傀儡。”说完,他右手食指一指,指向那个满面油光,刚刚从温柔乡里被拉出来的县令大人的小舅子葛成,“是你!对不对?”
得知先克要审案,孙副将派人闯进葛成位于西郊的别苑。葛成还沉醉在温香软玉当中,赤条条的被人从被窝里拉了出来,懵懂不知何事。来到县衙门前时,他还十分诧异,姐夫如果想要找他,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待他走进大堂,看到县衙的主人竟然只能站着说话,他才明白,有大人物到了。
面对这个跟他儿子年纪相仿的白面书生的指责,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张口结舌了半晌,才呐呐说道:“小的只是个…...闲人而已……并不懂什么酒楼经营……这些……都与本人无关……”。
“闲人?闲人能坐拥花园华府,郊外有富丽堂皇的别苑,藏着本县最艳丽无双的美人?”孙副将给到的信息非常有用,葛成睁眼说着瞎话,先克一口揭穿。“要不要我请人来作证,你便是县令大人的大舅子?或者把你夫人接过来,告诉她我们是怎么抓到你的?来人啊……”先克扬声作势就要差人去办。
“不……不……”葛成连忙摆手。她夫人是出了名的醋坛子。听说他金屋藏娇,可是从没抓到现形。被葛成几次三番糊弄,以为只是捕风捉影。如果让她来到此地,公堂马上就会上演全武行。她撒泼耍赖起来,可是惊天地泣鬼神。不闹得人仰马翻,誓不罢休。偏偏家中大小钱财事务,均由她一手掌控。她的手腕凌厉得是人都惧她三分。
虽说有姐夫关照,葛成的夫人家也非等闲之辈。老丈人是位致仕的官员,颇有手腕。葛成还须仰仗夫人一家才有吃香喝辣,倚红偎翠的本钱,可不能得罪了财神婆。“小的承认……县令大人是我姐夫,酒楼……与我……”他看看县令大人,县令大人不敢与他视线对接。他又看向对面的先克和他身旁沉稳如山的中年人,决心还是实话实说。“小的才是真正的掌柜。”
说完,他闭上眼,不敢向四周围看。他有预感,开了这个口,他们的利益联盟已经被撕开口子。但是,他也是被逼无奈啊……
“这里还有一位证人——”先克指了指镖局老板,“还有一些往来账目。”先克朝成康点点头,请他将账目拿给县令大人过目。“‘醉仙楼’里的打手,据我们所知,均是“灰狼”派遣的兄弟。”
“雇请这些人的费用,却是通过镖局先垫付给“灰狼”,再由酒楼支付给镖局,最后由县衙支付给酒楼。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费用,最终是县衙买单。县衙请的打手,驻扎在酒楼。酒楼是葛成经营,葛成又是县令大人的小舅子。这一系列联系起来……”
先克看向葛成,故意忽略掉被吓得脸色发青的县令大人。他已被吓得太多,有点昏昏然,且让他休息片刻。
先克转向葛成,“酒楼既是你经营,县衙所有人吃饭都去你那划账,这不奇怪。毕竟县令大人是你姐夫,帮衬小舅子的生意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一个小小酒楼,却要雇请江湖上出了名的帮派的打手,你怕什么?难不成你开的是黑店?卖的是人肉叉烧包还是虫草煲人骨?”
“小的不敢,不敢开黑店。”葛成吓得脸发白,连忙辩解,“小的绝对没有做杀人越货的勾当,绝对没有。”
“那余风算什么?”先克步步逼紧,“他不过是对菜价有所质疑,就被你们派出的打手打成重伤。到了县衙,又被县令大人下重刑。客死异乡,孤苦零丁。家人还盼着他返家团聚,尸骨未寒却被草草掩埋了事。你们虽没煮人肉蒸人骨,你们的所作所为不是黑店?”
成康和刘进到依县查访时,余风的老婆孩子还在翘首以盼,等他归家。却不知,余风早已死在眼前这些人的棍棒之下。这些人真是心狠手辣,残忍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