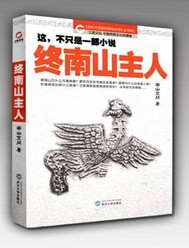秦军那边一直密切关注着晋军的反应。没等到动静,心想,指不定对方气昏了头,现在正排兵布阵,明天一早见分晓。
谁知第二天,晋军还是依然故我,不紧不慢。秦军急了,又派出两名擅长模仿的军士,将昨日的声讨,惟妙惟肖的又表演了一番。这回是上午两场,下午两场,仍然不见反应。
如此情况持续了三天。
秦军再去骂时,竟被晋军将士嘲讽说:“能不能换点新鲜的话题?同样的说辞,我们听得耳朵都长茧了。我们大将军根本不理会,你们省点力气留赶路吧。”
骂战军士气得不轻。回去跟长官一说,长官这才明白,原来骂战已经骂到对方烦闷,却未达到让人愤而出战的目的,白白浪费了三天时间。继续消耗,吃亏的是他们。这样下去,他们就会无功而返。
此次是君主亲率大军,如何丢得起这个脸?除非硬拼?可是,现在是天时地利都不在他们身上,贸然出战,到时损失惨重,危及君主安危,更是下策。左思右想,正不知如何是好。
这一边,赵盾召集五将开会。例行询问了军情,交待军中纪律,强调战略意图之后,会议解散。
夜已深,月亮已经悄悄隐藏在云层之后。有两个人却无心睡眠,在说悄悄话。
“这样守下去,有什么意思?”说话的声音很低沉。
“这可是大战前就定下的计策。我军占据优势,守比攻好。”一个略微沙哑的声音回应道。
“战前就定下的计策?不就是那个臾骈说的,坚决不出战,将对方拖垮?”低沉的声音似乎很不满。
“你好像对臾骈将军很有意见?”沙哑的声音不明就里。
“不过是我赵家给他机会,他便处处献宝,偏偏我堂哥还非常信任他。要不是他,我早在“六卿”之列了。”低沉的声音恨恨道。
“臾将军位列“六卿”已有三年,并非此次新任,为何偏偏针对他?”沙哑的声音打破沙锅问到底。
“‘六卿’哪个不是功勋之后?”低沉的声音有点气恼。
“那倒也是。”沙哑的声音企图安抚对方,说道:“赵将军,事已至此,你就放宽心吧。你是赵家人,只要着力表现,熬上几年,还怕入不了“六卿”?大将军一定会关照你的。”
原来,声音低沉的,正是赵盾的堂弟——赵穿。
不久前,“六卿”又有一员空缺。赵穿得知之后,曾去找过赵盾,要求将自己纳入。不想,竟被赵盾一口回绝。回想当时的情景,赵穿仍耿耿于怀。
“堂哥,之前说是刚肃清“五君子”,不好用赵家人,以免落人口实。此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为何还不能将我列入?”在赵府,两人就是兄弟,而非上下关系。赵穿也不拐弯抹角,单刀直入主题。
“是,那事已经过去。可是——”赵穿性情冲动,实在不太合适委以重任。赵盾想直接说破,可是又怕伤了他面子,只得婉转道:“你还年轻。你看看,你做个附马爷,每天斗鸡走狗,喝酒赏花,不是挺好的?你想打发时间,在宫中也有任职,全在你能力范围之内,轻松即可完成。何必一定要这掌管军事,行军打仗的苦差事?”
赵盾对赵穿最大的期望就是——安分守己的做个花花公子,别闯祸闹事就行。
“堂哥继承了伯父大人的事业,光宗耀祖。小弟我也想为家族事业添份薄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如果堂哥总是用老眼光看我的话,我如何有机会成长?”赵穿知道,赵盾是吃软不吃硬,不能硬着来,只能软着上。
“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堂哥又没有日日在我身边,怎知我没个长进?前几年,我是太年轻,只知玩乐。现在已经修心养性,努力做事了。”赵穿说道。
反正赵盾也没天天盯着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夸得像朵花。不是曾经有人写信自荐,最后得到任用的?听说现在仍颇受堂哥赏识呢。
“我的小弟啊——”赵盾看着赵穿,越看越像牛皮糖。黏人不说,还韧性十足,不屈不挠的。
为这个位置,几年前就开始明示暗示。那时,他推说他年纪还轻,要多磨练几年,算是搪塞过去了。没想到,他倒像是蚂蚁遇到糖似的,念念不忘此事。而且还嗅觉灵敏,每次都第一时间就知道有空缺,真是让他头痛不已。
赵盾被逼无奈,只能把实情说出。“‘六卿’之位,每家一名,才能平衡各方。胥甲是众人推荐的,他是胥臣的后人,人品才华都颇受肯定。之前的栾盾,也是栾枝之后,不可能把人家拉下来吧?”
‘六卿’之中,荀林父家世显赫,资历最深。虽与赵盾不是同一阵营,自从羽翼尽失之后,算是接受现实,两人配合无间。
栾氏、胥氏的父辈都是贤能之人,立过大功,又与赵家渊源颇深。这两人,虽不是赵盾一力提拔,却与赵盾在家世背景上大体相似,正是赵盾想要的。这比用力提拔一个自己人更合理,用起来也更方便。
所以,赵穿还是不能用。除了他本身能力性格达不到要求之外,目前的形势仍是不允许。现在是大势稳定,内政变革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稳’字当头。赵盾不想太过强势,打破平衡。毕竟,此时的他,要的是治国成绩,并非战场杀戮取功。
“可是,臾骈并非功勋之后,不也位列六卿?”赵穿气急了。听堂哥的口气,‘六卿’之位,不管从前还是现在,或者未来,就是与他无缘就对了。依此推断,前几年说的要磨练他几年再说,不就是敷衍了事?他恼了。用出身来推托,他第一个就要把臾骈揪出来。
“臾骈已经位列上军佐,”面对赵穿突如其来的指责,赵盾只觉莫名其妙。“他的忠心耿耿、机智谋略、处事沉稳是有目共睹。我身处劣势能奋力一搏胜出,他可说是居功至伟。”
“有大功于赵氏,却从不邀功。这样的人,为何不能赋予重任?如果没有他的一臂之力,现在整个赵家都无一人在‘六卿’之列,还谈何光宗耀祖?”被赵穿一激,赵盾也恼了。
“我没说要将他拉下来,我只是……不服气。”赵盾不高兴,赵穿的口气也跟着软下来,“为何在堂哥眼中,我就是不如一个外人?”
“如果你不要一直把自己当成附马爷,赵家的少爷,你就能客观公正的认识臾骈这个人。”刚才太过严厉,赵盾也调整了语气。“我虽不是聪明绝顶天赋异禀之人,可是,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也成长了不长。自认也能分清贤愚不肖。”
“如果仅仅因为侍奉赵家两代,臾骈便能位居‘六卿’,赵府上下,多少仆役小厮都能做将军了?栽培弟弟们,是我身为赵氏继承人的责任义务,这一点我从不敢忘。可是,也要分清具体情势,还要天时地利人和,水到渠才成啊!”
赵盾的一番苦口婆心,不知这个贪玩任性又心高气傲的弟弟能明白多少?明白与否,他也只能言尽于此。他站的位置越高,看到的东西越多,需要兼顾的各方利益就越来越多。
以“五君子”事件为分水岭,他采取的政治手段、处事方式与以往大相径庭。外人不懂,他心里最为清楚。势易时移,许多变化是潜移默化,外人不足道也。
“既然堂哥心意已决,小弟也无话可说。”既无转睘余地,赵穿只得悻悻而去。
作为补偿,赵盾把赵穿派到此次战役。赵盾的本意是,把堂弟带到战场上来见识见识,磨砺一番,让他知晓行军打仗不是玩耍打闹,促他早点成熟懂事。
可是,赵穿未必能领赵盾的这个情。
两次争取都不能荣登‘六卿’之位,令他十分窝火。这把火,没法烧到出身显贵的人身上,臾骈,便成了替罪羊。从前,他对臾骈印象颇好。现在,一想到他,便觉得是眼中钉肉中刺般,恨恨不已。
尤其是想到,他出身低贱,竟然能列入‘六卿’,很自然的就将这一切归结为是沾了赵家的光。这么一想,更觉得臾骈就是个攀附权贵的小人,面目立马十倍可憎。偏偏替此役谋划‘只守不攻’计策的人,又是臾骈。赵穿越想越恼火,怎么哪儿都有他?臾骈的存在感越是强烈,赵穿就越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