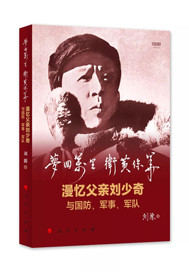这一夜,没有预想的半夜敲门。赵盾睡得格外沉。两日的疲惫叠加,将他击倒。直到仆人提醒,他抬头起身,发现东方渐白,又到平日里准备出门的时点。平时到点他自然会醒,想不到昨夜竟如此好眠。突然想起昨夜和臾骈的约定,他叫过仆役,问过府里上下,并没有人夜半来访。是不是意味着线索又断了?并不是先都所为?
带着满腹疑惑,赵盾洗漱换好衣服。刚出府门,远远就见臾骈骑马而来。
“大将军受累了。”臾骈对赵盾行过礼,赶忙说道:“昨夜没有追踪到有用的线索。让大将军担心一夜,属下有错。”
“没有一夜。”睡饱的赵盾,今日神清气爽。他笑着说:“以为有确切消息,不再担心,反而把前日缺的睡眠补足了。”
“大将军精神如此饱满,属下惭愧稍减。”客套过后,臾骈这才说起昨晚的事情。“昨夜属下派去的人,跟上了先都将军一行。不知是不是察觉了什么,他们出城后,很快就调头。之后,去到一家酒楼饮酒。期间只是闲聊,并没有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坐了一会,就往回走了。”
“好狡猾的先都。”赵盾发出一声感叹。不用问,对方应该也有人监视他们。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不可能大半夜出城又掉头。“一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
“我让他们一直盯着,直到先都将军回府。现在,已经换了一批人去轮值。”臾骈摇摇头:“我把昨夜负责跟踪的骂了一通,要他们下次务必小心,注意隐藏行迹。”
“不一定是他们不小心。”赵盾说道:“昨日下午,我们才开始派人跟踪他们,他们立马就察觉了。在我们的周围,一定也有他们的眼线。”
“现在怎么办?”臾骈想了想,“不如……请郤将军带齐人马,去昨夜所说的‘虎啸岩’搜查。我这边,把监视的人撤掉,静观其变。”
“也好。”赵盾想了想,认为这样可行。“我们派去的人太多,有一人察觉,其他人就会互通有无。今日暂时全部撤掉。等郤缺的人查找归来之后,就算要恢复,也只监视蒯得和先都。”
“大将军是说……”臾骈压低声音,“他们两人最可疑?”
“目前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二人,我们集中精力紧盯他们即可。”赵盾深信,蒯得一定牵涉其中。毕竟,他的反应太不合常理了。
主意已定。臾骈负责将赵盾的命令传达给郤缺,赵盾则前往官署处理政事。
刚到“丝纶阁”门口,刘进一脸焦急的在门前来回走动。看到赵盾,他“扑通”一声跪下,“大将军,小的昨夜一直等,却没等到消息。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不敢去将军府等赵盾,大白天的,太惹人注目。只能在此苦侯。
“快起来。”赵盾赶紧将他扶起。好好一个年轻人,浓眉紧锁,面容憔悴。为了先克的事,愁得像个老头。赵盾说道:“昨夜并没有收到有用的线索,所以就没去通知你。我也是天亮才知道的。”
“那……”怕耽搁太久,耽误赵盾处理政事,刘进急急问:“今日是不是要派人去‘虎啸岩’?我能不能去?”既然臾骈他们没有得到有用的消息,今天应该会改变策略。刘进早就想去‘虎啸岩’一探究竟。只是昨日被赵盾严令,不准私自寻访,只得作罢。经过一夜煎熬,他迫切的想参与到找寻先克的行列之中。
先克失踪后,老夫人整日跪在祖宗牌位前,求福祈祷。夫人则日日以泪洗面。从早到晚,足不出户。晕倒几次过后,喝点粥勉强维持性命。四大侍卫的其余三人,去先克带他们去过的地方,翻遍每寸草地,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刘进跟他们不一样,他自责内疚最深。他不满足于在外围乱跑,他紧紧追随赵盾。他希望第一时间拿到有用的线索,早点找到少爷。
其余三人也在找。但是,他们的心情,他们承受的痛苦,不足刘进的十分之一。虽然老夫人从未责怪过他们,三人也经常劝他不要自责,那次冲突纯属意外。但是,刘进没办法原谅自己。他跟先克年龄相仿,两人融洽亲昵。他们更像是好兄弟好伙伴,而非少爷与仆从侍卫的隶属关系而已。
得知蒯得与此事有关联,尤其搜得那张布帛时,他已大感不妙。心底有个声音,不断在耳边絮叨——少爷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他强抑这些杂音,告诉自己,无论是死是活,他一定要亲自带着少爷回家。所以,他迫切希望参与到大将军召集的搜索行动。如此,就能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备受煎熬的苦等。
“臾将军已经通知郤将军,今日带人去‘虎啸岩’找人。你去跟他们会合吧。”赵盾本不想让闲杂人参与。刘进年纪轻轻,为自家少爷如此掏心掏肺,他实在硬不下心肠。赵盾只得强调道:“不可单独前往。记住,一定要先找到郤将军的大队人马,跟他们一道。明白吗?”
“小的遵命。谢大将军,谢大将军,谢大将军恩典。”说着,刘进“扑通”一声跪倒,像死囚蒙特赦般感激涕零。说完,他转身上马,疾驰而去。
“这孩子,这两天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赵盾本想宽慰他几句,奈何他走得太快。又是哭又是跪,突然一刹那就消失在视野之中。想必他心中的痛楚已经深入肌里。重负之下,情绪才会如此高低起伏。
先克啊先克,你在哪里?你再不出现,有人会因想你日渐衰竭。有人会为你彻夜难眠,有人会为你操劳心碎。你究竟躲在哪里?赵盾喃喃自语。虽说精神好过昨日,可是一想到先克还不知所踪,心头仍是沉甸甸的。无奈一身官袍压身,职责所在。只得拼命维持,强打精神批阅公文。
另一边,“五君子”这边的气氛,显然比赵盾那边轻松得多。如果说赵盾他们是焦头烂额愁云惨雾的话,他们这边就是顺风顺水风和日丽。
“赵盾被逼去见君主时,脸色多难看?后来不也乖乖听命了?”先都先是一脸鄙夷,接着是一阵得意的笑。
“早知道,还不如早点听我们的劝。何必闹到君主面前那么难看?”祖产被夺走后,这是蒯得第一次露出笑容。
“你说,赵盾这次会不会又是拖延了事?”箕郑父问梁益耳。
梁益耳表情淡漠。他没有蒯得和先都形而外的喜悦,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好一会,他才说道:“据说,他已经把地方上书全部带回府了。他的办公署内,片简不留。你说,这是拖延,还是紧急处理?”梁益耳的回答,模棱两可。问题又抛回给箕郑父。
“我听说,军情不容乐观。秦军已经接近武城。看这阵势,不久便要攻占武城。这可是军事要塞,一旦为秦军所有,对我们十分不利啊。”士榖突然将话题转到晋秦两国的战役上。
“相信赵盾也收到了前方来报。”箕郑父明白过来,为何士榖突然插入一段似乎毫不相干的话。“如果这样的话,赵盾必须以对秦作战优先。那么,他应该不敢像之前一样,将我们的话再当儿戏。”
“而且我听说,既然秦军打来了,楚国也想趁机占点便宜。”士榖继续道:“一旦楚国动起来,郑国身处晋楚交界,首当其冲要选边站。陈国靠近楚国,有可能也被波及。”
“赵盾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硬脾气。”士榖和箕郑父说起对外关系,梁益耳也插嘴道:“就算秦军占领了武城,失去武城也不会威胁整个晋国的安危。不足为患。楚国本就是贪图小利的投机者,风向一对,捞点好处。风向不对,闻风而逃。楚国暂时也不足以威胁我国的安全。”
清了清嗓子,梁益耳继续分析道:“仅凭这两件事,不足以逼迫赵盾改弦易辙。除非,我们能造成更大的动荡,让他不得不被动应变。”
“我们目前造成的动荡还不够?”说着,先都颇有几分得意,“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四处……”
“不可说,不可说。”箕郑父坚持认为,越是做大事越要低调。所以,他制止先都,不让他往下说。
“军师以为——”先都望向梁益耳,“我们要怎样制造更大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