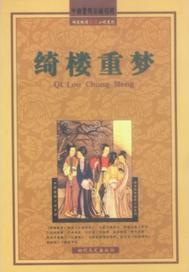“小沫,你去看看束阳是不是到了,我进屋去张罗张罗,让徐妈多准备些你们爱吃的菜,干脆晚上也别回去了,就在这住下,反正你们的房间徐妈她们每天都有收拾。”池利芳拉着烟小沫的手,笑盈盈地说着这些。
烟小沫看着姨娘脸上那舒展的笑容,也不好回绝,点了点头。
见烟小沫点头应承了,池利芳这边松开手,同着福叔一道进了屋,而烟小沫则是就着姨娘的意思朝大门走了去,看看段束阳的车是不是到门口了。
段束阳这段时间都很忙,每天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书房里,彼此间也没有怎么说话攀谈。上回听暮娟说,江都的案子是市委在牵线的,而段氏又是安城地产业的大户,说不定可以打听到一些事情。
段束阳下班后就直接开着车子到了庆安巷,路过警卫的时候,摇下车窗,警卫看见他人还有这熟悉的车牌,放行通过了。原本打算将车子直接开到池家门口,后来一想,就在警卫岗几米外找了个闲置的车位将车子停了下来。
简洁的白衬衫,袖子均卷过手肘,领口的两颗扣子不羁地解开着,他靠在驾驶座位上,目视着前方,漫不经心地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叨在唇间。
摇开火机,他点烟的时候眯了下烟,深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一个烟圈儿。
苏婉这次的安城之行,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在安城扎根五年里,除了最初的那半年里,接到过她的两通电话以外,他们之间几乎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而他也很少回北京,在安城,他有自己的家,在北京,她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彼此由最初的两条相交线,经过了那个交点以后,又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前进着,不再有交集。
袅袅的烟雾氤氲着他俊朗的面容,一抿一灭的星火在昏暗的车厢里闪烁着。就着巷子两旁的路灯散出冰冷又昏暗的灯光,段束阳远远地看见池家老宅的门口,一个瘦弱的身景站立在风中,不时地朝巷口瞭望。
段束阳抽完了烟,穿上大衣,拧起副驾座上装有锦盒的牛皮纸袋,下了车,并没有急着往池家方向走去,而是倚在车门边,寒风从巷口呼啸而来,带着深冬里的冷意,刮在脸上,生疼生疼的。等到身上的薄凉气息完全覆盖了那股尼古丁的味道后,这才迈开步子朝老宅的方向走去。
刚下班的那会儿,暮色四合,残阳如似,整个安城都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像一个身披彩霞的仙子,到这会儿,天色昏暗,冰冷的路灯散发出没有温度的光。
烟小沫双手环抱着自己,两只脚一起一落地规律地碰撞着地面,鞋跟与地面的撞击发出“蹬蹬”的声响,双手哈着气,不时地朝巷口探头望。
福叔先前还说,段束阳的车子都进了庆安巷,这都等了将近快半个小时了,愣是人影都没见着。
“这么冷,怎么站在这里?”是段束阳的声音。
烟小沫一转过头,就看见段束阳呼着热气地站在跟前,冻得有些通红的小脸,红扑扑的,朝段束阳笑了笑,道:“来了,进去吧!姨父跟姨娘等久了的!”
烟小沫小跑着进屋,这个冬天真冷,才刚站在门口等了那么一小会儿的工夫,她都觉得自己都快给冻成冰疙瘩了。
看着烟小沫这模样,段束阳忍不住叹气,浅摇了摇头快步追上她,跟着她一前一后地进了屋。
得知段束阳来的信儿,刘应余早早地就被池利芳给拉下楼,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而她则是在厨房里跟徐妈一起张罗着晚餐,还不时地朝门口瞄几眼。
见着段束阳烟小沫两人一齐进屋,赶紧地从厨房里洗了把手,笑盈盈地走了出来,道:“束阳来了?”
“诶,姨娘,近来可好?”段束阳一边向池利芳问好,一边褪下身上的大衣,递交到烟小沫手里。
“好,就是你跟小沫都不常来看我们,这宅子里啊,就剩下我跟你姨父两个人,怪冷清的。”
段束阳撇了眼一旁打理他衣服的烟小沫,笑着道:“这不是怕给您添麻烦嘛,要嫌冷清,那往后我跟小沫隔三差五地过来噌饭得了!”
“那赶情好!”池利芳一听,乐了。
“刘叔在家呢?”一直都这么管刘应余称呼,跟烟小沫结婚快四年,段束阳也没有改过口,虽然池利芳一老说他,这么叫,显得不亲份,可也还是没有改过来,就这么一直叫,这都快四年了吧!
“束阳过来了。”刘应余低下头,沉着老花镜看了眼,道。
“诶,刘叔,一直都知道你喜欢骨瓷,特地托朋友从邯郸陶了几件送您,,我对这些东西也不太懂,也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今天特地带过来,您先看看成色?”段束阳一边说着,一边从牛皮纸袋里将锦盒拿了出来。
刘应余没有啥别的嗜好,偏偏就爱好收藏骨瓷,他的那些什么烟嘴啊,茶壶啊,茶杯啊,就连家里的那些碗,盘呐什么样的,都是骨瓷制品的。当然啦,也有几件压箱底儿的宝贝,可是,也只是心痒痒的时候才拿出来赏玩一下。
一听是从唐山那边弄过来的骨瓷,刘应余立刻两眼泛着精光,扶正了眼镜,看着段束阳将小心翼翼地将锦盒打开,待看到那盒子里面躺着的杯身时,就听见他笑着声来,道:“束阳啊,还是你懂我啊!这可真是好宝贝啊!”
听刘应余这么说,烟小沫也不免多看了两眼,红段面的打底绒布,静躺着四个杯身釉有五彩梅图案的茶杯,还有盖碗的配件,做工精致细腻,白如玉晶莹剔透,明如镜光可照人,一看就价格不菲。听说钓鱼台国宾馆里招待外宾用的都是从唐山那来的骨瓷器,也难怪姨父喜欢得紧。
PS:终于忙完了,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