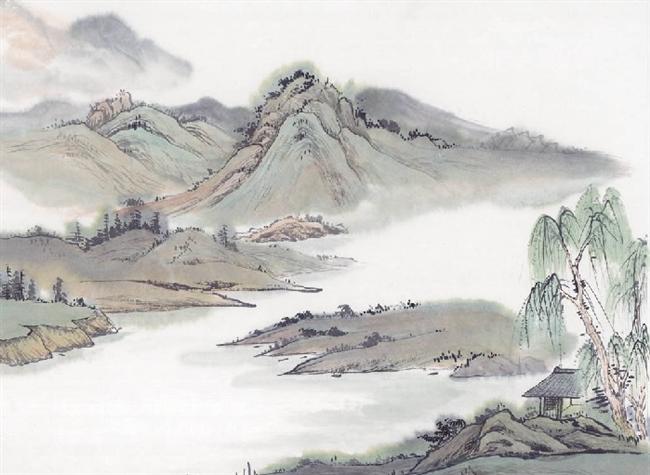宴席将近深夜才结束,沈牧迟什么话也没有,带着碧落就离开了。人群四散中,采苓同他们走散,再找到秦王府的马车时,驺子已经策动缰绳,马儿也开始缓步朝前,太子的车马动后,后面诸车才能缓缓往前。
采苓于人潮涌动中目送太子的马车渐行渐远,陶陶不知何时已站在身后,“看来只能由本少送你回去。”
回程的马车内,陶陶极尽聒噪,将今夜之事不由分说地详细叙述了一遍。说到眉飞色舞处,口沫横飞,“姜少,你可真是烈女子,平常人哪里敢那样磕头,直把额头磕出血来,那尚书府三小姐素来嚣张,今日闭着眼睛不敢看。”
采苓心事重重,本不愿说话,看他一派幸灾乐祸的模样,忍不住狠狠盯着他。
那只不怀好意的手抚在额头上,极是轻柔,面上的笑容却带着几分调侃,“本少刚开始以为你是做戏,没想到还真是渗了血。”
“疼!”采苓没好气道。
“要不要去找郎中瞧瞧?”陶陶这才有了三分正经。
采苓当头嚷道,“除夕深夜里,你去找个郎中出来给本少瞧瞧!”
“那你这伤的可真不巧。”陶陶故作焦虑样。
采苓闭起眼睛,身心俱疲,早说不出一句。陶陶自讨没趣,只坐在一旁不再惹她生气。
陶陶将之送到王府大门前就要走,采苓没好气道,“天色如此,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进去。”
“府内自然安全。如今三殿下情绪不稳,本少还是保护好项上人头要紧。你我几日后便可在东喜楼再聚。今日后本少更敬重你几分,届时东海鲍参、山中珍馐皆算在本少头上。”陶陶向采苓拱了拱手,便催动驺子速速策马。
毕竟是除夕,王府虽大,处处院子张灯结彩,红灯笼高挂,竟将黑夜映得如白昼一般,欢声笑语仍在,所行之处满是生气。采苓心中却五味杂陈,想到渊儿还在等她,便是一阵急行。
推开院子的小门,见到屋内昏黄的烛光,心中瞬间安定。屋内,漫云在榻上绣帕子,渊儿枕在她腿上睡得安稳。采苓轻轻走近,看着他红扑扑的笑脸好生可爱,不由露出慈母般的笑容。
“哎呀。”漫云低叫一声。采苓转眼瞧去,见漫云将绣花针刺在自己食指上,目光却紧紧盯住她的额头。
采苓替她拔了指腹上的针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后,才道,“无碍。”
漫云小心翼翼将渊儿放平,才去帘后取来绢布和药膏,“幸好当初留下一瓶,不然这除夕夜里也不知该去何处讨药。”
采苓静静坐着,任由漫云将冰冰凉的药膏涂在她额头上,有些刺痛,药味浓重,她只强忍着。直到擦完药,漫云要将长长的白色绢布裹在她额头上,她才笑道,“这就不用了吧?好像不太吉利。”
漫云连连点头,又要去帘后找其他颜色的绢布,小榻上的人儿翻身缓缓睁开眼睛,睡眼惺忪、模模糊糊开口,“姑姑……”
既然渊儿强行醒来,答应他的事情到底不能不做。采苓让漫云将前几日赫悦送来的一包纸炮放在院中,便拿着火折子要去放炮。
这炮竹是稀罕物,采苓同漫云小时候都没玩过。渊儿年幼,自然是只能远观不可亵玩的。采苓鼓足勇气站在院子中,一手拿着炮竹,一手拿着火折子,往火折子吹了几口气,火折子里便有火苗跳动。
“姑姑快去点炮竹上的细丝儿。”渊儿兴奋地跳跃起来。
采苓战战兢兢很想放弃,可见渊儿满是期待的目光,只好将颤动的手移到炮竹一头,火苗迅速传递到细线上,火星噼啪,采苓吓得尖叫,随手将那炮竹扔出老远,跌跌跄跄迅速跑回。
只听“砰”一声急响,却不见火花,唯有两声女子的尖叫。采苓问:“炮竹呢?”
渊儿和漫云无可奈何地看着她,指了指院外,谁曾想她竟然吓到将炮竹扔出了围墙。她哪里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本事,非要去围墙外找那半截炮竹的残骸。漫云劝道:“那么小的炮竹,怎会好找?”
“那么小的纸炮,怎能被扔到院外?”她笑道,刚拐出院子,一抬眼,见两盏琉璃灯摔在地上,两名丫鬟正吓得瑟瑟发抖。采苓心中有愧,忙要道歉,于那琉璃灯的光影里看清站在丫鬟后面的人,长身玉立,正是太子沈牧迟。
彼此对视片刻,默默无语中仿佛过了天长地久。采苓看见沈牧迟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夜里却很难看得真切,她便不自觉走近了两步,沈牧迟却将手缩了回去,转身正要走。
漫云带着渊儿一路笑闹着出门来查看情况,见了太子,知道刚才那炮仗冲撞了殿下,心叫不好,连忙拉着渊儿跪下。
渊儿强撑起头,嚷道:“姑父!姑父!”
采苓巴不得赶紧捂住这小子的嘴巴,却见沈牧迟止了步子。渊儿顺势乞求道道,“姑姑她不会放爆竹,实是无用,姑父乃人中翘楚,一定会放爆竹吧?”
沈牧迟身子一僵,采苓嗫嚅道,“三岁稚童,语无伦次,殿下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姑姑!我今年四周岁!”渊儿不依不挠。
她当然知道他四岁,只是说小一点方应了那句童言无忌,可这孩子怎么就这样不上道!
“好!姑父同你放。”沈牧迟再转过身,已是和蔼慈祥。
那一夜除夕,全城喜气洋洋一派祥和,秦王府内炮竹声连连,孩童嬉笑声不断。直将几杆爆竹、一堆纸炮放干净,渊儿才心有不甘地拉着漫云的手去睡觉。
“今日之事是我莽撞,早该同你商议。”采苓将太子请进屋,面有愧色。
“册立太子妃之事,确实是本王思虑不周。”他忽然道歉。采苓最担忧的莫过于因此事与沈牧迟交恶,若是能推心置腹讲讲各自的难处,真是求之不得。
再开口时,已是面上含笑,“我很感动。只不过……”她想说“朝廷之内后宫之中早无我容身之地”。
“不过是本王随性为止,你不必放在心上。”他喝了口水,说得云淡风轻。
像是有刺卡在咽喉,她半天说不出一字,良久后,笑问:“手里拿着什么?”
“给你的。”他随手扔过来一个瓷盒,瓶身带着他暖暖的温度,正是宝和林的白玉膏。采苓打开盒盖,立即看出不同,平常得来的白玉膏有草药味颜色偏黄,而这一瓶色如羊脂香如芙蕖,可谓白玉膏中的珍品。
“谢了。”她正要将那瓷盒盖上,沈牧迟的手指便伸了进去,沾取膏体往她额头上抹,她本想躲开,可见他严肃认真的表情,又不敢躲,只怯怯道,“我刚才有擦过药。”
“每日三次,不许偷懒。”他冷冷道。她忙着点头,熟知他手中动作未停,那白色的药膏就直端端涂在她头发上,她连忙手忙脚乱去整理乱发,见她如此,他才渐渐有了笑颜。
“明日你就出府去吧。”他的目光瞧向轩窗外,月色如水。
“嗯。”她垂目。
“往后多加小心,凡事与人商议,不可再伤了自己。”他如长者般淳淳教诲着,令她心上生出许多不舍,却竭力掩饰着。
“本王走了。”他站起身,目光幽深,再细细看了她两眼。
“恭送殿下。”她屈膝埋首,不敢让他瞧见眼中的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