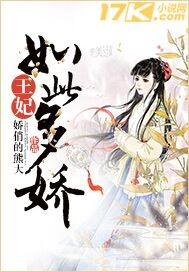王爹封侯拜将,成为当今圣人的宠臣。汤瑄的父亲是恰恰也是圣人宠信的文臣,然却与王爹一派素来不合。
汤瑄是文臣的公子,我是武将的女儿。他生性温润善良,待我极好,好的让我心生错觉。
原本门第相当,可他却对太行院的师兄弟说,文脉清流,此生绝不娶武女为妻。
我听说了以后,便渐渐凉了心,开始慢慢与他疏离,暗藏起那一丝初生的情愫。
那日,听歆儿师姐说,汤瑄的父亲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是另一位文臣家的女儿。
他大婚那夜,我在长安城明明灭灭的灯火下,哭成泪人。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几年后,王爹将我许与朝中他的亲信之子。
我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心魂的木人,嫁与谁又如何呢?不过是一块行尸走肉。我恨我自己,不够勇敢、不够直白。
一日去长安云殊殿上香,拜了菩萨;合十凝望菩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心底的那尊佛,从来都是他。
一直在心里,从未敢忘。一切不过是因缘交错。
再遇的时候,他看我的眼神,依旧那样温润清泠。
“师兄近来过的可还好?”我问。
“终是不负众望,武状元已是囊中之物。”他笑曰。
那甚好。”我不由讥讽道:“如此,你亦是当朝的武将了;却为何那时,瞧不上将门之女呢?”
他一愣。我亦不再言语,同他擦肩而过。
汤瑄的府邸,恰好在我隔壁,隔着府中的一道矮垣,那里的花谢花开,秋枫白雪,幕幕皆在眼前。
他临上沙场那日,漫天梨花如雨。他隔垣对我深情一笑,却无片言半语。
从初见到如今,无论那人最后变成了什么模样,终是我心里的那抹梨花白。我终于知道,我仍是放不下。
来年梨花开时,他从战场上归来,而他的娇妻,已为他诞下一位麟儿。
明月下、碧窗前,他那双相识的眉眼,仿佛历经几生几世的熟识。梨花雪中,凝笛舞剑的白衣人,几曾梦里见过?
情不知所起,偏到如今,方觉一往情深。而一切为时晚矣。
妇人为他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花前月下。吾也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直到色衰爱迟。
我嫁与的这个男人,纳了一个又一个的外室。我则躲避着隔壁那家人,常年宅于府足不出户,只以教子为乐。
汤瑄因作战有功,升官拜爵,圣人在长安城中的兴化坊处,另赐了他一方官邸。
自他搬走后,冬去春来又是十多年;隔壁原本荒芜的院落中,惟有梨花还绽如烟萝。
当孩子们各自嫁娶,我亦步入孤寡之年;终于肯越过那道矮垣,去看一看、抚一抚,留有当初那人余温的地方。
漫天梨花飘落如雪,像极了当初方遇的时候,那人清瞳如水、眉鬓含英;一袭白衣胜雪,黑发如云。
屋内一张木几上,留有两句字痕浅白的诗:别后空一水,重来已三生。
那熟悉的字痕漫入眼底,想来是他当初临征战前,留给妻子的情笺。
我隐在心中多年的泪,终于倾泻而出;是啊,原来他,就是我心里,守了一辈子的梨花白。
晚春的风卷帘而入,梦里的梨花香拂面而来。我拭去泪痕,见庭中那棵梨树下,依稀坐着一个眉眼含英、手持笛剑的白衣公子,深情宛宛地笑着,轻轻说:“嘿!我知道,你心底那抹梨花白,从来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