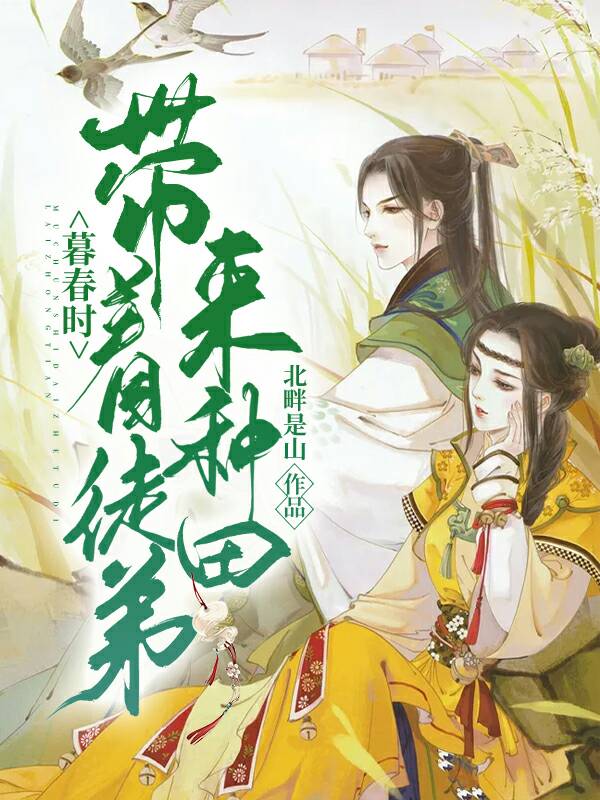黑格尔在原则上是反对表演对于戏剧文学的脱离的。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剧本只给演员提供了一个框架,一种机缘,剩下来的一切都得让演员按照自然、习惯和艺术要求去任意自由支配;或者认为舞台上要展现的只要是演员的灵魂和艺术,剧本只成了一种附属品。这种表演主张在意大利人的某些喜剧里体现得特别明显,结果剧本无所谓,角色类型化,观众只捧专长一艺的演员。黑格尔把这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演风,指出:“单凭纯粹的自然主义及其生动的老套,并不比单用性格特征的简洁易懂的描绘更能触及事情的本质”。
另一种脱离戏剧文学的倾向是转向炫耀奢华一途,不把剧本内容作为全剧的关键,喧宾夺主,让辉煌的舞台装饰和艳丽的服装之类的附属品“变成占优势的独立因素”。古代罗马悲剧的演出和近代的歌剧大多有这种倾向。黑格尔认为在这类感性外表的装饰上精工雕琢对内容的表达不仅无补,而且有害。他深刻地指出:“如果在布景,服装,器乐这些艺术上费尽了全力,真正的戏剧内容就不会受到认真对待”,“这样感性方面的富丽堂皇当然往往是已经到来的真正艺术衰颓的标志”。至于芭蕾舞,除了舞台装饰的考究外全力倾注于灵巧轻捷的双腿,这也是黑格尔所不满意的。他也不要求舞蹈表现太丰厚的精神内容,只要能从中见到“一种节制和灵魂的和谐,一种自由活泼的娴雅风度”就好,可惜并不多见。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戏剧文学也要力求适合表演。戏剧的价值在于上演,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提供内在的戏剧的价值的主要是一种便于上演的动作情节”,既然如此,不便于上演的剧本再有文学价值也是失败的。
是不是一定要每一个剧作者全都精通表演、谙熟舞台呢?不必。黑格尔把两种情况划分了开来。一种是剧作者不一定要了解的知识,如换幕换景时布景的更动,演员换装和休息的时间,要是剧本忽略了这一些,一般说还不影响剧作的价值,在实际上演时调整改动也不难;“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些其他因素却是诗人想达到真正的戏剧效果就不能不注意的”,这主要是指实际表演、实际动作,剧作者在动笔时如不时刻考虑到,就要出大问题。
以戏剧语言为例,如果把对话写得像写信那样,斟字酌句,表演时说起来就显得很不真实;写对话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表演,黑格尔主张把剧中对话写成“临时的实际谈话”的形态。这种谈话方式是在没有反复考虑余地的情况下直接表现心思和判断的,“只是眼对着眼,口对着口,耳对着耳,直接把当时心里话说出来。在这种场合,动作和话语都从人物性格中生动活泼地流露出来的,不去在多种可能性之中进行选择”。演员在舞台上想要表演,而且最适宜于表演的,正是这种生动活泼的自然和真实。尽管黑格尔说过,那种不为上演的剧本也可能有艺术价值,但心底里却很不喜欢这种剧本,为此他甚至主张今后不要再正式出版印行剧本,让剧本只与剧场和演出发生关系,这会使那种不能上演的剧本少出来一点,少让人看到一点。他对这类剧本的棒点作这样的概括:“用的是有文化修养的精炼语言,表达的是高深微妙的感想和深奥的思想,可以缺乏的正是使戏剧成其为戏剧的那种动作情节和活泼的生气。”“使戏剧成其为戏剧”,这是一个多么简单而又重要的命题!
因此他进一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舞台表演确实就是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总之,表演和戏剧文学只有互相照应,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
黑格尔的这些意见,以高度的艺术鉴赏能力缕析了戏剧领域中的一系列具体艺术问题,剀切中肯,反映了他的美学体系与艺术实践的连结。
他在表演艺术方面的研究,细致和内行的程度不让于专业的戏剧评论家,而在概括和分析上又显出了他的理论能力;他在这个领域里指出的一些时弊,事实证明,在他之后还长期存在并流播益甚,这又反映了他的美学体系与时风流俗的联系。凛然而又缈然的理念统辖着他的美学和戏剧理论,呈现出一派深奥玄秘的气象,但当这些理论层层伸发、落实,终于与现实的艺术土壤扭合在一起的时候,又使人感到亲近和实在。可惜他的理论结构与土壤接触的是枝叶而不是根,根在虚无缥缈间,在那个冥冥之中的理念天国。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首尾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