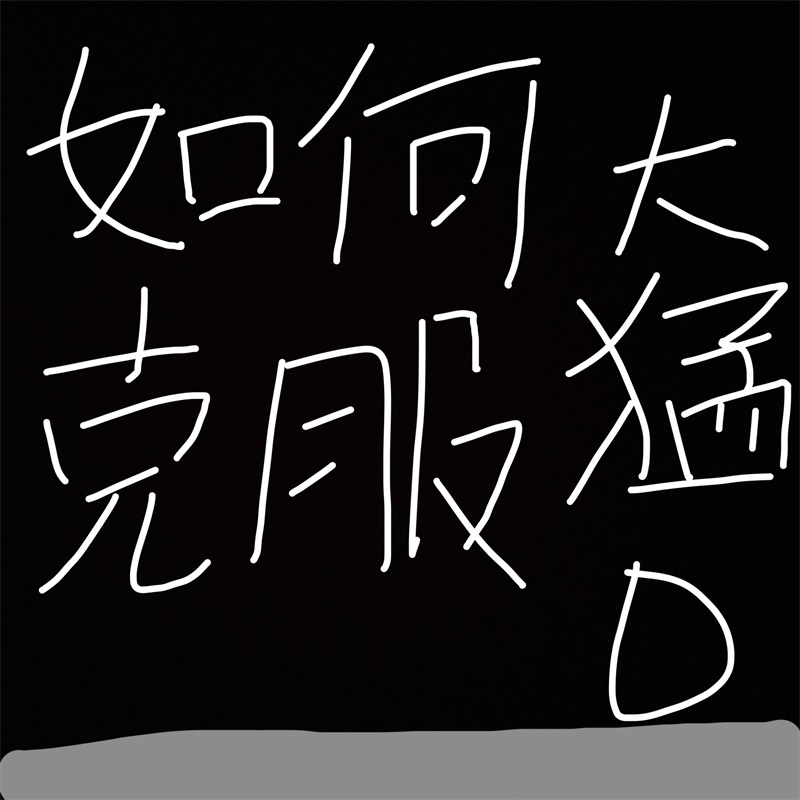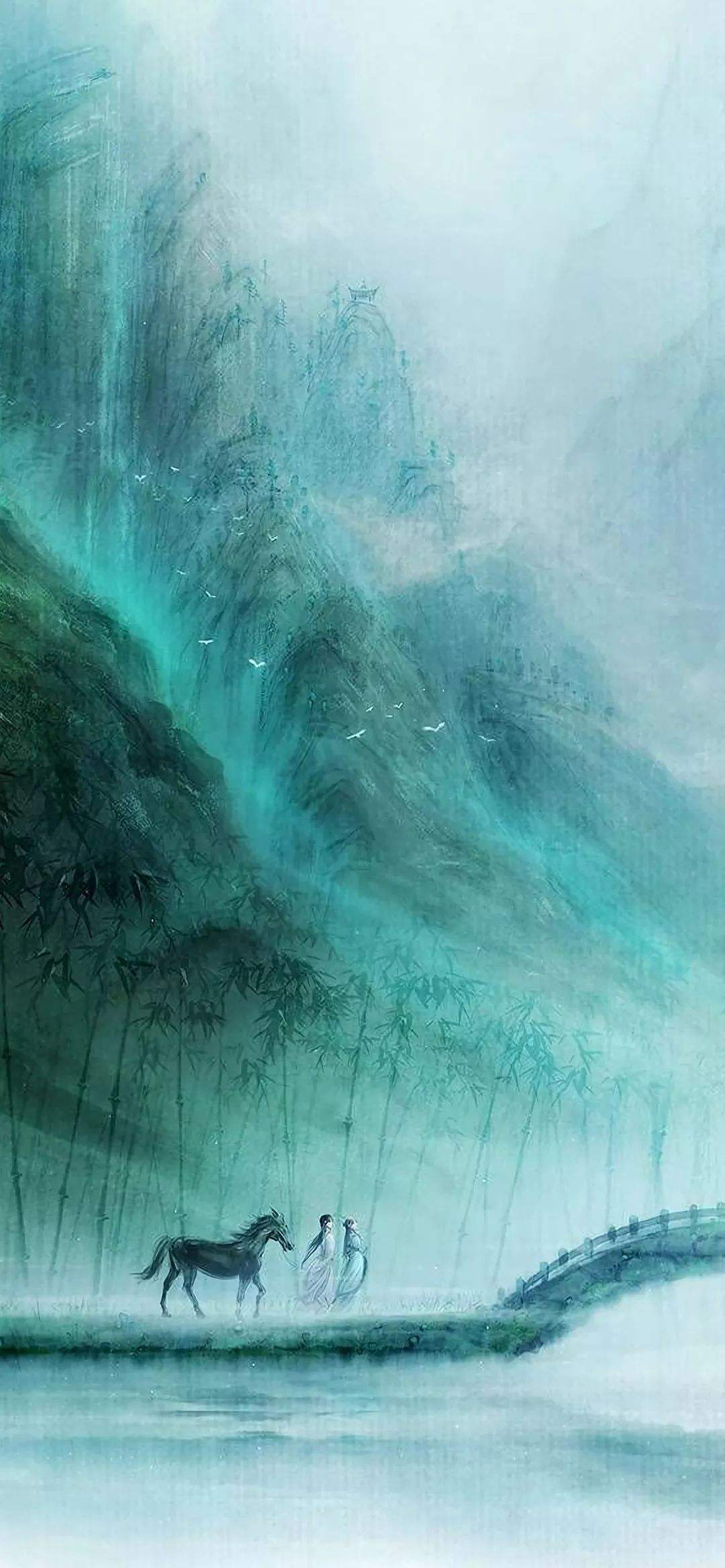冬天太阳一大早托着羞红的圆脸从云彩里钻出来了,越来越温暖,透过房屋的窗户,越来越晒在香莲的屁股上。
“香莲,你个死妮子,起来了。你舅母在等着你呢。"香莲的娘一把就把《拇指姑娘》的香莲从被窝里拎了出来。
“又咋的了,娘。”香莲睁开惺忪的睡眼,赶忙问。“哎呀,娘哎,我这就起来,咋把你说的事忘了呢?”香莲在床上胡乱抓着。
“香莲,你起来,好好收拾一下,都老大不小了,还是打扮一下吧,你在不着急,你娘就上火了。”香莲的亲舅母说话香莲就觉得味道怪怪的。可她娘就喜欢听。香莲就觉着看得出亲舅母是她娘的亲弟媳妇,说话就是不一样。娘听着就来劲。
“香莲,你个死闺女,你听你大舅母的。你瞎摸索啥,眼睛瞎了,把今冬刚买的红妮子大衣穿上,给我弄个人样,别再给我丢脸。”香莲的娘立即又有了骂人的精神头,但对于上次相亲香莲那副邋邋遢遢样子好似"心有余悸"。
“哦”,香莲答应着,“舅母,你坐下喝点水,等一等,我这就收拾一下,咱俩就走。”香莲招呼着她的亲大舅母,然后端了脸盆洗脸梳头去了。留下她娘和她的亲大舅母在那里嘀嘀咕咕着。
香莲一边走,想起她娘拜托她亲大舅母给她提的她的同学的哥哥,香莲那时还觉得自己年龄小,不着急,再说同学的哥哥都认识咋好意思的。虽然到了自由恋爱的季节,可是香莲不会啊,就像她的娘说话不会拐弯抹角一样啊。细细的回味着亲大舅母的话。老大不小也不是自己长得,岁月熬得谁能不长大啊!
香莲仔细的洗了脸,慢慢腾腾的梳好丸子头,这不是农忙的季节,香莲还把脸上涂了点雪花膏。找出今冬刚买的石榴红裙式大衣,前边一排金黄色菱形纽扣,当时流行的娃娃领,下边是太阳裙裙式摆尾,脚下一双磨光的四分跟软牛皮鞋,娇小而玲珑。香莲走到正嘀咕的娘和舅母面前。
“好了,舅母,你看这么行吗?”香莲试探的问。
“行啊!香莲。这不也挺会打扮的吗!真是人靠衣衫马靠鞍啊。”香莲亲大舅母眯着眼,上下打量着。香莲的娘也有点眼睛放光了。
“哎,要是香莲再高点多好啊!”香莲的娘不无遗憾地说。
"人无完人,这就很好了。走走。”香莲的亲舅母说起话来,香莲总是觉得味道不一样,也听不出哪里不一样,就是觉得不一样。
“她大舅母,这回就靠你了。你看着点,见机行事,人家不乐意,就领着咱香莲快回来。你也不尴尬为难,香莲看不出来的,你就给她看着点。”
“娘,你叨叨啥呢,又不是上战场,成就成不成就拉倒。”香莲不让娘说了,按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同事丽萍跟她一起探讨的箴言,香莲彻底明白爱情的缘分就那么回事。哪有娘眼里这么不值钱的自己,还指不定谁不看好谁呢!
“你就放心吧,姐姐,香莲又不是傻瓜,这人家乐不乐意,香莲精得很,比咱眼里看得明白。”亲大舅母安慰这香莲的娘。推出车子和香莲骑上,直达止埠村。
进了村头,就是一家不起眼小饭店,陈设简单,外边也没包装,也没打什么广告,简简单单能看出《家常饭店》四个字,香莲的亲大舅母说“就这里了,我们进去看看吧。”香莲知道娘跟舅母都嘀咕了,香莲也不用问,停下车子,就跟大舅母进了屋里头。
进屋里,靠窗下是一张小床,小床的前边是一个柜台,柜台外边的地板上摆了一张吃饭的小桌,桌子前后对着两张凳子,墙上贴着菜单。靠里边的墙角柜上摆着酒香烟等等一般饭店需要让顾客取用的东西。再靠后墙的桌子旁边有一个往里走的内门,内门通着里面的大院,和北面的正房。开饭店得这一间是这座宅子的西屋,西屋靠着马路,开了一门然后就做饭店用了。
听亲大舅母说是小伙子租的。香莲正打量着,里边走出一个个子不高面色黢黑的小伙,和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抬着一张桌子进来了。
“里边坐,里边床沿上坐。”小伙招呼着,和那个大哥把桌子放下。屋里实在太窄,刚好容下他俩从那个内门进来中间摆上这张桌子
香莲也不客气,拉大舅母就进门坐在里边的床沿上,“我还得去搬两张桌子,你们等一下。”
小伙子说着就跟那中年男人走了。
“香莲,是不是就那小伙子,咱来了还这么忙。就让我们在这等着。”香莲的大舅母撇撇嘴。
“咱还的坐床沿,这吃饭桌的凳子还没让我们坐,这什么意思?我们在这等着,他们自顾自去搬他们的桌子?!”香莲有点光火。
“看看再说,香莲,先别急。”亲大舅母看来是记住香莲她娘的话了,“见机行事”。
“好吧,我们出来等等吧。”香莲说着人已经到了马路上,刚好看见那小伙子和那个粗壮汉子抬着桌子过来了,看见香莲他俩也没再吱声。
气的香莲推起车子就走,她舅母就在后边赶。“香莲,等等我。”
“还等啥,快点走,回去我还得上班呢!"。香莲也大声的说着,唯恐小伙子听不见,特别加重了语气。
舅母尖着嗓子的声音小伙一定听得见,被放了鸽子的香莲也是气咻咻的,谁家不要尊严,自己难道就这般那寒碜吗,无事相什么亲,自找晦气。不过香莲也很轻松,任凭你大舅母怎么怎么滴,小伙也一般模样,他瞧不上我,我香莲还瞧不上他呢!我香莲再怎么寒碜,也不至于自己把自己贬到地里。香莲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相亲。也是最丢人的相亲何况后边跟着原先给她保媒的亲大舅母。
大舅母一会赶上来。“小伙一般,咋还一点礼貌没有,成不成也得走走过场呀。”
“走啥走,咱走了不就是过场了。”香莲漫不经心的说,好似不是她来相亲的。有大舅母这张嘴,香莲娘那儿咋交代香莲是一百个放心了。
冬天的风干巴巴的吹着,吹在脸上就像刀子割一样的疼。香莲的娘为了香莲的婚事彻底崩溃了。对待香莲就像屋上的积雪几经风吹日积成了太阳也化不了冰。娘俩从最后一次相亲后成了彻底的冷战。香莲的娘也冷得似冰霜,香莲的心更像冬天的冰。除了上班,吃饭,睡觉,就是茅厕,上班,吃饭,睡觉......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红莲因为怀孕了,婆家怕吃不好,几乎不叫她怎么回自己家了。母亲的脸本来就像冬天的霜,被风一吹,越发显得脸上的皮更紧了。再加上香莲的婚事,一见着香莲,那简直是阴的就像天天不见太阳,冰雪漫天飞舞的天空。香莲更不想自讨没趣,就变着法想躲着她娘。娘在家,不是去睡觉等夜班,就是上白班,反正香莲觉的对着脸的日子越少越好,不见更好。到了休班的日子香莲就想跑姨家去躲着她娘,就是不想她娘见着她的影子,俗话说得好“眼不见,心不烦。”
香莲的二姨是个高挑的女人,也长着杏仁眼,说起话来颤悠悠的,跟香莲娘真是一个娘生不一个娘养的。香莲的姨夫瘦高个子,会做木工手艺,香莲有三个表妹,一个表弟。香莲二姨为了生香莲的小表弟历经千辛万苦,老来得子,这点随了亲生的娘,香莲的亲姥爷老来得子。八十年代封建残余重男轻女的陋习还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到了今天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男多女少的比例严重失衡,促使人们的思想完全解放才再也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那年头,香莲的二姨为了生香莲的小表弟流了不少的泪呢。最后才终于如愿以偿,香莲的二姨才有了笑容。
大姨家的表哥姐都成人了,表嫂子进了门,大姨哄孙子孙女不在家,去了就大姨夫在家香莲觉得没趣。最小的姨正是拖儿带女的时候哪有时间管她。
二姨家的表妹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过比香莲小几岁,二姨还不着急。所以最后香莲决定去二姨家。
香莲二姨的家在正庄,庄头住着是香莲的大姨,庄尾住着香莲的二姨。香莲的二姨从小做了张家的女儿,是香莲的大姨偷偷的抱出来的,自然后来认回自己的娘亲也不算稀奇。在香莲二姨的养父很早得病走了,她二姨的养母没生育,就香莲二姨一个女儿。只有娘俩相依偎命。
香莲的姥爷怕娘俩受人欺负,就托香莲大姨认回了香莲二姨。香莲听她娘说,香莲的二姨起初也是不乐意不明白为啥把她送出去,直到香莲的娘去说了实话为什么,香莲二姨才原谅了父母,偶尔来走动走动,等香莲二姨的养母也走了,香莲二姨也就跟香莲的姥姥姥爷越走越亲昵。现在香莲的表妹表弟也都长大了,小表弟很争气还考了名牌大学,二姨就越来越是开心也越来越自信了。香莲二姨养父在世的时候供着她二姨读了识字班,后来还上了高小。香莲二姨不仅识字而且有文化的人,香莲跟二姨待得不多但是也是最谈得来的人。
推开香莲二姨家的门,原先是个很深的院子,但是在九一二年香莲二姨夫翻新了。改革开放后,香莲二姨夫的木工活做得好,翻身也快,很快盖起了红砖青瓦的大房子。进去客厅,正面是香莲二姨夫自己做的雕花椅子和大方桌。香莲二姨夫妇都忙着挣钱,家里也没什么讲究,什么卫生不卫生,就是简简单单的就好。
“二姨,在家吗?”香莲推开门,轻轻的呼唤二姨。
“在呢,谁呀?”二姨惊异地问,推开北屋门,一个头上蒙着围巾的长得跟香莲娘有着一样的眼睛,但看上去比香莲娘还年轻的妇女从屋里出来了。这就是香莲的二姨。
“二姨,是我。”香莲笑着回答,“表妹在家吗?我找她们玩。”
香莲的二姨看到香莲很是高兴:“香莲,你咋不来玩了,上班没时间是吧?二姨在家不一样吗,尽管来玩,你表妹上班去了,上白班呢。“香莲的二姨热情地接待着香莲。
“二姨,我真想来你家,我娘天天给我甩脸子,我受不了了,想来对你说说,又怕你忙没工夫,所以说找表妹玩。”香莲干脆也不拐弯抹角了,无限的委屈好似终于找个倾诉的地方,找到了一时的解脱。
她有好多问题,请教二姨,问问有文化的二姨,什么是爱情,面对自己没着落,妹妹还急在眼前,弟弟也也等着招亲了,还有母亲眼前的冷战,面对眼下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啊。这是香莲眼下的最着急的问题也是解不开的疙瘩。
香莲知道和娘的冷战只要开始,总有一天迟早会爆发。香莲只想躲一天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