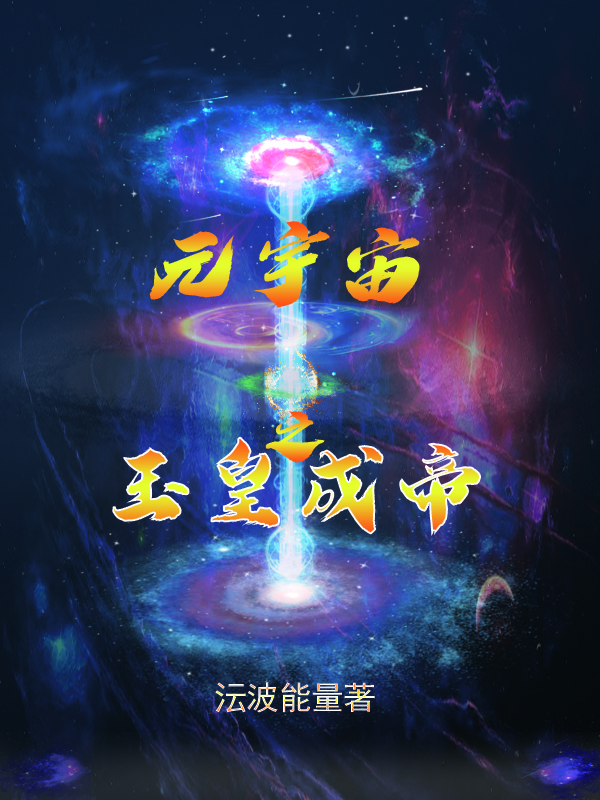白阿婆的尸体是放牛娃在山涧第一个看到的,半路说给了刘全胜和儿子苦娃,刘全胜怕尸体被狼或者其它野物抬去了,就让苦娃到村里找舅太爷,他跟着放牛娃去了溪边。
舅太爷去的时候,天正晴好,溪水闪着银光,山涧的鹅卵石如一颗颗白色的鸭蛋铺着,一丛丛的草绿的刺眼,白阿婆浑身湿漉漉的躺在水边,她的衣服上有血迹,头也磕破了,皱巴巴的褐色皮肤此刻成了灰白色,在溪水中泡了一夜,已经浮肿的不成样子,就跟泡了的馒头似的,动一下就要散了。
庄里又来了几个人,赶着牛车,拉着门板,小心的把白阿婆抬到了上面,舅太爷亲自牵牛,把尸体送到了桃源镇南的白土坡,一路上有不少人打问,得知白阿婆殁了,纷纷唉声叹息,都说她活的苦,死得冤,多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走了?
白阿婆一生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她给人接生了一辈子,自己却没留下一儿半女,没人养老送终,也没能寿终正寝,她就想再接生一个孩子,完成在后土娘娘跟前发下的愿心,可到底是没能实现,没有圆满。
只叹:黑也无常,白也无常,人世无常啊!
舅太爷牵头,在几个地主爷的帮扶下,给白阿婆办了丧事,她活着的时候,过的清苦,死了倒是风光了一回,麻先生写的诰牌,罗汉爷念的经文,曹阴阳点的坟头,吹鼓手送的葬,埋在青山头,左右绿树掩映,背山望水,人人都说是块风水宝地,住进了凤凰穴,要升天做娘娘,有发善心的老爷出钱,推倒了白阿婆的房子,在庄廓上建了一座娘娘庙,麻先生捉刀写匾,题了四个大字‘白阿婆庙’,前往的人甚多,香火鼎盛,听说很灵验,即便是特殊时期破四旧,也保留了下来。
有年我去白土坡,有幸见到,虽还在,却也是门庭冷落了。
白阿婆最后一个接生的是我阿婆金莲,人都说金莲命贵,可她却苦了一辈子。
我阿婆干活泼战,能顶几个男人,她杀过土匪,进过山林,狼嘴里抢食,洪水里捞椽,她七岁就能背着一百多斤重的麻袋在山路上轰隆隆跑,用天生神力来形容也不算过分,都说她长大后更不得了。
金莲这个名字,还是我阿婆出月的第二天,舅太爷特意跑到桃源镇上请有学问的老秀才麻先生给起的。麻先生本姓刘,满脸麻子大家才这么叫他,就因为我舅太爷在他儿子的宴席上,不小心打了一个兰花儿碟,就心上不到,嫉恨下了,给起了一个金莲的名字,说五行缺水,莲生水中,得水之气,顶好!
这是人说的话吗?
酸秀才坏起来,那是坏到骨子里了。
在与世隔绝的桃源镇上,牛大的字能认一个的人都少,更别说读《金瓶梅》这种大作了,就是连听都没听说,更不知道“千古第一淫·妇”潘金莲的恶名,不然以我舅太爷的牛脾气,要断他的腿子都是轻的!我舅太爷还给他好几个大钱,吃了忘八亏尚不自知。
在我的印象里,我阿婆长的不高,至于容貌如何,这是无法推断的,毕竟我有记忆的时候,她已经老了,她去世已经十多年,脑海的碎片,也逐渐模糊。她是圆脸,嘴角有一颗痣,银白的头发扎着两个长长的麻花辫,盘在头上,戴着一顶黑布帽,穿着黑色的大襟衣裳,黑色的大裆裤,系着黑布裤带,脚上是黑色绣花鞋。
我儿时最好奇的,便是她洗脚时掺下来的长长的白色裹脚布,怎么也想不透,脚上为撒要缠那么长的一条布,她每次都会遮住脚让我去旁边耍,总是说:“尕娃们看不得!”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双折断了的畸形的脚。
那条布,缠了中国女性几千年。
听说南方四五岁就开始裹脚,北方在七八岁,我阿婆金莲缠脚是在七岁半。
那是一个春天,早启时分的阳光分外清新,她走在宁静的村庄小路上,脚下是已经在此生长了千万年的草,远处的山丘从太古开始就存在,背篼里的牛草散发着清香,离庄里还有一段路,她便听到有读书声从前几天刚盖的私塾里传出,那声音时近时远,时断时续,难解其义,间或有三个哥哥的声音:
人子出,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狗不叫,新奶千。
骄子到,贵一砖。
羊不叫,斧子过。
窖不严,狮子多……
她停住身子往上抖了一下背篼,喘了一口气,继续朝着庄里走,在拐弯出山坡的土台上缓了一缓,然后卯足劲儿,一口气来到了泉边,正好遇见了蹲在大柳树下舀水的苦娃。
“苦娃,在担水呀?”
“你早得很么,阳婆儿才出来,你就割了这么一背篼草。”
“嗯,我先走了。”
“你赶紧到屋里去,背那么重的一背草,背篼系勒进了肉里,看的我肩胛骨都疼。”
“不疼,不疼。”
“不疼才怪哩,赶紧去吧。”
她应了一声,背着草上了陡坡,到屋里的时候,妈正在撵麻线,她放下草,从缸里舀了一盄(diao)子水,咕嘎咕嘎的喝了个饱,然后去堂屋里给娘帮忙。
快晌午的时候,达从地里回来了,三个哥哥也从私塾下学,妈摆了炕桌,金莲在锅头旁等着抬碗,洋芋拌汤里的葱花散发着香气,哥哥们也来了,拿筷子的拿筷子,拿盐盒儿的拿盐盒儿,拿馍馍的拿馍馍,一家子在堂屋里围着炕桌喝早茶,金莲与三个哥哥蹲着吸溜吸溜的喝,舅太爷与舅太太各自坐着一个矮树墩。
舅太爷说:“你问了啦,严老太顾得上吗?”
舅太太说:“这几天不闲,得过些日子。”
舅太爷说:“耽搁不得,过了年龄,就不好裹了。”
舅太太说:“我到镇上去跟集的时候,听人说皇帝倒台了,外面在闹革命,女人以后不用裹脚了。”
舅太爷说:“你个女人家,知道撒,我才听到的,说是复辟了,辫子要留着,脚也要裹,麻先生说没皇帝不行,没人做主,人是要乱的。”
舅太太说:“复辟,是皇帝回来了吗?”
舅太爷说:“是的,又回来了。”
舅太太不在说话,咬了一口馍,细细嚼着。
私塾里的先生是从外面逃难来的,不过是个病鬼,学生们一个月也听不了几堂课。
舅太爷说:念个屁,算毬了,把庄稼务!
三个哥哥见不用上学了,一个个高兴的能跳八丈高,整天放鹰一样满山跑,大哥帮着舅太爷干农活,割牛草的活成了二哥的,三哥很顽皮,不是下河摸鱼,就是拿着弹弓打雀儿,还把麻子家的草垛子给点着了,赔了不少钱,让舅太爷吊在房梁上一顿皮带,可是屡教不改,当时哭死连天的,过上三天原打原。
金莲也没闲着,帮着妈做饭、洗衣、喂猪,舅太爷进山割柴去了,放牛的活也落在了她身上,那天她牵着野牦牛从六岔滩回来已经是晚夕时分,家里来了一个她没见过的穿黑衣的老阿婆,吃完夜饭,妈把她叫了进去:“这是严阿婆!”
不知道为撒,见到严阿婆,她有些害怕,但还是叫了一声:“阿婆!”
严阿婆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唵!”又对舅太太说:“女儿长的肌骨得很。”
肌骨大抵是冰肌玉骨的意思,形容长的俊。
金莲扫了一眼,三个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炕上摆着炕桌,达盘着腿在喝茶,严阿婆坐在炕沿儿上,她看着舅太爷说:“全生,开始准备哦!”
舅太爷说:“忙撒,你再坐一会儿吧。”
严阿婆说:“这都快坐成禅了,再坐就要粘在炕上了。”
舅太太局促不安地说:“那我去烧水。”
舅太爷放下茶碗儿说:“嗯!”
金莲站在堂屋里听的莫名其妙,不知道达和妈在跟严阿婆在说什么,严阿婆起身拉着她的手问:“几岁了?”
金莲说:“七岁半。”
严阿婆在她身上一阵乱捏,弄的她浑身酸疼,又问:“脚心痒吗?”
金莲说:“不痒!”
严阿婆放开了她,对正在穿嚡的舅太爷说:“是个硬骨头,要吃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