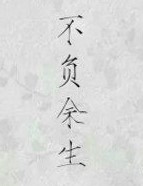舅太爷进屋后赶紧用抹布擦了炕桌摆上:我给你倒水。
火炉上搭着一个熏的乌黑的水壶,里面是烧好的开水,提开水壶后,火用一个圆形的石块封着,有淡淡的青色烟气升起来,他拿过花瓷茶碗倒了水,小心翼翼的放在了炕桌上,她达坐在炕棱头儿上抬起茶碗喝了一口:萍萍怀了你的孩子,你说怎做?
舅太爷打了一个激灵,然后扑通跪了下去:达,我要和萍萍好好过日子,一搭儿养孩子。
她达没想到舅太爷说出这话来,连达都叫上了,原本还想教训一下,现在看来也没必要了,而且柳全生会告阴状,真要惹急了,保不齐就要添油点灯让阴鬼勾自己的魂,再者闹的动静太大,传出去名声就完了。
她达瞥了一眼舅太爷:起来!
舅太爷起身抖了一下土:达,我等一阵儿找个媒人。
她达嗯了一声,起身看了看房子,就走到了院里,对舅太爷说:我先去了。
舅太爷挽留:喝完早茶再去。
她达说:不了,不了。
舅太爷将她达送到了泉下边庄下头的小路,这才回了屋里,晌午时找了庄里能说会道的王大娘,送了一竹篮鸡蛋,王大娘眉开眼笑满口答应着,第二天骑着自个家的小毛驴,下了炭山,出了耳阳沟,过了芷水船桥,一路朝南来到了后土村,稍微一打听,就知道安萍萍家住哪里了。
王大娘把小毛驴拴在了一棵横卧的白杨树上,进了巷头推开了舅太太家的大门:屋里有人啦?
舅太太说:你寻谁呢?
王大娘上下瞅了几眼:你是萍萍吧?
舅太太说:嗯。
王大娘走到了院里:你达和你妈在屋里啦?
舅太太说:我达地里去了,我妈到井上担水去了,等一会儿就来了。
王大娘笑着说:好,好。
舅太太问:你有撒做的吗?
王大娘说:你妈来了我再说。
舅太太自个家心里思慕了一番,已经猜到了七八分,夜来个达给她说了去炭山的事,看来这个老大娘是柳全生叫的媒人,她把王大娘让进了屋里,让她坐在方桌边的长凳上,然后倒了热水,王大娘正渴着呢,咕咚咕咚喝了几气,刚放下茶盅子,外面响起了吱扭吱扭的声音,起身一看,是安萍萍家妈担水回来了,她迎了出去:担水来了呀?
她妈说:唵,你啥时来的?
王大娘说:在你前脚儿刚到。
舅太太过去帮忙将桶里的水倒进了缸里,妈与王大娘进了屋,很快屋里便传出了笑声,两人说的很欢。
晌午时达从地里回来了,与王大娘说了一会儿话,舅太太炒的洋芋,王大娘吃了两大碗,用手绢擦了嘴说: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过两天我找个日子,带全生来认门儿。
王大娘到炭山上后给舅太爷说了,寻庄里的白胡子老人翻了老黄历:九月九,久长久,是一个好日子。
舅太爷问:哪天认门儿好?
白胡子老头说:随便都行,这个不讲究,认门儿,送嚡面,最好一把连了,省事。
王大娘也说:刘爷说的对。
舅太爷置办了礼当,三天后与王大娘几人去了后土村,认了门儿,送了嚡面,顺便递上了喜帖,舅太太她达收了喜帖,然后摆了酒菜,好好答应了一番。
晚夕时分,舅太爷一行人才离开后土村,过芷水船桥的时候,有一个喝了酒的人差点儿落水,把大家着实是吓得不轻。
九月八日,舅太太家摆了宴席,亲戚邻居都上门了,热闹了一天。
九月九那天,炭山村的街坊邻居天不亮就开始拾掇了,全庄的牛车马车都合到了一处,绑了大红花,最前头的是舅太爷家的野牦牛,脖子上挂着一对儿大钢铃,走起来的时候当啷当啷响,车队下了炭山后,沿着耳阳河出了半沟,又沿着大路到了芷水船桥边上,一辆车一辆车的过了桥,往南而行,最后停在了后土村,舅太爷与几个亲坊到了舅太太家门外,尕娃们纷纷堵在大门口讨要喜糖,这是一个老风俗了,名曰:把轿门!意思是不给喜糖,就拦着不让新媳妇上骄子,不过乡里人,哪有什么骄子?当习俗却也没少。
舅太爷把提前准备好的喜糖和喜钱撒了出去,尕娃们一阵哄抢,他到了院里,见到舅太太的娘老子,然后把舅太太背上了挂着红布的牛车,老丈人将的亲坊们有的抱着新衣服,有的抱着新被子,还有陪房了一个黑色的小嫁妆柜,全放在了牛车和马车上,搭了礼亲坊邻居都上了车,一路欢天喜地的来到了舅太爷家,院里摆了不少方桌和长凳,主事人给知客们各自做了安排,两个人管一桌,倒水的倒水,上菜的上菜,答应的非常周到,宴席罢的那会儿阳婆刚落山,女人和孩子们又开始闹洞房,掐新媳妇要喜糖,好不热闹。
半夜儿,人已走,院子里的桌凳与搭的凉棚都撤了,炕上铺着松软的新褥子,舅太太一身红衣坐在炕上,黑色的长发盘了起来,绑着红头绳,白净的皮肤在油灯下因娇羞透着红晕,舅太爷喝了不少酒,洗漱罢两人吹了灯,睡下后舅太爷摸着舅太太鼓起的肚皮说:你说是儿子还是女儿。
舅太太说:我怎么知道。
舅太爷说:嘿嘿,我猜是儿子。
舅太太说:你怎么猜的。
舅太爷说:我乱猜的。
舅太太就笑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年春天,如舅太爷所言,养的果然是个儿子,白白胖胖的,舅太爷出门碰了一个人,是白胡子刘爷,给起了一个名字:柳青松。
这就是我大舅爷!
他这名字,乍听不错,不过我这有给孩子取小名的习惯,给在名字的第二个字后面加一个‘娃’字,也不知道是那辈上传下来的规矩,柳青松的小名,自然就是青娃了,不过也还好,不算太离奇,毕竟叫蛇娃,狗娃,鸡娃的有一大堆。
舅太爷与舅太太婚后过的不错,翻修了老房子,在农闲时挖土打了基坯,又盖了三间灶户,将围墙重砌了一下。
第二年夏天,养下了我二舅爷,起了一个名字:柳新松。
第三年秋天,又养下我三舅爷,起了一个名字:柳劲松。
有人会问:怎么跟挤青豆儿一样,这么能养?
其实,那年月,家里有十个八个孩子,很稀松平常,这才三个,算少的了。再者,养的多,死的也多,有的家里养了十几个,能活下来的,可能就两三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是只养一个,死了,就绝后了。
乡民种地,人多力量大,在野山里挖一块地就能种,不缺地,缺的是人。
舅太太在屋里带三个孩子,舅太爷没黑没白的干活,好在是老天爷赏饭,年年丰收,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外面战火连天在闹革命,却也丝毫没影响到桃花源上人们的生活,毕竟这里太过偏僻,没有那个军阀会看破红尘,带着部队跋山涉水来此过隐居生活。
一连生了三个儿子,舅太太觉得有些对不住祖宗,她出生的后土村,自古有生女为美的民俗,认为儿子都是讨债鬼,赔钱货,只有女儿才是宝。在更古老的时候,甚至流传着“只有接进来的女婿,没有嫁出去的女儿”这样的谚语,这种思想从小就在舅太太的心里扎下了根,为此她瞒着舅太爷,特意回了一趟娘家,去娘娘庙烧香,祈求后土娘娘保佑自己能生一个女儿。
天随人愿,神有感应。
上天真给了她一个女儿。
可是,我舅太太怎么也想不到,她女儿金莲长大后有杀人放火的脏腑!
金莲快养的时候,在她肚子里转筋扯肠子,疼得她在炕上直打挺,舅太爷在灶户里烧热水,大儿子挂着眼泪第九次跑来拉着哭声说:达,我妈疼的在炕上打滚呢,你赶趁去瞭一眼。
舅太爷把手里的麦草填到了锅灶门里,火照的他的脸金红金红的,他从小矮凳上起来用袖口儿抹了一把大儿子脸上的眼泪,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哭撒?尿水子就广得很!又说:我让你干爷去请白阿婆了,也快来了,你在灶户里把看火,我去瞭一下。
他先去看婆娘娃娃,进屋的时候哭成了一团,舅太太在炕上痛的泪流满面,二儿子和三儿子趴在炕沿儿上哭,现在正农忙,人都下地了,连个帮衬的人都没有,舅太爷见了揪心的差点儿落泪:萍萍,再等一会儿,白阿婆就来了。
舅太太都快疼晕了,头皮仿佛刀割,肚子好似针扎,心如油煎,汗如雨下,那听得进去一个字?舅太爷没一点儿办法,他到了院里,一个雨点儿打在了脸上,他仰着脸看了看天,云很重,黑压压的,他往东山湾瞅了一眼,白濛濛的雨幕正朝炭山而来,他跑到打麦场的土崖边扯着脖子往进村的山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嘴里嚼了一声:还不来,总没死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