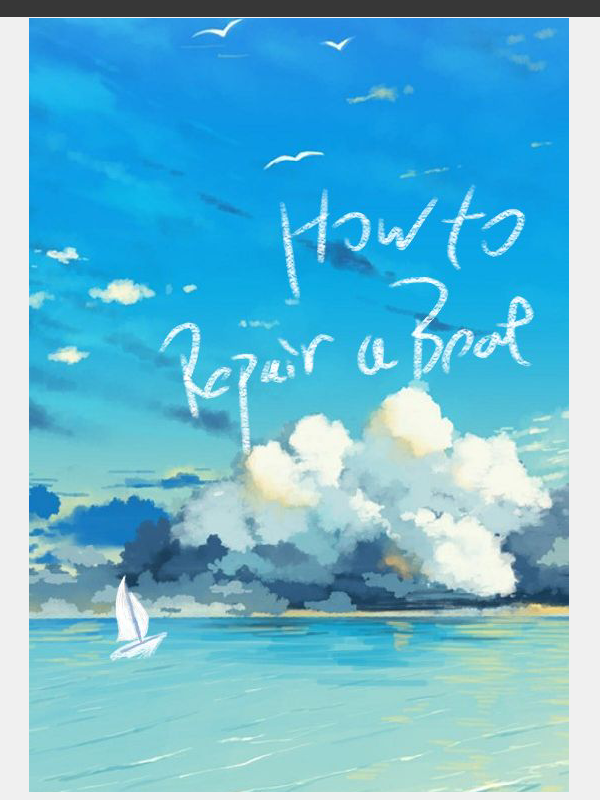不日,和谈结束,除了留下戍守的军队,其余人等班师回朝。一路上估计也没少受到百姓们的夹道欢迎,虽是尽量加快了脚程,还是足足用了一周有余的时间才回到帝都城下。凌帝亲自出城相迎,犒赏三军。照例就在京郊设宴,以防有人拥兵自重,趁机逼宫。酒水和肉食不断的送来,一帮血性男儿酣畅痛饮,可惜这场面却不是我能够见得着的。
而后几位主副将还有一些战功卓著的将士们便跟随帝驾入宫听封,一车一车的战利品也随之运进城来。听苜蓿说,进城时倒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纷纷夹道欢呼,将手中的鲜花、罗帕汗巾之类色彩妍艳的东西撒向帝驾和将士们。其中,最受欢迎的自然还是风姿绰约的辰殿下,一笑一挥手就引得一票少女欢呼尖叫,几乎没衍生成为暴动了。
回宫后,自然先是在御花园赐宴,这类国事盛典按照律例是要由帝后共同出席,因凌帝后位空缺,很多时候还需要劳动太后出席,我也正因此沾了光,得以陪伴在旁。
隆将军的位子自然是最靠近帝位的了,接下来是左右相,还有百官以及一些皇子们。凌旸和容翰非虽有军功在身,也不见僭越,仍然稳坐于以前的位置。待众人刚刚落座,凌帝眼中带着笑意道:“这次的胜利可是仰仗你们这一文一武了。隆将军,自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智勇双全,威震四方啊!容探花做得也漂亮,这和谈的新条款虽是以前没见过,细细想来倒是比加赋税要妙哉十倍有余呢!难为你们怎么想来的?”
容翰非依旧不卑不亢:“禀圣上,微臣不敢擅自居功,这些法子是隆将军还有辰殿下共同商讨出的结果。”
凌帝颇有兴趣地向前俯了俯身:“哦?老五也出谋划策了?”
一边的隆将军发话了:“可不是?殿下可确实是有才智的,这里面大半都是他拟出来的。”这可确实是个直肠子的军人啊,凌旸已有了军功在身,害怕太过惹眼才让容翰非顶上这功劳,这下倒被他一下子捅破了。看他颇有些愤愤的表情,该不会是以为容翰非要抢了凌旸的功劳,才仗义执言的吧?
“老五,平日倒是看不出来啊,这趟战场还真是去对了,受到磨砺不少啊!”
凌旸连忙恭恭敬敬回话:“隆将军谬赞了,凌旸不过是跟在将军和探花后面学习罢了。说起才智,那是绝不敢当的,隆将军之勇,容探花之智,那可绝非儿臣可以望其项背的。”
众人又是一番对三人的溜须拍马,把他们说得天上有地上无的,让我不禁好笑。
“父皇,今日宴会可是还有一位贵客没有请出来呢!”许是三殿下凌晖看不下去众人的吹捧了,便向凌帝打断道。
“哦,是了,可真是忘记了这位‘贵客’了!还不去请上来!”凌帝嘴角带笑,满面得意之色,却掩不住眼底的那一抹轻蔑。
旁边早有人领命下去,不多时,身后已经跟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回来了。他一身夷赫服装,黑色的贴身劲服,襟口袖口以暗玄色的织绣做镶边,隐隐可以感觉到衣服下肌肉由于动作而起伏的样子。外面裹着一件亮眼的火狐皮子,与他衬麦芽色的肌肤十分相称,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男子。与凌旸的容颜秀美不同,他似乎更加俊逸,有着少年和青年共同合体的一份气质。如果把凌旸的美比作山泉的灵动,他则是开阔的旷野,别具一番风味。
他走到凌帝坐前,单腿屈膝:“夷赫离王三子离白鷲参见丰国凌帝!愿陛下福寿安康,丰国能与我夷赫永为友邦!”虽然半跪于坐下,受到凌帝居高临下的审视,却丝毫不见他有何怯懦的神情。依然神色平静,仿佛根本不是在做一件屈辱的事情,依然还是夷赫那受人尊敬的王子。
“好好,”凌帝并不急着让他起身,而是问道,“听闻三王子是主动自请来我丰国的?”这倒让我惊奇了,要求夷赫必须遣一名王子来我丰国做质子,是和谈中的必要条款。但是谁都明白,在敌国做一个质子意味着什么。除了必要的忍让屈辱,更可能的是,若两国再有争端,这头一个做祭品的自然是质子了。可他竟然还自请为质?
“回陛下,我夷赫皇室子嗣不多,只有三个,大哥二哥皆是有家室的人,让他们抛弃家事远赴千里似乎也是不妥。而我,自小就一直很是醉心于丰国的文化,正好想借此机会来丰国学习学习诗词之道呢!”
“呵呵,如此甚好,三王子就安心在我这宫里住下吧!你也下去坐着吧!”
离白鷲这才领命站起,走向为他准备好的座位。也不知凌帝是不是故意的,特特把他的位置安排在一群武将之中。行军打仗的人没有文官那么多的花花肠子,说起话来也一向不客气,更兼对方还是一个敌国的王子,刚刚战乱结束,这些眼见着死亡和杀戮的战士们还都没能平复心情。如今新仇旧恨一起来,言语间对他也十分的不客气,各种嘲讽轻蔑的目光投来。而离白鷲丝毫没有拮据的神情,反而相当的泰然自若,自顾自地饮酒布菜,对一切充耳不闻,举手投足间还保持着良好的风度礼仪。
这样一来,如同一记猛拳打在团棉花上,无声无息没有后文,让许多等着看笑话的人也甚觉无趣。武将们见他如此,也渐渐失去了兴致,只自己痛饮起来。
我忍不住又多看了他两眼,容貌甚为年轻,至多不多二十岁,却能够有这般的坚忍和定力,实在是不易。看他身形颀长,步伐稳重有力,想必也是一身武艺的好手。如此一个人才……我深感庆幸,当时教唆凌帝让夷赫出一个质子的做法。他绝非池中之物,若放任此人,不出五年,他必定成为我丰国的一大患。幸而,如今他入宫为质,我暗暗嘱咐自己,以后可要小心钳制这个人。
正想着,离白鷲似是有所察觉,转头直直向我望来,眼眸漆黑,目光如炬。让我不禁生了躲避之意,又一想,在我丰国国土内还能示弱嘛!看谁比谁毒,就看谁先弄死谁!于是,便毫不示弱地回看过去,你要比瞪眼还是比电力?本帝姬奉陪了~~~
他接触到我毫不回避的目光,神情中流露出丝丝奇妙的莫测之意,转开了脸,又专心盯着他案几前的几个平方。我忙低下头,眨巴眨巴自己略有酸痛的眼睛。一抬头,又见凌旸若有所思的盯着我,似笑非笑的,我偷偷向他一吐舌头,然后不予理睬。
宴会结束,我殷勤的望着太后已上了凤辇,才往晌汀殿走去。天开始略略飘起细碎的雪花,幸而宴会上吃了几杯酒,又捧着手炉披着观音兜,倒也不觉得寒冷。苜蓿在前掌着灯,芷萱打着伞扶着我走,倒真把我当做柔弱的小姐了。
苜蓿忽然停下了脚步,前面晃动的灯影中似乎站立这一个人,“前面是谁?快出来,别惊吓了这边主子。”苜蓿大着胆子问道。
那个人影依旧没动,风拂起衣服的下摆,露出一双金线鹿皮靴子,俨然是一个男人的脚。“到底是谁?再不出声我可就要叫侍卫了!!”苜蓿的声音有些发抖,芷萱也略紧张起来,把我护在身后。
对面的人影衣襟微微抖动,我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好了,你也别这样逗她们了,凌旸,你快出来吧!”
那个不疾不徐从黑影中走出来的,不正是凌旸嘛!他似乎笑不可支的模样,眼角眯起越发地上扬,在昏黄的灯光下,更显出几分妩媚之气。他走到我面前,笑指苜蓿:“这丫头,还真是蛮有趣的,以前怎么没发现她胆子这么小?”
苜蓿一见是她“英勇的辰殿下”,早已说不出话来,脸色略有红影,垂头看地。我不由一笑,嗔怪道:“你也别笑她,险的也唬住了我呢!要不是见你这双靴子,我确实记得的,现在定叫你被一帮大内侍卫追着打呢!”
“你也小看我了吧!若真是这样,指不定谁打谁呢?”凌旸颇为自负。
他再自然不过地接过芷萱手中的伞,与我并肩走在一起。芷萱也十分有眼力见儿地前去和苜蓿一起掌灯。
他一只手撑着伞,另外一只手揽上我的肩头,对这样亲密狎昵的动作我略有不惯,微微动了动肩膀。
“别动,这样我们两才都不会在伞外面。”凌旸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有些酥酥麻麻的感觉。
我又不安地挣了一下,始终脱不开他的钳制,才放弃了,向他没好气地说道:“你还好意思和我争伞呢!刚才也没见你这么娇贵,一点小雪也受不得?”
“笙阳妹妹,真是不会心疼人!哥哥好伤心啊!”
我努力说服自己,不就打个伞嘛,有什么好别扭的?凌旸可是这具身体的哥哥啊,任谁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和十八岁的哥哥一起打伞都不会觉得别扭的啊!这样想着,倒忽略了凌旸那欠修理的语气。
“怎么巴巴的想着送我回去?你可有事?”我忽然想起。
这次凌旸没有插科打诨:“你看那个夷赫的三王子怎么样?”
我思忖着:“言行气度竟不像个不到二十岁的人,绝非池中之物!”
“谁告诉你他不到二十?”
“啊?”
“离白鷲今年可是二十有五了!”
我惊讶了一会儿,开口:“真是看不出来,他好似还有点少年的气质。”
凌旸的语气略微暗淡:“只要他想显出什么样子,那就能做到啊!”
“这是什么意思?他这样又是何用意?为了让父皇看轻了他而放松钳制嘛?”我蹙起眉头。
“只怕还绝非如此!”凌旸略顿一顿,“在宴席上,你为何盯着他看?”
我惊愕,有那么明显吗?还不等我回答,凌旸就转过身子,认真的看着我“不要把他放在你的眼界中,你既然已经看出他非池中之物,就该知道他不适合!!”
“什么?”我略有些气恼,他又犯了这乱点鸳鸯谱的毛病,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怎么样,就是多看了一个男人几眼,虽然是个大美男,但你未免也想得太多了吧,真以为我是色女嘛!感情您这紧巴巴地赶上来送我回宫,就是为了杜绝自己妹妹的早恋倾向,把一切苗头扼死在襁褓之中?
“谁说我看上他了?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没有?”
“当然没有!”我斩钉截铁地说道,“先前不过是好奇罢了,后来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他先瞪我来着~~”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估计确认了我认真的表情,才让笑意渐渐又浮上了脸颊:“依哥哥看,还是容羿比较得我的心,是个适合的人选。”又向我细数起容羿的种种好处,巴拉巴拉的。
我忍不住捂住耳朵,向前冲去:“不听不听不听,你喜欢他,你娶他好了,干嘛推给我!耽美大神会保佑你们的!”径直冲到芷萱她们面前,“走,我们不要理他,今天他忘了吃药了!”然后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走了。
苜蓿和芷萱忙匆匆向凌旸回个礼,去追赶笙阳了。
所以连她们也没看见,凌旸一个人举着伞,静默地站在雪中,漫天雪花如蝴蝶飘散,轻轻落在那双鹿皮靴子边上,轻盈的消失不见。与一贯辰殿下那标志性的俏丽笑靥不同,他的脸上浮起一丝清浅的笑意,将另外一只手慢慢地握紧握紧,仿佛要把刚才那点温暖的触感给一直握进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