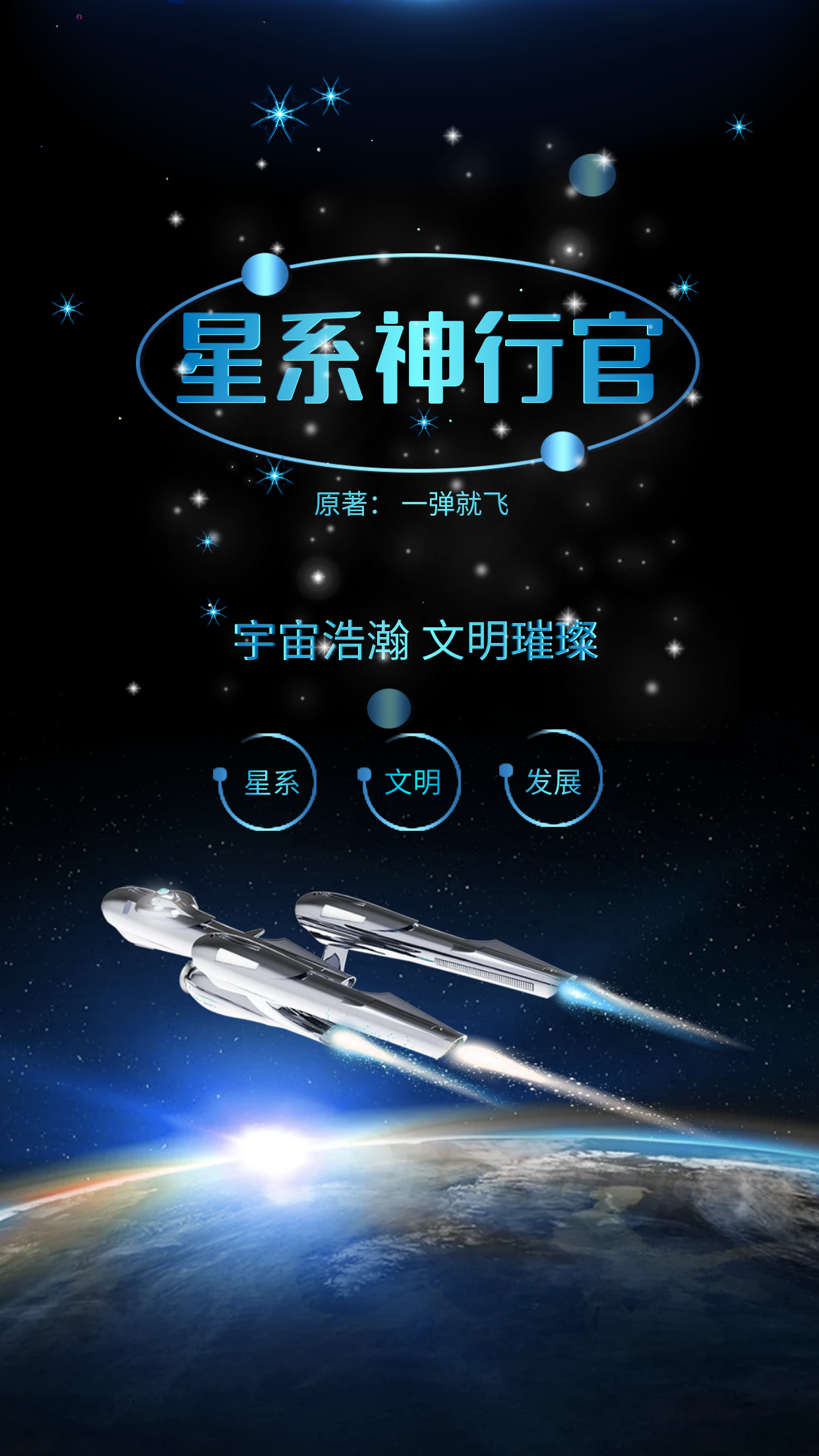下山后的蒋开兵跟打摆子似的一路喊冷。王文礼看势头不对,直接带着三人奔离此处最近的蒋开兵家走去,一进屋就让他钻进被窝,然后让李亦奇找了一个废弃的铁盆,端到蒋开兵睡觉的屋子里升起了火。蒋奶奶也帮着忙里忙外。
“嘶... ...这也没下雪啊... ...咋这么冷。”蒋开兵蜷缩在自家的床上,尽管已经用被子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却仍然止不住的打着哆嗦。
“你冷是有道理的。”王文礼微笑的说道,边说边拿着干柴往床前的火盆里面添。火烧的很旺,干柴在里面烧的噼啪作响,盆边上煨着一个陶罐,那里面是本地农户自酿的土酒——竹叶青。
“今天晚上在何军长庙里,咱用你的身体走了一回阴,现在你的两个肩膀上的阳火现在烧的不旺,阳气微弱的很,所以你会觉得冷。而且不光你冷,我也觉得冷,亦奇,你呢?”王文礼问道。
“我觉得稍微有点冷,正纳闷今天穿的挺厚的咋还觉得冷,原来是这个原因。”李亦奇答道。
“年轻就是好啊,阳气旺盛!”王文礼叹道。接着他对蒋开兵满怀歉意的说:“今天走阴,拿你娃娃当了架子人了,委屈你啦。”
蒋开兵哆嗦着直摇头:“没的关系师父,只是... ...”
“只是啥子?”王文礼问。
“只是下一次要弄这个的话,您提前知会一声,我好准备准备到,起码有点心里准备... ...”
“嘿!你这个要求还真满足不了!”王文礼大笑的说。
“啊?为啥啊?”蒋开兵苦笑着问道。
“因为,走阴这个事情,并非是个人都能扛得住的,它对这个架子人还是有要求的。活着的人叫“阳人”,死了的人叫“阴人”。阴人要让阴差带走到阴司录了薄,那就是鬼了。这人呐,有三魂七魄七窍。三魂是天魂、地魂、命魂;七魄:天冲、灵慧、为气、为力、中枢、为精、为英;七窍:两眼、两个鼻孔、两个耳朵、嘴。走阴其实就是让阴间的阴差或者阴人操纵阳人的身体说话做事。说白了是需要打破阴阳界的这层窗户纸进行沟通交流。道家讲:天、地、人、神、鬼是这天地间的五仙,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一般是互不侵犯的。阳人因为有灵慧这一魄守着人的意识,加上两双肩膀上的阳火始终在燃烧,阴人无法强行侵犯。今天让你走阴,要使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整晕过去,使你的灵慧这一魄出窍,让你吸进香灰,这样你的慧灵迷恋香灰就走不远。然后阴差就提起你的身体在香案上写下我们问卜的事情答案。阴差属性极寒极阴,由于阴差提了你的神,你肩膀上的阳火被压的烧不起来,体内阳气严重衰减,所以感觉到非常冷,说实话,这种冷比你大冬天脱光了站在雪地里还要冷,早些年我师父走阴的时候,那架子人的眉毛都结霜了。你之所以只能到这个程度,是因为你还是童子之身,本来阳气就足的原因吧。”王文礼说了一番话,从火盆里端出陶罐,斟了一杯竹叶青递给蒋开兵:“来,赶紧热热的喝了。”
蒋开兵接过酒,仰头一饮而尽。
王文礼给李亦奇也斟了一杯,李亦奇接过后有些迟疑:“祖祖,我最近在调理身体... ...”
“我晓得!走阴的不只是开兵这个架子人,他只是受的阴气最重,我们两个也或多或少也有些受影响,现在你只是觉得冷而已,寒气入侵,如果不祛除,回头搞不好还要感冒或者大病一场咧... ...赶紧!酒能散气,把你体内的寒气散一散。我说老实话,你要听。”
李亦奇见老师父说的是严肃话,接过酒杯也来了个一口闷。只感觉似乎是一团火热流顺着嗓子进入肚中,如同一条火龙一般在胸中来游荡,他皱着眉头就要张嘴呼气。
王文礼见状一把捂住他的嘴:“不要张嘴!让酒自己消磨。”
经过许久,这团热才慢慢平息下来,从肚中朝身体其他地方扩散,李亦奇额头竟冒出来细小的汗珠儿,身体渐渐的就暖了起来。
王文礼也自斟自酌一杯,三人各自一杯酒下肚,脸上泛起一阵红晕。
“嘿!”李亦奇惊道:“第一次和热酒,感觉不错!”
“啥感觉?”王文礼问。
“这煨过的热酒倒是不烫,但是喝下去感觉像是活了似的。”李亦奇接着说:“但煨过的酒更香,老远能闻到醇香。”
蒋开兵笑着说“以前就都是煨着喝的,哪像你们现在,喝冷酒,师父说那样伤胃。”
“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不知持满,不时御神,逆于生乐起居无节,半百而衰,所以呢?”王文礼说到这里,眼睛盯着李亦奇问。
很明显,王文礼引据了《素问》中的【上古天真论】里的论述来考李亦奇。李亦奇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老师父的用意,立马答道:“是故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看来那些书,你小子还是多多少少看了一些,不错。”王文礼满意的笑道。“你现在也算是摸到医理边边了,以后喃,勤看勤想。我看你现在是打定主意要在山沟里谋日子,这些东西不是什么闲书,以后都是你的本事... ...”
吱——门被推开了,蒋奶奶端来了一屉热乎乎的猪油渣馅儿包子走了进来,招呼他们热热的吃了。几人吃过后,都开始犯困。王文礼感叹自己老了,竟然没意识到这接连几次的意外死亡可能是犯了重丧,在对自己的老马失蹄悔恨不已的同时,也决定找一下村支书商量后续的措施。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李亦奇便只身起床,急匆匆的窜到蒋开兵家房子后面的地坎上美美的尿了一泡。昨晚三人睡一条床,翻个身都很困难,虽说在竹叶青的微醺之下断断续续的眯了几次,但算不上休息,因此李亦奇感觉脑袋紧紧的。
他看了看手机,这会儿才早上5:23。反正回屋还得和老师父他们挤着,于是给将开兵发了条微信说自己先按照老师父的计划先行回家准备。
“犯重丧”的说法在中国的民间已经流传了有相当长的历史了。“犯重丧”中的“重”字,即“重复”、“多重”之意,从现象上来讲,如果方圆二十里的地理区间内在百日之内接连发生死亡事件,且死因相似,就应该考虑是否属于犯重丧的后果显现。昨天已经确认这几起意外是犯了重丧,对此王文礼昨晚已订好了破局的计划。
计划就是招魂。
根据王文礼的推测,明娃子家土墙倒塌事故发生后,王开英因为极度伤心而不顾民间忌讳,抱着丈夫刘德喜的尸体嚎啕大哭,将眼泪滴在了丈夫尸体的脸上。如此刘德喜的阴魂便舍不下生前的一切,大概率是挣脱了阴差门的管制,一直在这村落附近游荡,这才导致重丧事起。眼下要想办法将刘德喜的阴魂招至何军长庙,或可以要破这重丧之劫。
王文礼根据前人传下来的经验制定了全面的招魂计划,对自己和徒弟、李亦奇摊牌了任务。首先他自己负责和村支书沟通,通过支书按照计划发动村民配合;将开兵负责准备招魂起坛的场地搭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体力活,那就是在村子西北角垒砌一个三层三尺三高的土台。而李亦奇则负责去镇上的纸货店订制所用的纸货。
所谓纸货,就是一些办丧事用的纸钱、纸房子、纸马之类的用来烧给私人用的东西。
李亦奇到家的时候刚好6:20,他瞅了瞅手机,从关口垭蒋开兵家到自己家共27里地,这次从比上次又少用了7分钟,这说明他的体力又上了一个层次。
他来到自己养牛的牛圈门口朝里面望了一眼,这些牛犊一看到他来了,喘着气都爬起来都往门口凑。
“嘿,才喂了个把月,这都跟我熟了啊。”李亦奇笑着嘟囔。
“来,给你们整点早饭!”说罢他走到牛圈旁边的草料棚子里,拎出一捆苞谷壳子喂起牛来。
“是哪个!你在我圈门上想搞啥子!”
身后传来母亲的喊声,随即牛圈上的灯亮了。
冬季天亮的晚。母亲杨芬起来上茅厕,把自个儿子当成偷牛的贼了。
“妈,是我。”李亦奇道,这会儿他才看到母亲手里竟然拿着一把粪叉。
母亲把粪叉靠在墙边,拍着胸膛说:“吓死我了,你啥时候回来的?咋不开灯啊。”
“我也是刚拢,来看看牛。”李亦奇答道。“对了,昨天牛吃草肯吃不?”
“肯吃啊,咋不肯吃,就是这十几头牛关到一堆,牛屎得天天拾掇... ...”
“莫事,这我过几天来想办法。”
李亦奇把苞谷壳子一把一把的给牛分着,阴面子的山顶泛起一片鱼肚似的白,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农村这会儿正是耕冬地的时节,为了在爷爷下地前找到他商量买纸货的事情,他顾不上吃早饭就到李云祥家。
李云祥做了一辈子棺材,和镇上的纸货将林开渠熟得很,加上是自己师傅安排的事情,自然也是很重视,顾不上洗脸直接带着孙子来到林纸匠的家里。
林纸匠的店铺本来在镇上,但是近几年因为顾及到镇街道的美观问题,相关部门禁止他在镇上开门店,于是林纸匠只能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继续这个营生。在农村乡下,老百姓是很看重白事的,加上林纸匠扎纸货的手艺不错,所以就算没了门店他的生意依然很好。去年林纸匠还盖起了两层的砖房,房子外贴着雪白的瓷砖,远远望去如鹤立鸡群,十分亮眼。
爷孙两人进来院子,发现里面除了靠着院墙的纸货,堂屋的门倒是大开着却并没有人。
尽管整个院子装修的明晃晃的,但四周静的出奇,李亦奇望着一院子的纸人和纸房子,心里不自觉发怵。“这TM有点... ...吓人啊。”
他望着李祥云,盘算着爷爷接下来怎么做比较合适。
李祥云此刻正吧嗒着旱烟,只见他大声的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咳出一口痰吐在地上。
李亦奇看着地上的痰,正准备抱怨爷爷不讲礼貌,还没开口,便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狗叫。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堂屋里跃出一条近两米长大黄狗,龇牙咧嘴嚎叫着朝他们扑了过来。
李祥云一见,扭头朝院门外跑去。那狗便扑向他孙子。
李亦奇自打出去念书开始,已经多少年没见这阵势了,一时慌乱,扭头撞上了院子的铁门,那狗扑上来便死死咬住他的右臂。
好在冬天穿得厚,这恶狗虽然咬住右臂却没伤到他的肉。李亦奇赶紧用左手抵住狗肚子同时甩动右臂往外推。经此一推,大黄狗被他从身上甩落到地上,更加凶横,而这院中的狗叫引起了连锁反应,又有两只大狗从院门一跃而入,想是左邻右舍的看家狗闻声而来。
李亦奇看自己出不了院门了,一个助跑,脚在院墙腰蹬了两步,翻身跃上院墙,双手撑在院墙脊梁。
哪知道这院墙脊梁上抹上了厚厚的水泥,水泥里面全插着啤酒瓶砸碎后的碎玻璃!
顿时双手被扎的血流如注,而院子里的狗们还在狂吠这试图朝李亦奇扑来。
“卧槽啊... ...这林纸匠家得是多有钱,竟然这样防贼!”
李亦奇望着手里不停渗出的鲜血,突然想到《万法全录》中的“退狗咒”,刚好手上有现成的鲜血,他立刻右捏成手剑指,用血在左手掌心上划了一个虎掌,并在虎掌中间写上一个虎字。随即嘴里默念出:
“拜请金木水火土,老君来求敕,为吾请飞虎祖师来治犬,本师治犬,仙人治犬,玉女治犬,七组仙师来治犬,吾上飞虎背,吾奉请飞虎无停时,吾奉请飞虎封犬口,见吾面不能吠,吾奉太上老君亲敕令!”
反复默念第三遍后,李亦奇站起身来踩在脊梁的玻璃渣子上,右脚向前大力踏出一步,右手剑指指向掌心,大声说出:神兵火急如律令!敕!
紧接着用左掌往狗的方向隔空打去。
就在左掌打出的一瞬间,一阵风从李亦奇身后吹过,刚才还狂吠着并争先恐后的往墙上扑的三条狗像突然受惊吓一样后退了一段距离,嘴里不再狂吠,而是呜呜呜低嚎着,那条大黄狗夹着尾巴窜入堂屋,另两条在院子里乱窜了一圈,也从院门躲了出去。
“好家伙!请了这么多大牛后台,多少还是起作用了... ...”
李亦奇从院墙上跳下来,悻悻的想着,望着血淋淋的双手,不知道咋弄,他转身走到院门口,想看看爷爷咋样了,正要喊的时候,堂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谁在外面呢?”
李亦奇听到有这家人说话了,立马又走进院子,心想应该是林纸匠的老婆,便答道:“是我啊表婶,我是那个,那个李文祥家的,找林表叔有事哎——”
“谁——是——你——表婶啊!”堂屋那个女人不紧不慢说。紧接着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从堂屋走出来,她穿着白色羽绒服,带着金色的圆框眼镜,看着十七八岁的年纪,气愤又苦笑的问李亦奇:
“哎,你看清楚,我是你表婶吗?怎么我声音听着很老吗?”
李亦奇没想到说话的竟然是个小女孩,一时语噎。
但基于和前女友几年的相处经历中,他早已具备了较高水平的求生欲,立马说道:“哎哟,不好意思,小妹妹,我刚才把你当成我表婶了,不好意思哈。”他点头哈腰的陪着不是,眼睛却瞅着堂屋里面,他想看看这家除了这个小姑娘有没有大人——重点是林纸匠是否在家。
“那个啥... ...呃... ...小妹妹,我那个... ...林表叔,他在屋头吗?”
“小妹妹... ...那我又很幼稚咯!”姑娘双手抱在胸前,盯着李亦奇笑着说道。
女子前后的质问搞得李亦奇两头堵,不知道咋应对。他默了片刻,嘴里低声的说:“不... ...我的意思是... ...”
“哎哟,纸月回来啦,放寒假了噻?”李祥云不知道啥时候走到了李亦奇身后,对着这姑娘说道。“这半年没见又长高了啊... ...”
原来这姑娘叫纸月。
李亦奇依稀记得,那林纸匠倒是有两个娃儿,老大是个男的叫纸星,小时候他还带着这小子和村里一众玩伴整日打闹,但是这老二倒是没啥印象。
“这是你蛋哥,城里混球不下去了,现在回来放牛了。”李祥云指着李亦奇对纸月说道。然后他推了推孙子的背,继续说道:“蛋蛋,这是纸月,纸星的妹妹,你们小时候一起耍的嘛。”
“哦,好多年没见过了,都认不得了。”李亦奇附和着说。
此时双手传来一阵疼痛,他不经意的“嘶——”了一声。
也许是刚才处于高度紧张等强大情绪压力之下,手上的割伤不是很痛,因为强烈的情绪可以抑制疼痛,现在神经放松,疼痛感立马占领感官高地,渐渐的显现出来。
“呀,你这手... ...”爷爷这才注意到李亦奇的双手,惊讶的喊道。
“刚才被狗撵到院墙上去了,哪知道上面都是玻璃渣子,给我手扎破了。”
纸月看着李亦奇的手,眉头一皱,赶紧将爷孙两个请进堂屋。
堂屋里是一个装修气派的客厅,但农村里的家庭大抵都是扎样,往往太过豪华反而显得醒目而俗套。纸月让他们在沙发上坐下,说道:“祥爷爷你们先坐一哈,我去找点止血的东西来。”然后转身朝里屋走去。
那条大黄狗躲在客厅的电视柜下方的空格里,见李亦奇进屋,趁着纸月转身的时候,呜呜夹着尾巴窜出来抢在她前面逃进里屋。
纸月见状一脸疑问,回过头问:“蛋哥,大黄咋被给吓成这样子,你是不是打它了?”
“没有啊,我一下就被撵到墙上去了,手里啥都没得,压根没法打它... ...”李亦奇说。
“嗯... ...”纸月思索了一会儿,突然坏笑道:“你手无寸铁... ....那它怎么吓得跟见了老虎一样... ...我的天,你该不会是... ...咬了大黄一口吧,哈哈哈——”说完纸月在里屋门口笑的直不起腰。
面对这个没心没肺的妹子,李亦奇实在是相当无语,但是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他竟生不出气,无奈地的摇了摇头,皱着眉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这就给你找止血的... ...”纸月发觉了李亦奇的窘迫,连忙纸住笑声,进屋找东西。
不一会儿纸月左手捻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右手拿着一盒芙蓉王走了出来,她先来到李祥云面前,发了一支烟给他:“祥爷爷,来吃支烟罢。”
“哎哟,谢谢纸月。”爷爷谢道。“你们屋里这么干净,我出去吃,免得给你们搞脏咯。”
“没得事的祥爷爷,我爸爸也经常在这抽的嘛,你在这吃得没关系。”
“哎不行,这么好的沙发,给你烫个洞划不戳咧。”说完爷爷起身走出客厅,在纸月家的盖阳上找了个椅子坐下,他将芙蓉王别在耳朵上,从中山装里掏出自己的烟锅子,卷了一卷旱烟抽起来。
纸月来到李亦奇身边坐下,白色的羽绒服是带帽子的那种,帽子边沿是天鹅绒的毛毛,和纸月乌黑的头发以及她白色的耳朵和脖子加上近似眼镜,这些搭配起来显得非常干净,甚至可以说给人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来,手伸出来。”纸月说。
李亦奇伸出右手。
“两只手。”
李亦奇又伸出左手,纸月俯身趴在李亦奇面前,让他把手摊开。
双手手心向上摊开。
纸月立刻看到了他左手掌心画着的那个掌印和中间的“虎”字。她慢慢把脸转向他,此时两个人的脸距离不到十厘米,李亦奇嗅到扑面而来的味道,那是她呼出来的气跟洗衣粉或者洗面奶的味道混合而成的特殊香味。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吐气如兰”吧。
这令李亦奇心里想起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中的那句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不,应该是“邻家”有女初长成才对。
“哦——我现在晓得你如何收拾我的大黄了... ...”
纸月盯着他的眼睛问:“跟哪个学的?”
“学的啥?”李亦奇问。
“什么学的啥?看你手上!”纸月略带气愤的说。“不要以为我啥都不懂,我说,你是跟哪个师父学的艺?”她指着李亦奇手掌心,“这东西并不是说随便一个人乱画一气再哼哼几句就能起效的。你这样弄,我家大黄半个月在离你三里地以内的地方饭都不敢吃。”
眼前这个小姑娘明明是个在校大学生,可她怎么也对农村里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这么敏感呢?想到这里,李亦奇想实话实说,但是想起祖祖王文礼的交代,又怕自己拿捏不准,要是纸月不是真的了解这些传统,或者说她指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事情,自己要是照实说了,她搞不好会把自己当成一个神棍看待。
他想起小时候村里有人去世后,总会来三五个一口黄牙、粗犷不堪的中老年阴阳先生,他们焚香供奉着画着怪异神像的木板并在那前面敲锣打鼓诵经做法。指导白事主家在哪里打井下矿(挖埋葬逝者的坑叫做“打井”,将棺椁下葬成为“下矿”)。在没有遇到祖祖王文礼之前,在李亦奇的眼中,这帮人就是骗吃骗喝骗钱的江湖神棍。
现在他害怕自己一不留神会在纸月的眼里沦为那样的印象。至于为什么害怕,他说不清楚,但就是不情愿。
李亦奇不敢直视纸月的眼睛,但偏偏此刻纸月直勾勾的盯着李亦奇,等着他的回应。
“对不起... ...我那个... ...是... ...”他支支吾吾的,正在想如何搪塞过去,眼睛避开面前的人,在客厅里面四处扫视。
突然,他在发现纸月刚才出来的“里屋”其实并不是一间屋,而是一个横着的过道,透过道的墙上供奉着一个神龛。李亦奇集中精神,那神龛变得清晰起来,他看到神龛里供奉的神原来是“灵官马元帅”,也就是南方火神“华光大帝”。
李亦奇根据最近研习的古籍以及和与王文礼共同处理相关事务的经验迅速判断:一般人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安神”的,但凡在家中设龛安神,必定从事特殊职业,并且帯艺在身。
华光大帝是什么神?相传他本名姓马名灵耀,因生有三只眼,故在民间又称“马王爷三只眼”。相传有一天,玉皇大帝派星日马(即马王爷)和娄金狗、奎木狼、虚日鼠下凡,去四方巡察善恶。这四个神东南西北各走一方,没几天,先后返回天庭向玉帝述职。其他三个神所报的均是善人善事,说下界一片歌舞升平景象。只有星日马查访的善恶之事都有,并且有豪强欺负穷人的事。玉帝看了有所怀疑,就派太白金星下界复查。得知娄金狗三神所报不实,他们在下界贪吃受贿,昧着良心说了假话。星日马廉洁奉公,好坏善恶如实奏报。玉帝连声夸他明察秋毫,又赐给他一只竖着长的眼睛。从此,马王爷比以前更加目光如炬人见人怕。于是,民间流传这样一句俗语,“你可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不是好惹的”。马灵宫善于要火。身上藏有金砖火丹,随时用火降伏魔怪,所以后来民间又把他视作“火神”。一般那些唱戏的戏班子会供奉华光大帝,戏班经常到外地演出,戏棚是用竹子和木头搭建而成,因此很容易引起火灾。每当新戏台落成、开戏之前一定会立火神华光神位祭拜华光大帝,祈求消灾解难,因此很多戏班子都自称是“吃华光饭”的。
而林纸匠家扎纸货为生,家里必然是每日严防火灾,因此林家供奉华光大帝合情合理,照此推理,林纸匠必定也和祖祖王文礼一样,凡身帯艺。而纸月终日耳濡目染,因此也应该懂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我是跟着关口涯的王文礼祖祖学的“执尺”。”
当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最好的办法。李亦奇收回双手,站起来慢慢的说道。
“原来是执尺啊?那就好...那就好... ...站到起干嘛?坐下,手伸出来我给你包一下。”纸月恢复了笑脸,李亦奇听话的坐下来,她继续趴到他胸前,开始处理伤口。
李亦奇的左手被划破一处,右手更惨,手掌两处,无名指和中指各一处,手掌那道口子更是深到能看见骨膜。她这才看清纸月那所谓“止血材料”,原来是不知道哪里弄来的蜘蛛网。
纸月看到手上的那个最严重的伤口,心里莫名地竟觉得有些心疼,温柔的说道:“对不起呢,没想到这么严重... ...我这里替大黄给你赔不是了哦。”
“没事儿,这有啥... ...不过,你确定不需要洗一下吗... ...哎哟!”
话还没说完,纸月拿蜘蛛网盖住伤口用力压了一下,瞬间鲜血浸透了蜘蛛网,但蜘蛛网紧紧的吸附在手掌上出血的状况改善了很多。
“马王爷钦赐的止血布,绝对保险嘿嘿... ...”纸月调皮的说完。然后拿出来一件旧衣服,用剪刀剪开,三下五除二做了个简易的绷带给李亦奇包上。
那是一件前面印有蜡笔小新图案的粉色夏季女式短袖,毫无疑问是纸月的。
“爸爸扎纸货少不了要开竹子做篾条,经常割破手,每次都用这个方法,很管用的。”
“嗯嗯,谢谢啦。”
纸月转过头,望着李亦奇,略显温柔的叮嘱:“就是后面几天你千万不要让伤口沾水,不然就感染了,听到了没?”
李亦奇觉得两人距离太近有点尴尬,身体往后靠在沙发上,嘟囔道:“几天都不能沾水,还是双手,那我洗脸咋办?”
“那每天早上到我家这来,我给你洗,谁让是我的狗给你撵到墙上的呢。”纸月开玩笑的说道。
“咦,不至于... ...不至于... ...”李亦奇说着,望着院子里的院墙,心里缓缓涌现出纸月给他洗脸的画面开始走起了神,嘴角不自觉的上扬。
啪——
突然一件软趴趴冰凉的东西打在了他脸上打断了他的幻想。他回神一看是一双橡皮手套。
“喏,给你这个!”纸月说道,“也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你拿回去吧,作为对你的补偿。要是实在是要保持帅气必须洗脸的话,就带上这个洗。”
这东西李亦奇家还真没有,就打算收下,由于现在手不方便,只能用两个被包扎的像熊猫一样的手疙瘩夹着橡皮手套,但又不知道往哪里放,放下也不是,夹着也不合适。
纸月见状又咯咯的笑脸起来,说了句“我来吧”便拿起橡皮手套,塞到李亦奇的外套口袋里,然后拿起桌子上芙蓉王,抽出一支来。
这家伙别不是要抽烟吧?李亦奇惊讶的看着纸月,根据这货之前的表现出来的性格,搞不好... ...像是个抽烟的主儿,卧槽,可惜了,不抽烟就完美了... ...
纸月抽出一支烟,却没有递到嘴里,而是转过来塞到李亦奇的嘴里。
“干啥?我不... ...”
“我晓得你抽烟呢!”纸月不等李亦奇编完瞎话,拿起打火机打着火给他点上。
卧槽,形象没了!
爷爷抽完烟又走进客厅,正好撞见纸月给李亦奇点烟,他涌出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容,问到:“纸月,你爸爸和妈呢?”
“他们都不在家,今天幺爹家宰过年猪,爸爸早早的去给按猪去了,下午还要吃剖膛,所以妈也去帮忙弄菜,早早的就走了。”
农村少集市,年底将养了一年的肥猪宰杀,然后做成腊肉供来年食用。宰过年猪是一件热闹的大事,须请几个壮年男子和一个杀猪匠,于上午将猪按在板凳上对其放血,之后放入黄桶倒入开水除毛,再由杀猪匠开膛取出内脏后进行分解。下午准备几座饭菜请左邻右舍一起吃肉喝酒,这样的宴请便叫做“吃剖膛”。
李亦奇听罢,起身来到院子里浏览了一边,一般的甲马、冥服、倒是有了,但是还缺几样。
“你们找我爸爸有什么事?是帮忙还是扎纸货?”纸月问。
“扎纸货。而且很急。”李亦奇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