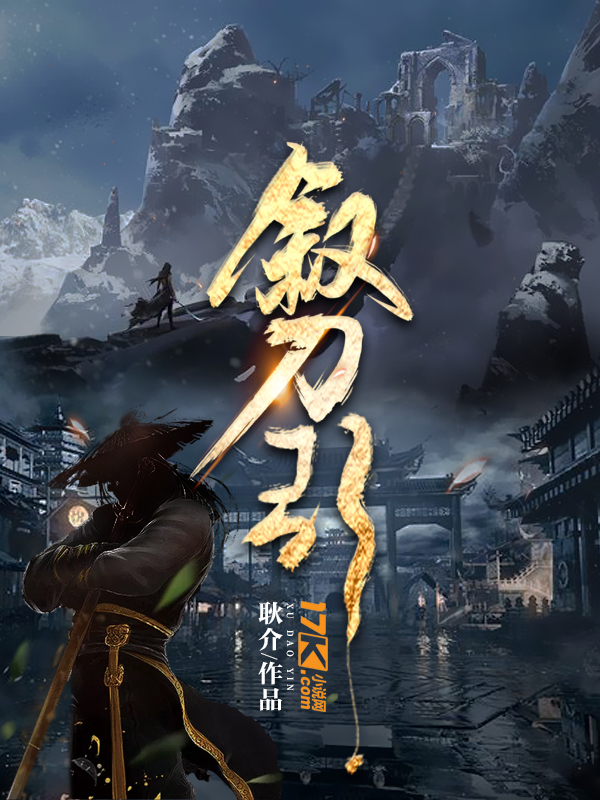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开花落,花落花开,时光如驹。
此时西楚已是寒冬时节,道路旁的青草红花已然不见踪影,只剩下光秃秃的黄土地。一个白衣少年,骑着一匹白马,飞驰于乡野大道中。
那白马的蹄子飞踏在道上,击打出“咚咚”,“咚咚”,“咚咚”的响声,贫穷乡下人很少见过如此景象,大多都忍不住回头,好奇地观看。
少年骑马奔过乡道,来到一间酒家打尖。小二一见来人骑着高大白马,急忙上前招呼。少年朗声道:“小二,照顾好这匹马,这是赏你的。”
说着,丢给小二一大锭银子,便踏步走进门。一进到店里,少年一眼便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正瞪着自己,少年委屈道:“爹,一年不见,怎的一见面便这般瞪我?”
那中年男子哼道:“在外闯荡这么久,性情还这么张扬,为父不是和你说过,行走江湖,切莫露财么?”
少年辩道:“哎呦,爹,此地偏僻,人心淳朴,又岂会像在锦城那般,人心难测,连一个说心里话的朋友都没有。”
中年男子叹道:“你厌倦朝堂上那一套,我也不逼你,只是江湖也并非像你所想,仗剑天涯,快意恩仇,当年我和你伯父闯荡江湖之时,若是像你这般,只怕脑袋早就搬家了。”
少年警惕地望了望四周,见食客都在用饭,低声道:“父王您在边境戎马多年都安然无恙,又怎会折戟于江湖呢?”
中年男子白了他一眼,道:“游历江湖,武功没学到,油嘴滑舌倒学了不少。”
酒店中的食客颇多,大多是乡野村夫,谈论的大都是今年的收成如何如何,亦或是谁家的姑娘又出嫁了之类的。
只听得邻桌一个粗狂的声音道:“舅舅,你此番进京可有什么奇遇?说来听听呀。”
又听得一个略带低沉的声音道:“此次进京倒真是大开眼界,这京都可比咱这鸟地方繁华多了。”
那人抿了一口茶,又续道:“不过,我在京都听说向帅辞官了,这倒是个趣闻。”他此话一说出口,旁人无不惊诧,纷纷转向他询问。
白衣少年也是同样惊讶,对中年男子小声道:“父亲,此话当真?”中年男子摆摆手,示意此处不方便说话。
一老者问道:“敢问阁下说的可是天蚕军统帅,当今陛下的皇弟,战王向靖榆?”前一人道:“在我西楚,除了战王,还有谁称得起向帅二字。”
那老者抚须道:“当世或许没有,但在二十年前,同样也有一位向帅,便是他在天下大乱之时开创了西楚,才有如今我等安息之所。”
“您说的莫非是先帝,难道比之镇守北境的战王还要厉害?”人群中一个年轻人问道。老者显是有些愤怒,道:“哼,你们这些年轻人,只知今之向帅又怎会知道先帝………”
老者话未说完,年轻人也不乐意了,出言相讽,酒馆中顿时嘈杂一片。
“此地远离京都,不用谨言慎行,意见不同,便可高声辩论,比之京都那套繁琐礼法倒是有趣得多。”那少年骑在马上道。
父子二人见酒馆嘈杂,不愿多留,便骑马离店,此时向靖榆骑着一匹赤色快马,道:“羽儿,身在江湖,便可稍许放纵,待到了京都,可不许胡闹。”
向羽纵马狂奔,直到白马气喘吁吁奔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夜幕降临,向羽纵身躺在高坡上,夜空中群星闪烁。
“以前你母亲在世时,我们一家三口也经常这样看星空。”向靖榆坐在向羽身旁道。向羽听到提及去世的母亲,微笑道:“母亲生性向往自由,只是京都的星空总是有所遮挡,不如这野外的开阔。”
向靖榆道:“你若得空,也该去南蛮看看你舅舅,自你母亲去世后,我几次差人去请他来锦城久住, 他都不愿意来,你去劝劝他,当年若没有你母亲和他,也不会有我如今的向靖榆。”
向羽道:“舅舅同母亲一样,都是性子洁傲之人,母亲在世时他便不愿沾光前来,而选择久居南蛮,父王之愿怕是要落空了。”
向靖榆叹道:“屈指算来,你母亲也走了六七年之久,这几年我忙于朝政,才放任你游走江湖,这下好了,我没了官位,可得好好管教你,收收你这性子!”
“对了父亲,你为何要辞官?莫非朝廷真的污浊到父亲也不愿待了?”向靖榆轻声道。
“如今的朝廷,比起你祖父在位时确是变得不堪了,但你皇伯和那些良臣都已在尽力整治了,此番我辞去帅职,是同你皇伯一同商议的结果,只是我赋闲的日子当是不会太久,相信接下来为父会担任整治吏治的要位。”
向羽笑道:“父亲,您已为国征战多年,何不乘此机会远离朝堂,我们父子一同游走江湖,劫富济贫,岂不快哉?”
向靖榆轻声斥道:“荒唐,你这胡言乱语的性子若在京城只怕又要闯祸了。”向羽吐了吐舌头,示意已经认错。
向靖渊又继续道:“你向往江湖,可你当真以为只有在江湖之中可行救人之事?天下间那些穷苦之人,哪一个不是受朝堂上的决策影响才身陷囹圄?再者,我等都是皇族,岂可置家国大事于己身之外?”
向羽忙道:“父亲教训的是,孩儿失言了。”向靖榆又轻叹一声道:“想你祖父在位时,吏治清廉,国家强盛,岂料如今的朝堂只顾勾心斗角,我实在是有负他临终所托呀。”
向羽问道:“父亲,我听闻如今我大楚官吏腐败与外戚有关?”向靖榆瞄了向羽一眼,道:“羽儿,你不在朝堂,有些话,我对你说不得,只是你要知道,一国之衰败,不可全然怪罪到一人身上,朝堂之事,复杂得很哟。”
父子二人在坡上闲聊,聊着家国大事,江湖恩仇,二人倒也快活。二人聊至夜半,忽听得东南方向传来阵阵马蹄声,由远至近,渐渐清晰,约莫又二十骑奔驰而来。
群骑奔至向氏父子跟前停下,显是冲着他们而来。向靖榆起身道:“不知是那一路的朋友?”
那二十骑皆是黑衣蒙面,为首那人道:“你是何人?”向靖榆拱手道:“在下是锦城来的商人,今日得见诸位,鄙人身上还有些许银两,便全部赠与诸位,就当交个朋友可好?”
向靖榆只道那群人是打家劫舍的寇贼,如今己方势力孤弱,便想先用财物求得脱身,待日后再联合该地太守,整治寇乱。
岂料向靖榆话音刚落,为首那人便纵声大笑,接着随从之人也一同笑了起来,笑声奸诈狡黠,震耳欲聋。
为首那人道:“阁下身配宝刀,又岂是俗世商人?嘿嘿,这样,既然你是商人,就把那把宝刀给我。”
向靖榆道:“此刀乃家传之宝,恕难从命。”向羽挺身道:“父亲,何须同他们多言,待我去取他们的性命。”说完,拔剑纵身跃去。
为首之人冷笑道:“黄毛小儿,口出狂言。”向羽只觉身边急风吹来,一眨眼已然又三人落在自己身旁。
向羽急忙使出家传剑法中的“大漠孤烟”一式,格挡住三人进攻,那三人皆是使长刀,这招“大漠孤烟”靠的是速度,在一瞬间刺出数剑,因此也可以抵挡住多人攻击,但向羽只觉那三人招式凌厉,只得且战且退。
向靖榆见状,立刻拔刀出鞘,前去解围。只见向靖榆执刀一挥,那三人的兵器全部应声而断。
“羲皇出鞘逐天下,唯有伏血决雌雄,当世两大神兵之一的羲皇刀,果然名不虚传。”为首那人道。
向靖榆冷冷道:“既然知道是羲皇刀,那你可知道我是谁?”那人道:“武林中素知,两大神兵,伏血剑乃铸剑堂的镇堂之宝,至于这羲皇刀嘛,乃西楚天蚕军统帅向靖榆之佩刀。嘿嘿,鄙人见过向帅。”
向靖榆道:“在下向靖榆,今日就当同诸位交个朋友,还望诸位不要为难我和犬子。”
那人不语,冷眼看着向靖榆道:“向帅名满天下,我等粗人,本是不该为难您,只是……”向靖榆道:“只是什么?”
那人道:“只是,有人请我等来向您取一样东西。”向靖榆问道:“尔等是冲着本王而来?不知阁下要取什么东西?”
那人从怀中取出一块白色锦帕,帕上绣着一只盘卧的猛虎。“向帅见到这个,就应该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吧?”向靖榆面如土色道:“他……他真要杀我?”
向羽见父亲冷汗直下,他知道父亲征战多年,早已是沉着冷静之人,此时面露难色,定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父亲何故如此?”向羽问道,向靖榆显是受了什么刺激,喃喃自语,并不理向羽,向羽又转头向黑衣人怒斥道:“我父亲乃大楚战王,你们在大楚境内杀害大楚皇亲,尔等……尔等不怕死么?”
那人道:“哼,拿钱消灾,自然是不怕,向帅您是自己动手,还是我等替您效劳?”向羽大吼道:“混账东西,要杀我父亲,先过我这一关。”
说完,拔剑御敌。为首那人单手一挥,十余骑同冲下,向羽忽觉背后一阵凉风,只见向靖榆闪到前面,道:“休伤我儿性命。”
向氏父子同黑衣群骑打斗纠缠,那些黑衣人并不下马,居高临下,向羽虽是游走江湖,武功不弱,但此时也抵挡不住,身上被割伤了好几处,很快便被擒。
向靖榆被围在中间,但那羲皇刀乃是削铁如泥的神兵,黑衣人的兵器皆被斩断,一时间竟无计可施。“向帅难道不顾令公子之性命么?”
向靖榆见爱子被胁迫,当即住手。思虑一番后,提刀抵住颈部道:“尔等怕是跟踪我多时,不就是为了向某一条性命么?我一死,便可放我孩儿么?”
黑衣人道:“我等保证,不伤令公子一根汗毛。”向靖榆苦笑了几声,朗声对向羽道:“羽儿,活下去。”
向羽见父亲眼里满是绝望,他从未见过父亲流泪,这是第一次,竟也是最后一次。向靖榆滑刀割颈,暗夜中,一个黑影倒了下去。
“父亲------”向羽撕心裂肺地叫道,自道在世上已经没有双亲,也没有活下去的打算了,只求敌人能快些结果自己,好让自己快些与父母相会。
“检查尸身,那把刀也要带走。”向羽见黑衣人还要侮辱父亲,气急败坏地叫嚷着,但自己缚于敌手,无可奈何。
“这小子怎么办?雇主可是要求灭门的?”“斩草除根,把他丢到谷里喂狼。”
黑衣人见向羽仍吵闹不堪,动手扇了向羽一巴掌,向羽登时昏去,不省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