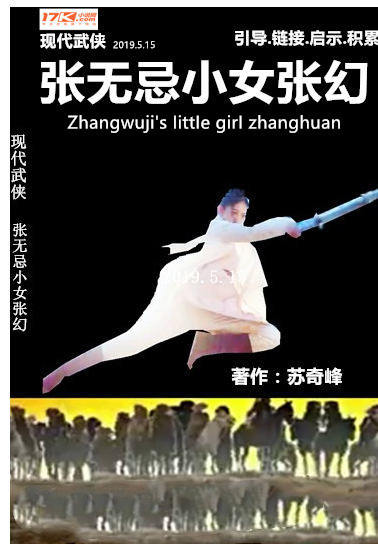司徒安史狞笑道:“蔡长老此番可是立了大功,待我回到京都,定向陛下禀告。”那蔡长老听完立刻欣喜万分:“大人您的大恩大德,小人没齿难忘。”
司徒安史又问道:“那冥顽不灵的蠢人如今在何处?”“大人,我们首领如今被关在太乙洞中,仍是不吃不喝。”
蔡长老忐忑地答道。向渊不禁心头一颤,暗道:蛮族首领如何被囚禁?这司徒安史又是何时有所密谋的?
却听得司徒安史暗哼一声,道:“那便让他绝食而死好了,蔡长老,他不听我的,待到我替陛下铲除逆贼后,你便是蛮族首领啦。”司徒安史一边说着,一边拍着蔡长老的肩膀。
蔡长老阿谀地点头,嘴上说着令人作呕的恭维之词,司徒安史倒也吃这一套,整个人听得飘飘欲仙,仿佛自己便是整个帝国的忠臣良将一般。
冷不防“嘭”的一声,显是门被人踹开了。向氏父子听得司徒安史道:“丁贤侄,快快请进……你先下去吧。”
向渊听他前一句十分客气,又叫丁贤侄,料想那人是皇属军统帅丁隐,而后面的话语气中含着轻蔑之意,显是对蔡长老的命令,蔡长老只得微微诺诺地退下。
丁隐道:“司徒大人好大本事阿,东瞒西瞒,凭一张巧嘴把所有人耍得团团转呐。”司徒安史忙道:“丁贤侄何出此言阿,如今粮草已备好,只需运往大军所在的祈县,大军补给一到,还怕灭不了逆贼?”
丁隐怒视着司徒安史:“借蛮族之粮,灭完天蚕军,再回过头来剿灭蛮族,是么?”司徒安史本想顺着丁隐的话再好好谄媚一番,一抬头却见到丁隐一双眸子死死地盯着自己。
“我丁隐绝不做如此卑劣之事。”忽的从屏风中传出一道声音:“丁将军此言差异,大丈夫建功立业,岂可在意那些婆婆妈妈的琐事。”
向渊大吃一惊,在屋外蹲了许久,竟丝毫察觉不到那人的气息,显是内功醇厚之人。又听见丁隐道:“不知是哪位前辈,处于屋中在下却丝毫没有察觉?”
那人道:“在下信陵裘无涯。”“信陵阁?莫非是我恩师请前辈前来相助。“向渊听丁隐的语气十分恭敬,心道信陵阁的名号似乎是听过,约莫是北方的门派。
司徒安史附和道:“丁贤侄呐,这位裘先生可是严太师特意请来相助的呀。”裘无涯道:“严太师有恩于我,他老人家有命我定然义不容辞,老夫定助丁将军一臂之力,只是……”
“只是什么?”丁隐问道。裘无涯冷笑一声,道:“只是得先除掉这偷鸡摸狗的小毛贼。”
话音刚落,身影闪至窗外,向靖榆眼前一黑,胸前早已中了一掌。裘无涯身法敏捷,比北境四魅还要快许多,向渊一下也未能反应过来。
待到裘无涯欲出第二掌,向渊立刻跃去,右掌扶住向靖榆,情急之下,左掌使出十足功力的“乾天掌”。
一时间,二人对了七八掌,裘无涯一开始在屋内只听得向靖榆的呼吸声,全然不知还有另外一人,因此一开始进攻的便是向靖榆。
此刻对了七八掌,只觉得那人掌力热焰,似乎同自己的内功相克,并无胜他的把握,当即运气聚力,将真气聚于掌中,打出一招“魄绵掌”。
向渊仍以“乾天掌”向迎,两掌相对,激起一阵气浪。裘无涯被震退了七八米,向渊则携着向靖榆踏步飞去。
“向……向渊?”司徒安史慌道。“不错,那正是向渊。”丁隐望着向渊离去的方向道。“前辈见谅,方才只顾看您同向渊打斗,而忘却号令卫队前来相助。”
裘无涯摆手道:“那人武功奇高,纵使人数占多也困他不住。”夜幕暗沉,此时司徒安史和丁隐都没有看到裘无涯在暗夜里露出的阴笑。
向渊抱着向靖榆飞奔于屋檐上,向靖榆此时已是昏迷不醒,向渊心急如焚,来不及细想便往楚氏兄妹家的方向走。
楚氏兄妹于睡梦中被吵醒,向渊将向靖榆安放在床上,道:“劳烦二位烧些热水。”楚氏兄妹也并没有多问或抱怨,匆匆忙忙地烧煮热水,楚慈望着向靖榆苍白的脸心里满是忧虑。
向渊激气入掌再传于向靖榆体内,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向靖榆吐出一股鲜血,脸色更加憔悴。
向渊心中暗道不好,忽闻门外传来声音:“向帅功力深厚,只是令公子之伤非内力所能治愈。”向渊飞步出门外:“裘先生乃武林人士,何以要插手朝堂之事?”
裘无涯冷笑道:“在下受严太师托付来助,只是还有一个私愿,只要向帅可以替我解答,令公子之伤鄙人保证治好。”
向渊嗔视裘无涯道:“只要能救我儿性命,但说无妨。”裘无涯讪笑瞄了向渊一眼道:“向帅可否告知我凤凰门之所在?”
听到此话,向渊眼里的光芒一闪即逝,道:“裘先生此话在下实在不明,凤凰门乃神秘之至的门派,武林之人尚且不知,老夫身处朝堂,如何得知?”
裘无涯“嘿”的一声,又续道:“一年前,我在孤傲峰大败李相儒,从他口中得知您便是凤凰门门主的大弟子,向帅放心,我如今连您都打不过,又怎能对凤凰门如何?鄙人只不过是仰慕武学至尊,想向其讨教罢了。”
向渊缓缓道:“不错,我确是凤凰门弟子,李相儒便是我成师后的第一个对手,老夫出师多年,又身处朝堂,世人早已忘记我的师从,阁下今日重提欲拜访我师本是无妨,但师门严令,出师弟子不得擅自泄露师门所在,阁下的忙在下帮不了,至于犬子的伤,相信阁下必有解药,你若不给,老夫夺便是了。”
裘无涯只道向渊迫于爱子的伤势会屈服,岂料向渊如此刚硬,一时间陷入僵持之境。忽听得嘈杂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待到近些,只见司徒安史和丁隐带着蛮族卫队将房子包围起来。司徒安史大喝道:“将谋害蛮王的贼人拿下!”
楚氏兄妹起先听二人对话,听见裘无涯对向渊的称呼,已然惊讶万分,此时家中被重兵包围,更加不知所措。
楚良慌相领头的司徒安史道:“大人恕罪,家父曾官任老蛮王的侍卫长,小人一家都是忠心于蛮王的良民,绝非包藏祸心之辈!还请大人明鉴!”
他这话讲得不卑不亢,司徒安史听完脸上挂不住,不由得怒火中烧,急忙扇了楚良一巴掌,指着向渊怒道:“此人乃朝廷逆贼,你窝藏他亦是重犯,来人抓起来。”
司徒安史手一挥,卫兵立即将楚良按到在地。“住手。”黑夜中,一声虚弱的叫喊显得尤为响耳,向靖榆倚在门外,楚慈急忙扶住他,焦急地道:“向公子你可还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救救我哥哥阿。”
向靖榆摆手安抚她,接着道:“要抓便抓我一人,放过我父亲和他们。”丁隐朝着向渊道:“今日之事,只要您束手就擒,其他人,可以放了。”
向渊沉默不语多时,暗中观察情况,只盼可拖到有所转机之时。但他知道此时已是绝境,自己纵然能全身而退,也保不了其他人。
裘无涯见向渊有所迟疑,千钧一发之际,闪过身躯,瞬时封住向渊的发功要穴。“委屈您了,待到了京都,一切是非曲折,您自相陛下禀明。”
丁隐拱手道。却听得司徒安史急道:“夜长梦多,将逆贼就地正法。”话音刚落,只见黄脸汉子手持羲皇刀朝向渊斩去,向渊被封要穴,已是无法动弹,向靖榆欲前去相救,无奈身受重伤,踉跄几步后便倒下了。
眼见那刀便要斩到向渊,黄脸汉子但觉左臂一麻,丁隐用刀背抵住黄脸汉子的手臂便说道:“且慢,司徒安史,生杀大权,岂是掌握在你的手里,你想谋反不成?”
只听见卫队群中有人有人小声嘀咕道:“司徒安史?”向渊知道丁隐一时失言,生死攸关之际,朗声道:“各位,我乃蜀州节度使向渊,诓骗你们捐粮之人才是司徒安史。”
此语说完,蛮族卫队议论纷纷,司徒安史大叫:“混账东西,逆贼的话岂可当真。“蔡长老也附和道:“大家别被那人蛊惑。”
话音刚落却听得屋檐处一道声音传来:“依本王看来,你才是蛊惑之人。”众人朝那边望去,只见说话那人被另外两人搀扶着跃下屋檐。
蛮族卫士一见那人,一齐“扑通”地跪在地上,“拜见大王”蔡长老瑟瑟发抖,瘫软在地道:“大……大王,臣……臣有罪。”
蛮王怒哼一声,道:“你真是狼子野心,本王真是信错了你。”在蛮王说话之时,搀扶他那二人一齐奔向向渊,正是李护与向靖炎。
原来,李护寻觅几日后已集齐了大部分天蚕军,为防再度同敌军相遇,便率部朝深山处靠拢行军,阴差阳错之际竟遇见蛮王被囚。
李护救出蛮王后,继续向深山处靠拢,又遇到了向靖炎,二人商议后,决定先护送蛮王回寨,于是便遇到了今晚之事。
李护帮向渊解开各穴,却发现要穴中有内力阻隔无法完全解开,向渊道:“无妨,我急运内力冲荡,片刻便可借,你们先去看看榆儿。”
丁隐早便对司徒安史的行为有所不满,此刻情势逆转,心中更是愤怒:“司徒安史,你行事不择手段,我丁隐实在难与你共事,待会我与裘先生,北境四魅一同护送你出寨后,你我便分道扬镳,至于以后之事便要到了京都请陛下定夺了。”
司徒安史刚想挽留,却听得向靖炎说道:“丁将军还不知么?京中早已大乱,还回去作甚?”丁隐冷笑道:“京中之事你远在南境如何得知?且不用说京中还有我师傅,又如何乱得了?若是你想由此让我投降,此计未免太过可笑了。”
向靖炎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道:“我在山中养伤十数日,几日前,一名身受重伤,又着京都官服的男子被我所救,他自称是御事使陈登,要找的人,便是丁将军你。”
丁隐沉默不语,他知道向靖炎并未到过京都,无论如何,他师兄陈登的官职姓名是不可能随意胡诌的,但内心却任不愿相信。
向靖炎将信件抛给丁隐,又续道:“严老太师征战北境过于操劳,于班师回京途中病逝,没有老太师的镇压,朝中各股势力相互排挤,各地节度使也发动叛乱,如今,连陛下也无能为力。”
在听到严太师逝世的消息时,向渊,裘无涯等人都大为惊诧,丁隐急忙打开书信,确认书信的封口是恩师传书的特有印记后,丁隐查看完书信,与向靖炎所说并无差异。
此事对丁隐来说便是晴天霹雳,恩师从小收养他,教他成人,又传授他为臣之道,当护黎民,建功立业,此番他来蜀州便是想建立一番功业,岂料那日与恩师在城门口的告别竟是最后一别,此后便是阴阳相隔。
丁隐想到这些,早已泪流满面,“我恩师一生,为国为民,却斗不过你们这些沽名钓誉之辈,忠臣良将,竟无法存活于世?哈哈哈……哈哈哈……”
丁隐指着司徒安史一阵大骂,司徒安史刚想辩解,只听得丁隐苦笑道:“该杀,该杀……”司徒安史一边发抖一边道:“丁将军……你……你欲何为呀?”
丁隐一边嘟喃着,一边抢过身旁黄脸汉子手中的羲皇刀,一刀斩向司徒安史,司徒安史哼都没哼一声,便倒在血泊之中。
漫漫长夜中,众人只听见阵阵撕心裂肺的啜泣声。忠臣良将,若是被君主所不重视,为身边污浊环境所排斥,也只不过是平添一丝哀怨和遗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