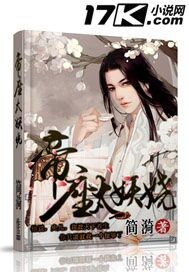在际水眼里,务笛和启然之一般年纪,她不会弄混他们两个。
然而际水第一次见到务笛是在知介花园,她看见还是小孩的务笛贪玩跑进那里。务笛被她吓到,哭得泪水流了一脸。后来她送给务笛梅子酒,至少那个时候她认为这个小孩会非常喜欢,不过这些想法在看到务笛心惊胆战地把梅子酒倒掉后就不存在了,再后来,他们在一场宴席中碰到。务笛是中阶神明,所任职倒还轻松,际水一直认为他做不了其他事,就这样坚守自己的小岗位也是好的。
不过她总把务笛和另一个影像混淆,她在恍惚混沌中看见伸出手,递过去一瓶梅子酒,到底是务笛接住了,还是其他什么人,她也不太清楚,她只能看到一双稚嫩的小手接过那瓶酒。
是个孩子。
是个孩子......
她的朋友少,从以前到现在能说上话的朋友也总就那几个。务笛是其中一个,然而这事说起来也算玄乎,她和务笛成为朋友这事本身就很魔幻,难以捉摸。务笛直到现在都对她有一种本能的害怕,据他说是小时候吓够了。
际水就是他孩童时期的噩梦。不过这并不妨碍际水在得空的时候找他去说话,务笛工作少,而且没有时间期限,际水也不怕打扰他。在易风卸职去人族之境后,她也没办法时时去找易风,务笛就自动被她定义为茶友。事实上是务笛收集的各色茶叶多,且质量上乘,际水自然来他这里蹭点,务笛倒是自然得不出声,任她去了。
务笛有时也想不明白,这万人景仰的南王镇主咋就怎么喜欢跑他这里来,是他这小地方格外香吗?后来他想明白,她的目的真的十分单纯,真的是他的茶实在太香,还有,她也不是如传闻所说,见人远矣。只不过不愿意与其他众人说话,自己在私下还是与朋友会说说。务笛本来觉得自己作为南王镇主的“朋友”这事有些荒谬,但际水自己毫不介意,次次厚着脸皮和务笛说话,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就两句,要是心情好起来,那他一时半会都脱不了身。只能在旁边无奈地抿茶。
可能那些在远处观望的神或民众,都认为她该是是独自一人,清心寡欲。
与其说是精心维持这种在外人面前的印象,到不如说是习惯了。谁还不是有多重性格呢?对于一个活过这么多年的神明,时刻保持清醒,于是消磨了热情,偶尔兴起多说了几句,也只会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至于内心里究竟想的什么,还是没办法说出来。他们为这种清醒感到痛苦。
务笛不懂这些,他过他比之其他神明要随性些的日子,听民间的音乐,收集各地寻来的茶叶,观察神界工作场上的动静,守着一方安乐的地盘,不去撩拨招惹别人,也自没有神想起他,这院里总是冷冷清清。他希望是热闹的,希望有神空闲时来拜访,可无奈他的存在感极低,这地方倒像是与神界隔离了似的。
际水大多时候过来心情都很低沉,因此这位极富盛名的神明踏足自己的院子时,他都觉得这院内的空气又冷上几分。至于际水说过的那个有关于梅子树和少年的梦,他也不记得自己听过多少遍了。想想自己这个狂躁的性子被磨得这么平和有耐心,一定有际水的大功劳。
原来那些站在高处的神明们并不是不会有情感,只是基于工作需要隐藏起来了而已。他们也有自己的缺点,不是事事都顺心,也会有执着或做错的事。好多以前从未懂得的事,自遇见际水后,就慢慢懂了。
茶香总是隔在他们二神中间,雾气很浅,一股清香散开,四处缭绕在发丝眉梢,务笛时不时被她的眼睛吸引,她喝茶时眼睛里的东西柔和下来,很清亮又朦胧,不再让他有那种不必要的恐惧,细细想来,她的眼睛真的很美。神界的事总是很多,际水有时闷声喝会儿茶就走了,他告别她后还会坐上一刻。
真奇怪,孩童时期一直害怕着的神明竟然变成朋友,生活可真是出人意料。
但她也不是一开始就经常来他这里。好像自从那场万年前的宴席后她就变得奇怪,她取了面具,很少戴上,眼神冰冷,神情淡漠。再过些时日,际水会来他院里说上一些奇怪的话。说到底,他也不太清楚宴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失踪了一些神明是真的,但日初大人封锁了消息,说是内部问题,出了意外,没有神去过问,他们原是没有资格去干涉身外事的。他呢,与他无关的事也不去探究,是日初大人的意思,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那个时候际水噩梦做得多,他偶尔猜想,会不会与宴席上的事有关?可她干嘛要总梦到梅子树和孩子呢?梅子树和孩子代表什么吗?因为他还是孩子的时候际水给过他梅子酒,所以际水才会认为梦中梦到的是他。但是看过际水的表情,却又不是那么回事。
他有理由相信际水在掩饰什么,总觉得她一直在自我欺骗。或许她知道那梅子树与孩子出现的缘故,但是始终不愿意承认。
她不说的,他就不多问。
不过后来际水去星启学院,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来。现在她又去了,不知道是什么事。
务笛原本以为际水在学校工作这段时间就不会联系他了,那套茶具还放着,也为她留了个位置,也算欢迎这个客人。这些天际水竟然给他开了视频通话,说的还是以前那些话。以前际水只亲自来他这里坐坐,一般不是特殊情况都不会给他开视频通话,但他现在看这种场面有一点别扭。际水在他眼前的一大片信息投屏上面,她正喝茶,和她以前一样,苦恼地和他分析她的新梦境,聊着聊着话题就会变歪,不过他并不在意。
际水问道:“你说,我要是有一个狂热的粉丝怎么办?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又逃不开。”
务笛疑惑:“你还有逃不开的么?什么人能影响到你工作,我倒想见识见识,这挺新奇的。”
际水盯着手中的杯子,思虑一刻后还是回应道:“这真不好说,要是有一个人老盯着你你不会感到别扭吗?那还怎么做自己的事?”
“是吗?”务笛笑道,“我每次盯着你看你都没发觉过。”
“什么?”
“没什么,不重要。”
她听见了,这小孩,整天脑子里在想什么呢。她想了想,这话和他说了也得不到答案,于是转回到原先的话题上来。
“做了一个新梦,梦到和我长得一样的人偶,挺逼真的,说了一些奇怪的话,说着让我去死,你说,这是不是在预示什么?”
“长得一样的人偶是另一个你自己啊,想象另一个你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方,多年忍受痛苦折磨,终于有一天被放出来了,发现外面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不一样,竟然有这么多新奇温暖的事,而自己却忍受过痛苦,于是心理不正常,产出疯狂的报复心理,一看见你就不高兴,还决心抢走你的快乐......”务笛瞥眼见际水听得认真,也觉得好像,于是又接着编,“但是她是虚幻的,她嫉妒你,她抢不走你的幸福,就希望在梦里毁掉你啊,不用担心,她能把你怎么样?不过是个梦而已。”务笛一本正经,满意地点点头,真心佩服自己的分析能力。
际水愣了愣,反应过来后也笑出来,“真像那么回事,我都要信了。”际水知道他在开玩笑,不过她就是想听务笛胡说八道,她从不信解梦一说,只是找个安慰罢了。务笛多年来已经根据她此前的梅子树梦分析出了数十条可能原因,前因后果都分析了个遍。最后不是也没改变什么么?
现在际水见到务笛就会想起启然之,除了看上去的年纪差不多外,她也说不出来他们有什么相似点。而且他们还有最相反的一点是:对于梅子酒的态度。务笛闻不得那味道,尽管梅子酒的味道不难闻;启然之却喜欢极了她的梅子酒,看得出来他对梅子酒有着一种奇怪的执念。
“际水啊。”务笛叫她的心里还是微微发颤的,他很少直接叫她的大名,即便际水当他是朋友,相处就随意了些,但务笛也很清醒,在神界,以他的身份,他是要恭恭敬敬叫她“南王镇主”的,这样称谓她“际水”,已经是不敬了。
际水在神界不在意别人叫她什么,自然也不觉得务笛有什么不妥。
要是哪天务笛见了她之后,低着头,认真而谦卑地叫她“南王镇主”,那才真叫可怖。
“怎么了?”
“照顾好你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梦,都是假的。”
际水笑了笑,这些年小孩们怎么都这么对她说话,她多活这么多年,还得让小孩们担心自己的喜乐,也不免好笑而辛酸,这里她也明白,为什么她会根据务笛联想到启然之。
他们对她说话的语气真的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