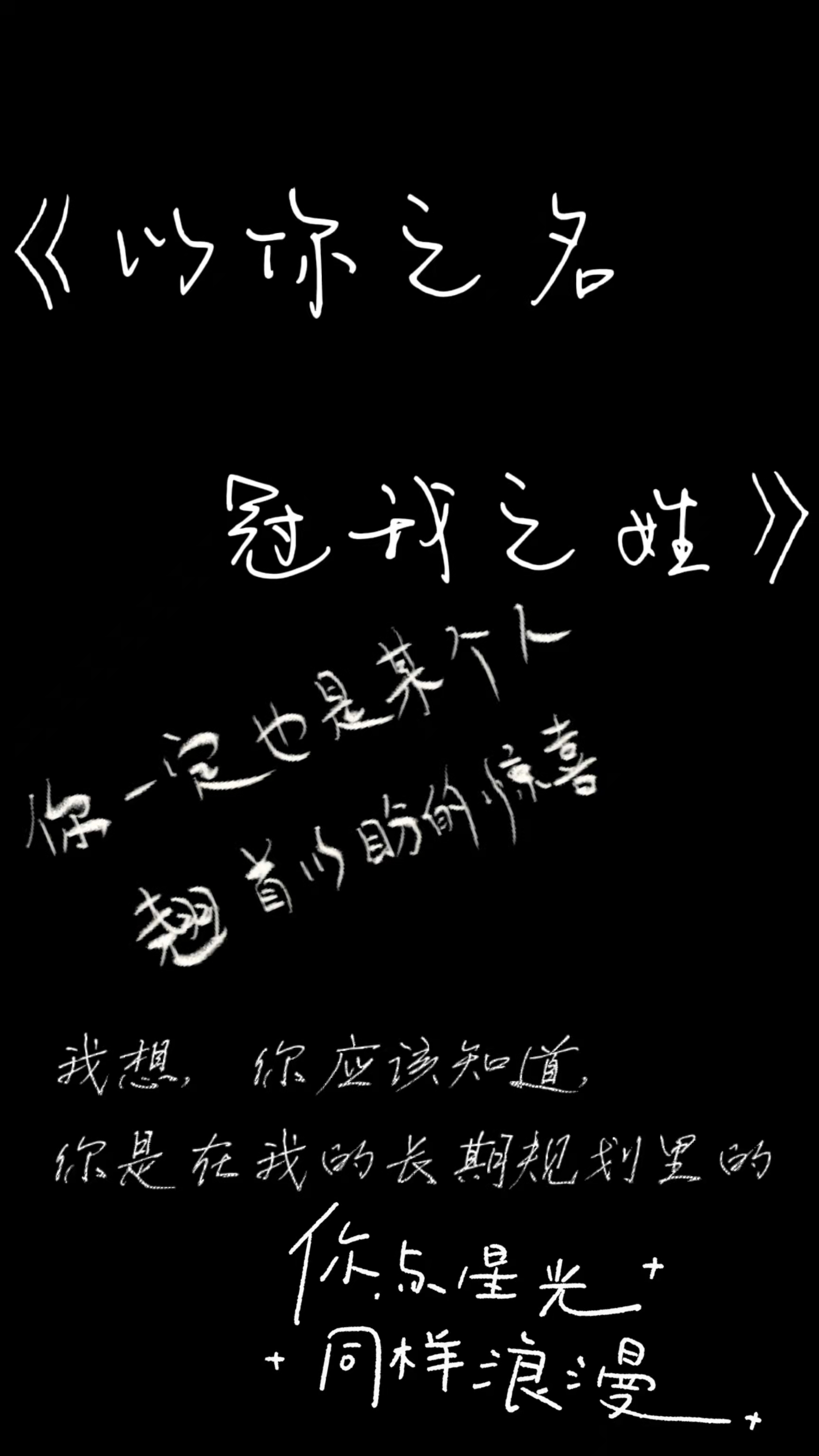他虽厌恶透了那些人,但也不会格外刻意避开。
妖族鬼族本就身份低贱,在四族之中是处于低端,而这个地方,不知在哪个犄角旮旯里,落后肮脏。
他能看见一些孩子被他们的父亲家暴,被追着打,吊在树上,扒光了衣服暴露在一众行人的目光中,心智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又羞臊又清楚感到皮肉之苦,起初捂着脸不住地叫喊,但没有谁上前帮忙,行人们只是像看戏一样观赏,从喉咙里发出“啧啧”的声响,戏谑又好奇的神色便在那孩子身上游走,似乎凌迟的酷刑。身上的痛楚模糊,那孩子像掉进一口大缸,四壁都是坚硬而真实的黑暗,敲打着扑腾着,接着他感到水注从大缸底部升起,口鼻里灌满了水,他快要溺亡。无法呼救,接近窒息,连眼泪也被淹没在污秽不堪的水里。在父亲看来,这不过对孩子小小的惩罚,孩子不过多久就会忘记,毕竟他是被敬爱的父亲。
只有棍棒落在孩子身上,他们才不会忤逆自己,质疑自己在家中的权威。
孩子喊得嗓子哑了,天色渐凉,行人也看得久,虽觉得乏味,最后却饶有兴致地叹息一声,当作是对这场表演的评价。接着便都离开了。只剩孩子停了呜咽抽泣声,眼睛是肿着的,双手垂下,像一条晾干已久无人收的死鱼,鱼肚白翻弄在外,鱼眼里只有绝望和空洞。那父亲在这场盛大的狂欢落幕之时,用握住的棍子拍打孩子的肚子,穷凶极恶的脸上突然显出几分温柔神色来,磨刀一般笨重粗糙的声音里是一串不咸不淡的句子,“你知道错了吗?知道错了就放你下来。”平时别人总压着他,可他自己的孩子还管不了么?不吃点教训总长不了性子,他这可都是为了孩子好啊。要是他不听话以后性子变坏了,也是要怪他不会教养的。
孩子沉默许久,父亲不耐烦起来,扬起棍子,孩子见那棍子身体条件反射地抽动一下,浑身颤抖,不住战栗,便怯怯点了头。父亲喜出望外,却要装作气定神闲的样子,扬起头,似有嫌恶的动作解开绳子。孩子被放下来后遮住隐私部位,父亲踢他一脚,“娃娃毛都没长齐,还会害臊么?”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那孩子瘦弱的身躯上布满棍痕,青一道紫一道,还未站稳就被踢翻在地,伤口在碎石砾上磨开血迹,疼得像浑身涂了辣椒油。“怎么这么没能耐,还起不来了是吧?我那时不也是被打着长大的?你是废物吗?装什么装,起来!”接着便被那好父亲掐着后颈脖拽起来,拖着回家。
间或有行人注目,那父亲皱眉举起棍棒恐吓,他们也便转过头去,当作没看见。总归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又不是自家的事,管那么多干什么?
毕竟,这事见得多了,小孩子嘛,不记仇的,又打不坏。
向父亲认个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不然养他作什么?
这不是很正常么?
启然之在旁边冷眼旁观着,看完全程,心里直犯恶心。
那孩子跪在地上求饶,眼睛肿得快要看不见眼珠,脖子上的指印发红,头被磕破了血染在地上还不停说自己错了的时候,启然之吐了出来。
这个地方是他自己来的,是无可选择的决定。他往前走一步是泥沟,往后走是悬崖。
或许那孩子回家后,母亲问起伤痕,父亲大概会说:“不过是轻轻打了一下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还经不起这点疼?”或许那父亲也会把母亲狠狠教训一顿......不对,那孩子早就没有母亲了。至于母亲么......受不了这样残暴的丈夫而逃了......旁人怎么说,旁人嘲讽说他没本事没用才让自己的女人都跑了......此后只要那孩子在外面多玩了一会儿都会被他按着脑袋毒打一顿,说孩子也想像那贱人一样跑得没影,便把气全撒在孩子身上。
他的脸全让这娘俩给丢尽了!
启然之看到街上有暴乱时,拿着刀到处砍的彪形大汉怒目圆睁,女人被扒光衣服扔在墙角,烂菜叶被踩在脚下,臭鸡蛋的气味充斥鼻腔。脏话声此起彼伏,谩骂和抱怨是日常生活的主旋律,鄙夷和嘲讽是最常见的人物风景。爬山虎依墙蜿蜒,糊满整面墙壁,小孩子在爬山虎下哭,把泥土往嘴里塞,一条手腕粗的青蛇骂骂咧咧经过,远处卖菜的小贩又缺斤短两,被揭穿后拒不承认,梗着脖子骂着脏话.....一只瘦小猴子被钢圈拴住,耍猴人拿着鞭子站在后面,那猴并不动弹,呆若木鸡地凝视每一个围观的行人,鞭子刷刷打在皮毛上,霎时皮开肉绽。可那猴全无反应,眼色涣散,痴傻样子。从围着的人群中扫视一遍,最终目光定在启然之身上,那猴的眼珠黑色瞳仁聚拢,直勾勾盯着启然之,怜悯而同情,启然之心里赫然一惊,愣怔着,而后转头跑回那间破烂的屋子。耍猴人又急又躁,面露羞色,额上出了汗,观众抱怨声声,那鞭子便也死死向猴子抽去,猴子像是受了惊吓,嘶吼一声,呲牙扑向那人,朝那清瘦病态的脸上咬去......一阵惨叫。
众人还惊魂未定,天空阴沉下来,阴云蔽日,寒风呼啸,倏忽下了暴雨,街上那些烂菜叶、鸡蛋壳、血迹全顺着水流冲刷下去,原本热闹的街上只剩了雨声,一切好像都平静下来,余人一哄而散,空气里泛起腐烂的气味。是肉的腐烂气味和果蔬的腐烂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雷声轰鸣阵阵,一道光影划破天际,雨声被放大一般,草屋外笼罩层层叠叠的阴森之气,启然之深切地体味到恐惧,瑟缩在角落里,双臂抱住膝盖,头紧紧埋着。
此刻没有咒骂和撕扯声,明明是纯粹的雷雨天气,却惊得他出了一身汗,这种恐惧不明缘由,只是在他心中沉淀,化作一架铁丝笼子罩住他。他想起猴子那诡异眼色下的同情。像极了有感情能思考的正常人,反倒围观的群众像邪祟鬼魅一般......那情形不断在他眼前闪现,在他脑内一遍遍回放,他下意识逃避,却又无处可躲。
好像掉进深沟里,他似乎也能够体味那被打孩子的感受,心里升起一股哀怨之气,可这怨气很快就被无力感掩埋。搁浅的鱼是无力挣脱的。
当黑夜铺天盖地袭来,雨声渐停,他一阵哆嗦,翻身趴在床上。说起来,喉咙像被扼住,被绳索勒着,呼吸声像浪潮一样。
但他很快平静下来。
这样的日子或许还会持续很久,他必须忍着。
后来......是万顺茶楼的老板娘见他孤身一人,又从他那孤僻的性子里看出他的聪颖隐忍来,便邀请他去茶楼做工。老板娘是妖族的,曾经也算富贵人家,后来家道中落,但手上还是有些资产,便开了这间茶楼。多年苦心经营,才到了如今这样规模,宾客不断。这间古朴的茶楼是开在原先那条街的尽头,隔了一段竹林,不太显眼,需得穿过一道浅沟和那两排竹子才寻觅得见,也算清净,避开那些争吵的俗事。
他已去茶楼后,老板娘待他极好,从不强迫他做什么,且事事尊重他的意见,与人说话时声音也总是轻柔的,周身皆是大户人家女儿的大气度,也不乏对通情达理的待人之道的贯通意。于是店里也总多了几分温情,因来客都是老板娘见过的,是真心实意来品茶,并不是碌碌平庸之辈,皆是文雅之人。茶楼似与那不远的街巷天差地别,像极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说起来,老板娘算得上他遇见的贵人,他以后要报答的。
再后来......再后来发生了许多事呢,它们重要么?既是鸡毛蒜皮,不足为奇的小事,提及或遗忘都是一样的。只是他影响深刻的是,老板娘的茶楼旁也手植一棵梅子树,枝叶繁茂,常常有鸟雀栖息,鸣声宛转悠扬。他做工或练习幻术累了,就坐在茶楼楼梯上望着那树。
树下的神明,可还记得他?
想吃梅子吗?老板娘偶尔打断他的思绪,温婉的笑像他怀念的梅子酒一样甜柔,她看那树,眼神柔软得似水波荡漾,好像那树也是活生生的人,能与她开口说话一般。不对,梅子是用来酿酒的。他轻轻地答道。
再后来些......
启然之手指抵着太阳穴,有些疲倦。
想来有些事物,无论过去多久,还是会重回原先记忆里那个样子。梅子树下那位清隽面容的神明又回来了,可这中间已逾万年,万年光景,不过弹指之间。
这万年间他作了许多挣扎,在世事沉浮中得以成长起来,当他发觉自己不知为何而活的时候,心里藏掖着的东西就该一一陈列了。他也本该站于黎明处,身后便是万丈光芒,脚下该是拔地而起的山川,他也该像她一样俯瞰众生,眼里保留有高洁的傲气,而不是像如今.....在泥里打滚,沾染一身污泥,惧怕深入骨髓的凡俗之气惊扰到她。
毕竟察言观色,洞察人心这方面,他可真是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