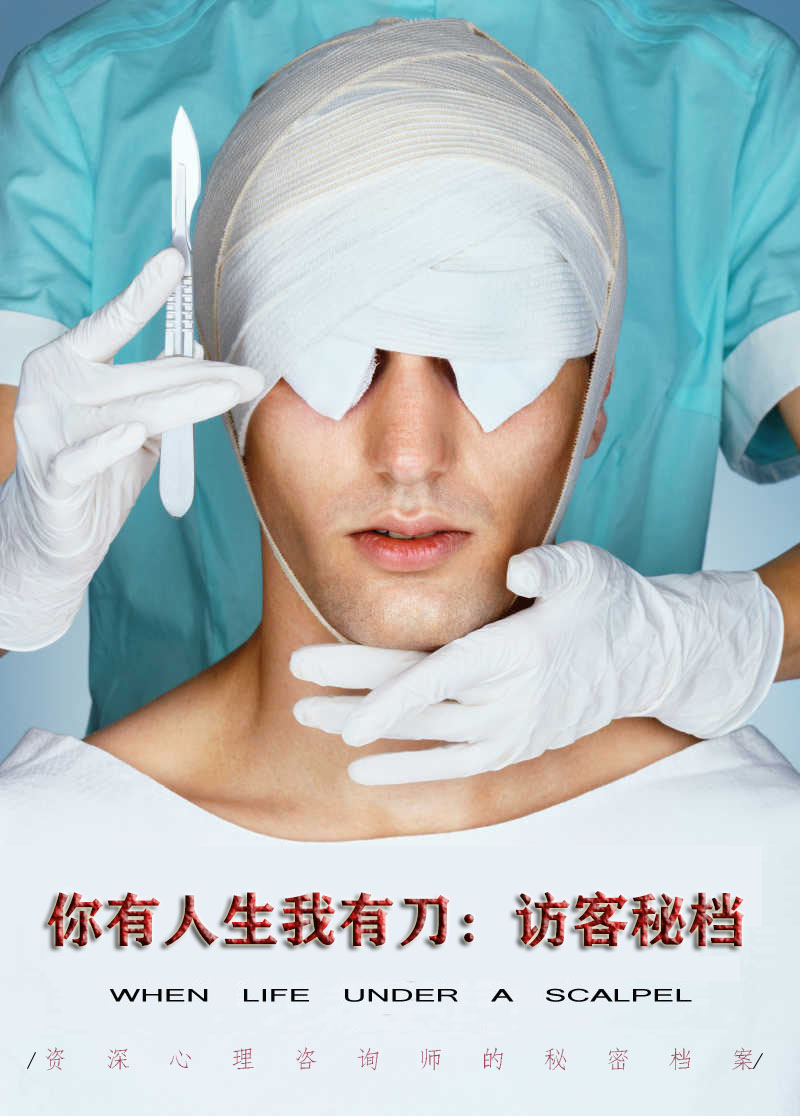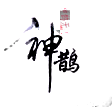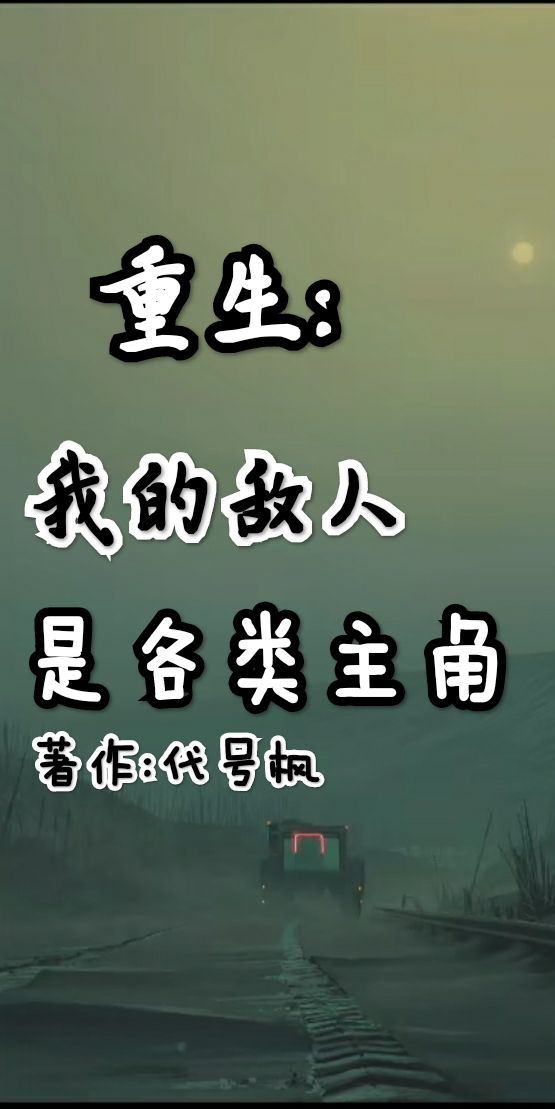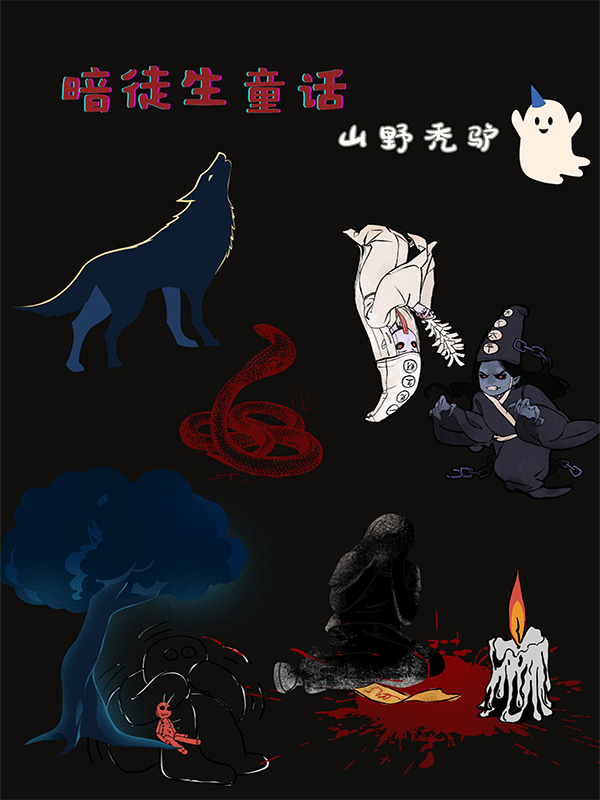初次见到方清,是在我们大学社团的介绍会上。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文学社社团,大家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那时候的大学,弥漫着一种类似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式的浪漫气氛,各种外国的新兴思想一齐涌入国内,读加缪,读海德格尔,成了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在那样一种氛围之下,相比于别的社团,文学社社团的成员不算少,并且大部分成员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对文学充满兴趣才主动选择加入的。而我之所以加入这个社团,一部分原因是高中时期做过的文学梦,那时候信心满满地以为,不久后的自己一定会成为拥有满身才华的文艺青年。不过这还是其次,更主要是因为自己当时有个心仪的女孩正好也加入了文学社,这样就有了接近她的理由。
由于每个进入社团的成员都要上台简单地做自我介绍,因此我开始注意上台的每个人。轮到方清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斜对面,离窗户很近的座位上,一个男孩站起来,迈着从容的步伐,走上了讲台。此刻,教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我注意到他上身穿了一件淡蓝色衬衫,下身穿的是深褐色的呢绒裤。站在讲台上的他,微微皱着眉头,神情严肃,说话的时候,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方清的介绍很简单,寥寥数语,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于他下台的时候,我仍然一直望着他。那时候的他也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年纪,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或者也可以说纯净,脸部轮廓分明,五官齐整,身材不算瘦弱,个子高高的,有着一头乌黑明亮的短头发,牙齿白得晃眼,皮肤白皙,偶尔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他这种长相一看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里娇生惯养的孩子才会有的,和我们这些成天在乡间小道,走街串巷,野惯了的农村孩子(我虽然出生在县城,但跟上海相比,其实县城和农村没多大差别),还是能看出区别的。但他又和我认识的,别的城市里的孩子不一样。第一次见面,只觉得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忧郁的气质,这也许会让别人产生一种距离感,奇怪的是,我竟然会被他的这种气质深深吸引,以至于有种想靠近他的冲动。
后来我知道,方清的确是一个不太会社交的人。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和写作,唐诗三百首,首首都能倒背如流,喜欢唐诗宋词,也读过四大名著,写的一手好文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让他看起来有点书生气,给人一种古代读书人特有的儒雅的感觉。有一次无意中听同年级的一位同学提起,中学时期,上海市举办过全国中学生语文写作大赛,那次大赛一等奖得主就是方清。再后来我从方清的家人口中得知,这只是他学生时代得过的所有奖项中的冰山一角。从孩提时代,方清就显示出了他在写作方面的卓越天赋,这曾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声誉。毕业之后过了很久,当我们再谈起这件事,他告诉我他始终都不太适应别人如此过分地称赞他,每次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来他家串门,他都要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因为他明白,呆在外面又会听到这些人对爸爸妈妈喋喋不休地夸奖他,他说他从来没因为长辈的夸奖而真正感到满足。
我们中国人爱攀比,什么都拿出来比较,所以从小到大,方清一直都是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口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缘故,让周围的同龄人都远离了他,所以他从来就很少有亲密的朋友,没有朋友可以互诉衷肠,他就把自己想说的话倾注在日记中,他后来养成了不管去哪都会写日记的习惯,我猜他的写作水平也是在日复一日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中逐步提高的。他的日记不仅用来记录生活,也用来创作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如果你读过他的日记,就会发现,在他已经出版的诸多部小说中,几乎都能从原初的日记里发现故事的全部或部分情节。
相对于方清来说,我的成长经历就显得简单和纯粹,从小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管束就少,这部分原因归结于他们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因而把教育的成功寄托在我身上,而这点,我从没让他们失望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面积小、人口少。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受外来的冲击和影响比较小,所以人际关系的特点仍然是靠着传统家族的亲缘关系向外扩张,民风依然显得保|守和淳朴,人际关系的纯粹,尊老爱幼传统的加持,使得家长们很少担心出门在外的孩子会有人身安全的问题。和别的家庭一样,当地父母对自家孩子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好好学习,考上一所好的大学,以便将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这种单线式的想法,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至于别的教育或出路,迫于现实的种种无奈,他们或者不愿意去想,或者压根就想不到。
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的人,性格自然也比较单纯,更主要的是,生活中我从未感受过任何巨大的压力,包括学习方面,也包括后来成家立业方面。我的人生之路一直都是平坦的,因而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神经大条的人,常常喜欢耍小聪明,爱各种运动,做事冲动不考虑后果,这些方面都和方清完全相反。他曾经用这样四个字调侃我,叫“玩世不恭”,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峰(疯)子”。只是他去世后,我才发现,真正“玩世不恭”的人,真正“疯”的人,不是我,而是他,这是后话了。按道理说,这样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是不会走到一起,成为好朋友的,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是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大学整整四年,几乎都没有分开过。我后来再想起这段往事,内心总是感概万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不时浮现在我眼前,仿佛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般。
有认识方清的人评价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这也许是对的。自我们大学认识时起,方清就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他性格中忧郁的一面,可即便如此,他当时也还没有忧郁到断绝和一切同学的来往,比如他当年加入文学社,写了很多稿子发表在学校当时的文学期刊上。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总是能给出很多适当的建议,文学社社长总喜欢征求他的意见。这些都表明他性格中的忧郁不是别人口中严重病态的,我认为这反而让他整个人都充满了魅力和神秘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文学以外,他当时的确对其他任何方面都不感兴趣。
他总是有很多奇思妙想,常常天马行空。比如他曾对我说过,历史像一个大转盘,我们都陷进去了,只有死后方可解脱出来。再比如,他也说,所谓的怪异,乃是人们先入为主的偏见,其实是不存在奇怪的事情的,理性,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我常常因他的这些言论而取笑他,说他是不是读书读疯了,整天想这些没用的东西,他则说,正是因为很多人不去思考那些看似合理的事情,所以人们常常浮在生活的表面,而不去关注生活中更加重要的和本质的东西,可是当我问他那些生活中更加重要的和本质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他也竟然一时语塞,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嘲笑他的自相矛盾和不切实际。现在想来,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因为我所说的这些话而感受到哪怕一点伤害。从他后来孤独的生活,我可以预想到,在他的整个生命中,以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的人绝对不在少数。甚至包括他的父母,他最在乎的人都这样告诫过他。如果不是他的坚持,他也许会走另一条平凡之路,我们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走过并一直在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