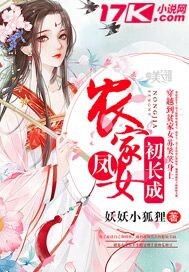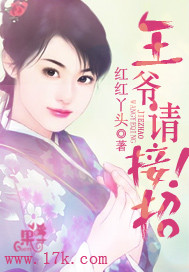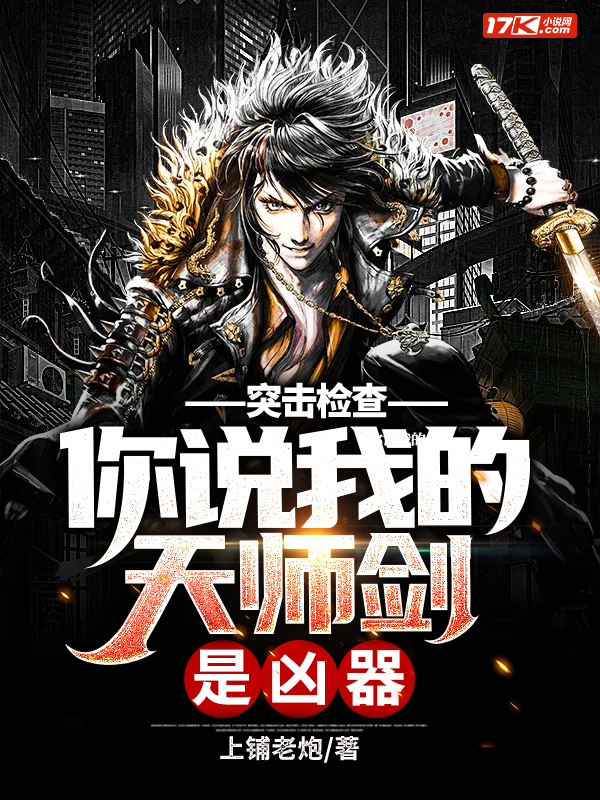方清三十岁的时候,离开上海,去了英国。那是他第一次离开祖国,离开父母。
我问方媛,方清为什么选择去英国而不是别的国家留学。方媛跟我说,她丈夫陈国立原先毕业于英国伦敦的一所知名大学,他学的是工科类的专业。虽说如此,陈国立却一直对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感兴趣,他在大学期间经常去旁听哲学系教授的课。由于哲学系的亚洲人不多,久而久之,哲学系的教授都认识了这个虽不是本专业,却对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亚洲学生。不过,陈国立并没有因此而耽误本专业的学习,而且,他的专业导师也鼓励他学习哲学。他跟导师聊天的时候,导师对他说,哲学这门学科是看起来最无用,实际上却是最有用的一门学问。一个人只学习工科而不学习哲学,就像他只看见眼前的一片树叶,却对树叶后面的整片森林视而不见一样,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不学习哲学,他就无法获得一种开阔的眼界,无法对自己所学的知识产生一种敬畏感和美感。如此而来,这些知识在他头脑中只能算是机械地重复和堆砌,日积月累,越堆越多,最后他的学习生涯只剩下了枯燥和乏味,他再也无法体会到思考的快乐和学习的真谛了。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做出伟大贡献的、最有学问的人,如牛顿、马克思、爱因斯坦...他们全都对西方哲学中讨论的基本问题一清二楚,他们在哲学上都有着很高的造诣,他们都是一群热爱知识,热爱思考,热爱智慧的“孩子”。
导师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陈国立,虽然他后来没有再专门学过哲学,不过哲学的重要性却在他心中生了根。方清年轻时对哲学的兴趣,虽然主要与他自己的气质有关,但是肯定也受到了陈国立的影响。
陈国立的父亲和方媛的母亲早年间是同一所学校的老师,两人是同事。陈回国后,在双方父母的介绍下,认识了当时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方媛,他们谈了两年的恋爱,最后顺利结了婚。以此姻缘,方清便结识了这个他后来称为人生转折点的姐夫。有段时间,由于见面频繁,陈国立经常跟方清讨论哲学问题,尤其是西方哲学。
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西方的很多思想都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可是影响力仍然仅局限于许多外国人集聚的大城市。更何况,由于中西文化上的隔阂,原著作品的晦涩难懂、以及翻译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即便在大城市,仍然只有受过高等教育且对西洋文化感兴趣的少数人才会想要了解这些新式思想。陈国立就是这样的人,他向方清系统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包括希腊三贤,以及之后的犬儒学派,怀疑派,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等各学派的主要思想,也包括后来的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以洛克、贝克莱、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等各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成就。
对于从小接受严格传统中式教育的方清来说,这些观点全都让他耳目一新,他曾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我像哥伦布一样,发现了新大陆!
离|婚以后,方清向姐姐方媛以及父母表达了要去英国学习哲学的想法,不过那时家人并不赞成他的选择,一方面,他们觉得学习哲学回来找工作是个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方清的年纪已经偏大了,学哲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最后能不能学得成,是一个未知数。
但方清去意已决,这次,他没有选择顺从父亲的意愿,他开始知道他想要什么,并勇于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了。
方清后来在一篇日记中提到过这个时期他的心理变化。他写道:平生,平生第一次,我发现了“我”,以前,我所有的关注点,都在别人身上,他们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怀着神圣的心情,激动而又不安,迎接了这个“我”的到来,它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我该对他负责吗?是的,我该对他负责!
他在这段话中,提到了两个重点:一个是他意识到了他的“自我”;二是他会对这个“自我”负责任。他后来的人生经历,似乎就是对这两方面完美的诠释。他人生的全部,从他人那里开始走向自我的回归。
以前我的确很少去想这类问题,或者说,我不愿意去想这类没有结论的、空泛的问题,因为我总觉得,这类问题不是我这种普通人应该想的。退一步说,真的想了,结果又有什么不同呢?生活不还是要过,日子不还是要照常进行。但现在,我对方清所说的这个“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我”,像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中的那个“我”一样。这个新的“我”到底是什么呢?
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确定别人是不是也有过。在我小的时候,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不同的,比如当我知道了其他所有人都会死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会死,这不是因为自己害怕死|亡,或者具备什么神奇的魔力,而只是单纯地觉得自己肯定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都会死,为什么自己就一定要死呢?那时我坚持认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是“我”,“我”当然也不是“别人”。
可是之后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这件有点令人失望的事,那就是,原来自己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特殊,原来自己真的只是万千人类当中最平凡的一员,会经历生老病死,会走父辈们已经走过的老路。如果说,孩提时代,我们还能朦朦胧胧意识到那个独特的“我”,那么这时候,很多人的那个“我”就彻底消失了。
对于“我”这个概念,心理学上说,眼前的东西,我们不一定都看得见,我们只选择自己愿意关注的部分,并把它认为对自己是重要的。我们从对自己的关注中认识自我,从物对人的关系中认识物,此时的“物”仍然是自我的一部分,因为人不可能外在于他自己去认识物。假如有一百个人愿意关注这个部分,那么这个共同被关注到的部分就成了对我们大家重要的。人和人之间之所以能够沟通,就是靠着这个共同的部分作为基础的,在这个相同部分的基础上构成了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共同体。
可问题是,一个人的感官或理性所关注的部分和另一个人的总不会完全重合,因而一个人所获得的经验和另一个人的也总不会完全相同。那么,我们怎么处理这其中不相同的异质部分呢?这样说可能读者不甚明白,我想我还是从感官和理性的角度分别举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好,假如一个人告诉我们,他喜欢异性,因为他的感官是这样告诉他的;而另一个人却告诉我们,他喜欢同性,因为他的感官也是这样告诉他的。在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谎的前提下,我们在“喜欢谁”这个问题上就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再比如,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向往自由生活,愿意遨游在自然的环抱中,因为他的理性是这样告诉他的,自由成了他衡量人生的坐标;而另一个人却对我们说,比起自由,他更向往奴役生活,心甘情愿被囚禁在牢笼之中,因为他的理性也是这样告诉他的,奴役成了他思考人生的起点。在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谎的前提下,我们在“自由还是奴役”这个问题上,也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判断这两个回答孰对孰错呢?
答案是,我们无法判断。因为假如我们承认人类的感官和理性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仅有的两种方式,那我们只能对于感官和理性中的相同部分做出判断,对于他人感官和理性中的异质部分,除了上|帝以外,我们是没有权力做出判断的,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承认异质部分的合理性。只可惜,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总是采取反对、谴责、惩罚、杀|戮等负面手段。
方清在他写的小说《无眼人》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天地的尽头,有一个叫安乐村的小村庄,这个村庄里生活着一群无眼人,他们都是天生没有眼睛,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群无眼人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靠着自己勤快的双手,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这个村庄里有一个名叫孙思奇的男孩,他从小就有许多奇思妙想,是一个喜欢思考各种奇怪问题的人,比如他会问同村人:太阳为什么会发热?人为什么要吃东西?我出生之前在哪儿?等等。同村的人没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因而不是随便用一个理由搪塞他,就是干脆不耐烦地说不知道。孙思奇显然不满意他们的回答,所以总是失望而归。除此之外,他也不喜欢像别人一样,天天只知道吃饭,工作,睡觉,重复着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旅行,而且每次都喜欢去不一样的地方,他期待在每次不同的旅行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体验。
有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决定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旅行,结果走着走着,迷了路,在攀爬悬崖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去。当他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接着他听到旁边有人开口说话。
那人用一种奇怪的语气对他说:无眼人,我是蓬莱仙翁,这里是蓬莱仙岛,众神居住的地方,你方才不小心掉下悬崖,误闯到了这里,碰到了我们,知道吗?若不是刚才我施法救你,恐怕你性命难保。
听了仙翁的话,孙思奇起身,说道:“多谢仙翁救命之恩。误闯宝地,小生万分惶恐。”
仙翁笑呵呵道:“不打紧,不打紧。你能到我这里,也算我们有缘。”
孙问道:“您能施法救我,那您一定是神仙吧?”
仙翁道:“不错,我是这蓬莱仙岛的守护神。”
这时,孙思奇想起了刚才清醒之后仙翁对他说的话,然后道:“我听说神仙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仙翁道:“可以,你想问什么?”
孙问道:“您刚刚称呼我为“无眼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请指教。”
仙翁道:“所谓‘无眼’,就是没有眼睛的意思。在我们这里,众神都是有两只眼睛的,我们既可以用它观察世间万物的表象,也可以用它洞察世间万物的本质。”
听了仙翁的话,孙思奇站在那里愣了半天,脸上露出惊讶地神情,说道:“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眼睛’这个东西。我们村子里的人没有一个跟我说起过这件神奇的宝贝,听您这么说,我真的很好奇那是什么。”
仙翁道:“万事万物,各安天命。若有错位,定遭劫难。”
孙思奇不理解仙翁的话中之意,此刻他全部的心思都在那个被叫做“眼睛”的东西上。他想了想,然后壮起胆子,再次问仙翁道:“我真的很好奇那是什么,既然您说您是神仙,您能否施展法力,赐我一双眼睛?”
仙翁答道:“罢!罢!罢!既然如此,我便答应你这个请求,但你须知,日后倘若因此而招致什么灾祸,不可责怪于我。我赐你眼睛后,会送你下山,你从哪里来,就往哪里去。”
孙回答:“多谢仙翁,我已谨记于心了。”
随后,仙翁施展法力,将两只眼睛安在了孙思奇的头上。得到两只眼睛的孙思奇如获新生,就在他准备感谢仙翁的帮助时,只一转眼的功夫,他就被仙翁送到了来时山下的路上,他连仙翁的影子都没看到。
他找到了回村庄的路,一边走,一边用神赐给他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像一个刚初生的婴儿一般,好奇地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白天的时候,他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首先对太阳的形状感到惊奇,随后光束射到他的眼睛里,他只觉得刺眼,“那是一块会发光发热的石头吗?”他望着太阳喃喃自语道。夜晚的时候,他抬头仰望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同样感到惊奇:“怎么白天看到的又大又热的太阳,一到晚上就变成了冰冷的‘月亮’和无数颗小‘星星’了呢?它们真的如我所见那般一动不动并发着光吗?神赐给我的这双眼睛会不会骗我呢?”他一边观察,一边用手在地下做着标记,同时心里也堆积着越来越多的疑问。
等到第二天,他又继续赶路,不知不觉,他走到了一条小溪边,伸头往水里一看,突然“阿”了一声,惊倒在地,他看到水里有一个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人的模样,他虽然害怕,却禁不住好奇,又伸头看了看,最终,他确定了那水里的人可能是他自己。随后他仔细地观察了自己的外貌,于是他确定,自己有一头黑色的头发,一双黑色的眼睛,一身黄色的皮肤,两个奇怪形状的耳朵和一个从脸部凸出来的大鼻子。他记住了自己的样子,包括颜色和形状,他打算回去告诉同村的人,他们听到了该有多么新奇和开心啊!
他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就回到了村庄里。孙思奇看到了同村的人,除了没有眼睛以外,都长着和自己一样的脸孔和身体。于是他召集众村民,想要告诉他们,自己在这次旅途中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在他的召唤下,村长带着众村民都围过来倾听,想知道他究竟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于是他把在蓬莱山的遭遇,包括蓬莱仙翁赐给他双眼的经历,以及在回来的路上看到的一切,在水里看到的自己,以及现在看到的众人的样子等等,都一字不漏,全都说给村民听了。
没想到,村民听后,不仅没有孙思奇预想到的感激和喜悦,反而引起了村民一阵恐慌和骚乱。村长非常生气,当场喝到,快把这个妖言惑众的歹民抓起来。在村长的指示下,村民们把孙思奇五花大绑,捆得严严实实,押送进村后的牢房中,等待村规的惩罚。孙思奇在牢房中大声喊冤,说自己不过是多长了两只眼睛,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事实而已。他不过是把关于这个世界的另一面讲述出来给大家听而已,他不觉得自己有错,别人没有权力惩罚他。可不管他怎么喊,都没有村民愿意听他的话,更别说理解和支持他了。
两天后,村长在听取村民意见后,做出了最终的审判,判决如下:安乐村村民孙思奇,两日前从不知名的地方旅行归来后,召集村民,当着众村民的面,妖言惑众,散播谬误信息,引起村民恐慌,危害村中安危,教坏村中青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现仗罚五十棍后,逐出本村,永世不得回村。
从此,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方清以此评论道,这个故事讲述的不仅是主人公孙思奇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