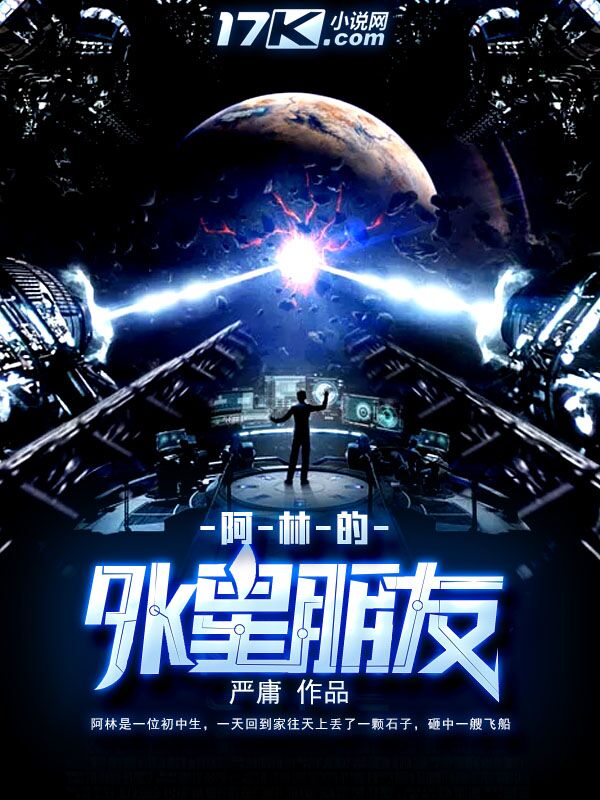启程去往杜兰戈的前一天,没想到会跟安先生发生争执,导火线还是因为他在我一个很久没用过的相机包的夹层里发现了我以前没抽完剩下一半的烟盒。
安先生那时候脸色铁青,气压低得仿佛身边的空气自己形成了一个大气压层,马上就有降温降雨的预兆。
“解释一下!”
客厅里,安先生和我各占了一边,他站在台阶下,背靠着墙壁斜对着我。我盘坐在沙发里,不面对他,面对着对面的墙壁和水彩画。
“何曦。”安先生的声音又低了几分贝,“我现在不是质问你,是想让你跟我解释一下。”
我挪了挪位置,将脸面对着他,但我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我抽烟有很长时间了,起初没有烟瘾,偶尔只在烦躁的时候抽一根,后来有了一点烟瘾,一抽两三根,但是不能让自己身上带着烟味,也不会经常抽,在烟瘾最大的那段时间,我也都很好的控制在一周只允许自己抽一包的量。在国外,日本烟,美国烟,韩国烟,习惯的几个牌子我都抽过不少,这一包上海红双喜,时间太长了,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买的,没印象了。
但是这包烟,我确实抽过了,这一点我无话可说。
我说:“是我的,也是我抽的,但是这是我戒烟之前了,你看我都忘了这个旧包里还藏着一包烟,要是我记得,你就不会看到了。”
安先生是要有点生气的,但是他已经急的生不起气来了,问我:“何曦,为什么要抽烟呢?你抽多长时间了?工作的时候,你也会碰这种东西吗?”
我说:“我已经不抽了,去年就已经戒了,真的。”
“去年就戒了,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刚见面那次你还在抽。”安先生绷紧了腮帮,记得清清楚楚,“你还是当着我的面。”
我暗暗地咬了咬舌,简直欲哭不得。心想那时候自己在发什么疯,非得在他面前表现得冷静和无所谓,要表现用什么表示不好,掉头就走都好过现在秋后算账。不过那时候我在展馆里看到他,惊喜,激动,紧张,怨恨,难过,一时间各种情绪都杂糅在了一起,我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怕他看出来,也怕自己奔溃,摸到兜里正好有烟,就控制不住了,忘掉自己已经戒掉了。
安先生见我不说话,他低下头,揉了揉眉心,“差点又被你带偏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为什么要抽烟,我不记得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到英国不久,我刚换了学校,租的房子离学校很远,我每天要很早起来赶最早的那趟巴士去学校上课。也是可以住宿的,但是那个时候妈妈她心情一直都很不好,她有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记得吃饭,有时候她去广场上喂流浪猫,一呆就是一整天,我不放心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我看着地板,那里映着我的影子。
“有一天上早课的时候我又迟到了,是那个月第三次迟到,这次教授不管怎样一定会扣我的学分的。我突然不想去上课了,我跑到一座荒废的教学楼,我看到一个女孩坐在楼梯口抽烟,这个人我不认识。我问她抽烟是什么样的感觉,她说,可以让她忘记烦恼的感觉,然后我就抽了。你说抽了多久,从那个时候到去年,一直断断续续在抽。工作的时候也会碰吗?会,它并没有给我带来痛快感,只有起初的新鲜感和刺激。也没有刺激我的灵感,只是看着烟蒂燃到尽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注入在那些作品当中的灵魂,这些本体赋予给影像的灵魂,它们死了,然后又重获新生。像“无垠之路”,我拍下来的,记录下来的东西,不是因为抽了那几口烟,而是每一个脚印都是我亲自走过来的,我感受到的它们带给我的尽头与重生。”
安先生早就走到我身边,他明白我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发现我抽烟的时候就跟母亲发现了真相的时候一样,不是质疑和责怪,而是担心和不解,但是他们问我的时候,我也解释不清楚。就像做了什么坏事一样,你做坏事的时候会给自己找什么借口吗,当然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个理由的,但是当你习惯之后,你还能找到什么理由吗。
安先生跟我说:“你以前的时候看到班里的男同学抽烟就跟我说,抽烟不代表是坏孩子,不抽烟也不代表是好孩子,但是你说过你自己绝对不会碰这个的。何曦说过她最讨厌外公抽完烟后就咳嗽,你还记得吗?所以我很惊讶。”
安先生握了握我的手,“阿姨知道吗?”
“比你先知道。”要不是知道,也不会在我住院之后,强制我再不许碰烟与酒这两样东西。
安先生说:“你看,不止阿姨担心你,你让我也吓了一跳。”
安先生就蹲在我面前,他把脸放在我的掌心,吻了吻我的食指,抬头看我:“艺术家虽然表面上个个看起来富有无穷的创造力,但是实际上的付出却并不比常人少,好像摄影家,一面追求美学上的至上至美,一面又想要干净纯粹的灵魂,往往很容易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徒劳无功。当思维陷入困顿的时候,人会追求刺激和灵感,我静不下心来去画设计图的时候,喜欢玩摇滚和喝酒,何曦,你还有什么古怪的癖好吗?你会喝酒吗?”
我脸颊一热,淡哂,知曦若曦者,安之谓也,这人也太聪明。
我说:“也会喝酒,喝酒会更厉害一些。”
安先生有疑问:“上次我们烧烤的时候,我不记得你喝酒了?”
我抿了抿嘴,说:“我妈不准,我喝酒得经过她同意。”
我在心底想,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偷偷喝酒了也就喝了,但是安先生在场呢,我母亲万一哪天旁强侧击地向他问起,我就露馅了。
这边安先生也从我的回答中嗅出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问我:“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吗?”
无奈,从实招来。我将去年那次半夜喝酒喝到胃出血的经历也告诉了他,但其实那次真不是过量饮酒,也不是故意醉酒,而是好些天没有按时吃饭,当天胃口不好,也没吃什么东西垫着肚子,一下多饮了几杯,胃有点经受不住刺激。
不过那次受的教训也大,从出院到现在,即使母亲一直都在饮食上刻意花心思帮我调养,但也因为诸多原因,一直到现在我的胃也没调养好。不喝酒不完全是戒酒的原因,而是如果喝酒没注意的话就会胃疼。
也说了这几年来自我放逐,因为刺激而做过的疯狂的事,比如徒步荒野,在北极圈追光,去绝峭攀岩。在追求梦想和艺术的路上,跪在现实和信仰的路口,丢失,迷路,然后又重新找到了新的路。早一步,在又遇到他之前,把这条寻了回来,走了正确的方向。
一直觉得这个契机恰好,没有让那个放纵过,牺牲健康,迷途不返的何曦碰到曾经干净包容她的安嘉树,而依旧是以前的何曦,不会对生活失望,不会逃避现实,不会流放自己,不会离她爱的人越来越远。又觉得对我们来说也会有一些遗憾,因为在最困顿难过的那段时间,不能向他求救,在最孤单和辛苦的独行中,没有在他身边支持陪伴。
世人皆说,感情是经不起太多考验的,好像最终拥有圆满结局的,也大部分不是共担过风雨,而是因为向往岁月的安稳。也有人说只有经历过考验的感情,才富有长久的生命力,在穷途末路为爱人,也为自己指明方向。
我不想去做如果我和安先生这些年不曾分开,当我们共同接受过这些考验之后会我们会变得怎样的假设,自由和独立才是我们,报团取暖或相互治愈只是一部分我们。完整的我们应该是不管在不在对方身边,不管在哪里,生命有一部分始终与他相连,不是为爱献祭,而是因爱新生。
茶几上的几支玫瑰刚洒过水,粉红娇艳的花瓣,翠绿欲滴的叶子,铺盖一层晶莹剔透的水珠,如少女刚淋浴过曼妙新鲜的胴体。蓝色的沙发往上,白色的墙壁上挂着的水彩画是灰蓝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麦田,风从阳台上吹过来的时候,麦田变成了麦浪翻涌。在安先生完全遮住这些视物的时候,有人开门进来了,我们的对话也被打断。
林东在门廊处准备换鞋子,一边打开鞋柜,一边往里看了看在客厅的我们。
“我回来拿几本书。”他把鞋子脱下,换身拖鞋进来,“没打扰到你们吧?你们......是在商量什么事吗?怎么看上去有点严肃?”
安先生手臂环抱在胸前,他原先靠坐在茶几上的,现在站了起来,看向他:“恩,是在说一些事情。”
“那你们继续。”林东对我们笑了一下,手一扬,飞快地爬上楼梯。
“我要去拿我的相机。”我蹭的从沙发上坐起,动作幅度太大又太快,把安先生都吓了一跳。
他看着我飞快地跑去二楼,冲到楼梯口,朝上喊:“何曦,你做什么?”
我快速地回了下头:“你别动,你就呆在那。”
两分钟后,我风风火火地下楼,一边打开我的相机镜头,一边走回客厅。安先生紧紧跟在我的后面,见我走到沙发跟前跪伏下来,将摄像机轻轻地往茶几上一隔,然后眼睛凑近取景器时,安先生脚下一顿,抬手将手背往额头上一搭,深呼一口气。
“何曦,你这突然的吓人。”他慢慢走近了,嘀咕一句,“我还以为你要做什么。”
我半跪在地上,调整了一下姿势,设置好焦距和光圈,调整满意的角度。
我指了指了茶几左边的位置,对安先生说:“你过去那,帮我拿着那个画框。”我又指了指挂在墙壁上的那个木架子。
林东从二楼下来的时候,我正好准备按快门,对安先生说:“你手再往右一点点,稳住,保持。”
林东一只手抱着书,另一只手臂撑在扶梯上,见到我们忙得乐此不疲,禁不住笑出声。
“何曦,你可太有本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嘉树被人这样指使,还一句意见都没有的。”
我看了一眼安先生,他也正看着我。
“是嘛?”我说,“他以前也经常这样被我使唤来使唤去,应该是习惯了。”
林东听完,手放在肚子上,夸张地哈哈大笑。
“何曦,你真是太可爱了。捡到宝了,捡到宝了,你们两个都是宝。”他边说,边笑着走下来。
我朝安先生摊摊手,他这是从哪觉得我可爱的?
“我要先走了哦,有时间再见。”林东刚走到门廊,又折回几步,“哦,对了何曦,你是明天下午的飞机,就走了吗?”
我朝他说:“是啊。”
“那晚上叫上大家一起吃个饭,然后一起去看个电影呀。”
我先朝安先生看了一眼,还没说什么,林东就跟我说:“懂了懂了,还是不打扰你们过二人世界了。”
“嗯......可以呀。”
“我和何曦就不去了,想在家里待一待。”
我和安先生同时说出口,不过他比我先说完。林东左看了看他,右看了看我,瞧着瞧着又笑了,说:“那不送了哦,一路顺风。”
等林东走了之后,我问安先生:“你不想出去跟他们聚一聚吗?”
安先生看着我说:“我是不希望你感到不自在,毕竟你跟他们不熟,不需要因为我去应付那些。”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去的?”
他微微地挑了挑眉:“你真的想去?”
我摇头,“但我总是要了解你的社交圈子的,你认识什么样的人,平时喜欢什么东西,即使我跟他们都不熟,或者不懂,但是如果我觉得不舒服,那我也可以选择下次就不去了。你也一样啊,你可以了解我圈子里的人,参加我的社交活动,如果有些你不喜欢,你也可以提出来,可能我们都不喜欢呢。”
我说:“嘉树,你不需要因为迁就我而不去跟朋友见面,参加活动,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觉得无聊,我还可以陪你一起。”
安先生说:“我觉得不好,你不觉得我们相处的时间都很少了吗?你跟我在一起难道会觉得无聊吗?”
我无语望天,他这厮又在装作听不懂了。
“何曦,你不能多把一点时间分给我吗?”安先生叹了口气。
我说:“我现在不就是在尽可能多陪你吗?”
安先生看了看我手里的相机,说:“那它霸占你的时间怎么比我还多?”
我回答说:“其他的时间是你的。”
安先生勉强觉得这个答案还算满意,又说,我不是你的吗?
我还没有答,他又问:“何曦,阿姨刚开始去英国那会精神状态就一直很差吗?”
我跺了跺脚,觉得他欺负老实人,对他说:“你这话题转得也太跳跃了,我刚还自我感动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