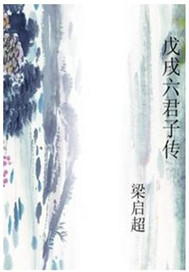停灵三日,便有祭拜三日的风俗,第二日,我们依旧是晌午时分到的。因为诚庆伯府并不连着亲,像文婧这样的未嫁娘子便是不需要参加丧仪的,所以丧仪现场也不拘男女,只宴席时分坐两处。
院子里,我拉着墨誉落后两步,担忧道,“你今儿个就跟我们去小室里坐一会儿吧,免得像昨日一样被伯府二房哥儿缠着。”
他俊美面容乐滋滋一喜,莫名冲我狡黠眨眼,“昨日被缠的紧,岳父大人找我说话也没来得及,今日他要同我说正经事情呢,再说,问过了午膳,还是要去军里的。”
我娇俏红颜睨他一眼,“傻乐什么呢”又恍然明白什么,不觉顿住脚步,紧张地看向他,铁定是为着容瑶的事情了。
他打断我的话,温柔指尖安抚地滑过我的背脊,“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这厢正说着话,那厢不知哪儿传出了沸反盈天的争吵声。我和墨誉四目相视,闻声寻了过去,不成想,这争吵竟是从灵堂屋子里传出来的。
我真是哭笑不得,都什么时候了,又不知出什么幺蛾子了。
我俩正步匆匆迈过去,正瞅着一位年长带络腮胡子的大叔揪着一位看似斯文彬彬青年的衣领,气势汹汹地龇牙,“你还有脸回来,怎么不等父亲入殓了你再出来,你个不孝子。”
“这是伯府三房老爷和大房长孙,也就是世子。”墨誉向我解释着。
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位三房老爷要给世子冠以这么大的罪名,还记得昨日母亲问起世子的行踪呢,连自己祖父逝世都迟迟未来送丧,果真是不孝,这世子的品行可见一般。
可绕是如此,世子也不甘示弱,一把反拧住那位大叔的手腕,两人拔河似的较着劲,一个趔趄,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世子仍旧东倒西歪踹着腿,嘴上骂骂咧咧,“三叔父既然这么好口才,怎么不说说自己是怎么气死祖父的呢。”
闻罢,我们面面相觑,不觉各个倒吸一口凉气,这,这,这信息量太大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个劲儿地往我身上泼脏水,还不是惦记着我头顶爵位的承袭,我告诉你,你没门,就是没有我,还有二叔排在前头等着点卯呢。”世子骂的尤不解气,好一副黑面嘴脸。
“我呸,爵位这头衔,就你也配,整日里不是花街就是柳巷。”三房夫人横冲直撞地奔过来,几乎指着世子鼻尖恨恨辱骂。
“就是,我说堂兄,你也不看看你为这个家到底做过什么?”一位估摸着十七八岁的男子,貌似要去扶世子起身,可眼底却渗出冷似寒冰的精芒。
“那又如何,我才是世子,是祖父亲自请封的,就是皇上也会替我作证,我承袭爵位那是天经地义,三叔父,你注定要矮侄子一头了。”世子迅速打掉那位堂弟伸过来的收,拍拍身上的尘土,傲然地高抬下巴,不可一世。
这话说的不可谓不重了,就是站在世子身边的一位装扮清淡节俭的女子也是忍不住眉目半耸,下意识地扯住世子的衣袖,“别说了,世子别说了。”
可世子正在气头上,哪里听的进去,不管不顾地推开那女子,瞬间与冲上来的三房表弟扭打在了一起,就是那三房夫人还是围着世子不停地恶语相向。
众人实在看不过眼了,两头纷纷上前拽住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温言软语地劝和起来。
“就是啊,一家人说什么重话呢。”人群中一位浓眉宽鼻大叔姗姗而来,男子披麻戴孝,双目红肿,哭的几乎眯成了一条线,还是步履蹒跚,语重心长地上前来安抚两人。
“这是二房老爷吧。”我凑近墨誉细问。
墨誉嗤笑地点了点头,正要说什么。突然,一声声高亢的咒骂好似平地一声雷,顿时淹没了众人的劝慰声。
“你现在来装什么老好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伎俩,就爱在人前扮贤德,父亲居然将祖上的那百亩良田赠给了你女儿做嫁妆,还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三房老爷气的面色青一阵白一阵,颧骨瞪得几乎变形。
“哼,还不止如此呢。”世子也围了过来,瓮声瓮气地嘲讽着,“叔父算盘打的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待我和三叔父互相攻讦,你在背后渔翁得利,这一招,厉害的很呢。”
“怎么会呢,你们误会了。”二房夫人也是菩萨面容,连连尴尬地摆手。
“哈哈。”世子不管不顾,睥睨着三房老爷,哈哈大笑,“三叔父可知道为何祖父对你动辄横眉竖眼,这可都是二叔父背后搞的鬼呢。”
“什么意思?”三房老爷吹胡子瞪眼,惊诧地跳了起来。
世子听了,兴致勃勃还待说话,身旁女子小心翼翼地拉住他的边幅,惶恐地直摇头,“别说了吧,这么多人瞧着呢。”
世子此时已是吵红了眼,哪里肯听,眉峰抖立,颇不耐烦地哼了哼,一个巴掌扇过去,那女子便哼哼唧唧被打倒在地。
我不可思议地倒退了一步,全身激起一层鸡皮疙瘩,抬腿就要上前,又顿住了。墨誉下意识地搂紧了我,“没事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只闻得世子“啊”地大声惨叫了起来。我狐惑回头,居然看到哥哥抡着拳头,一块铮铮铁板似的,恶狠狠立在世子跟前,那双黑瞳好像灼烧的烈火,愤怒喷薄而出。我再看向世子,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面颊一块印记通红通红,这哥哥下手真够厉害的。
可是,不对啊,哥哥,哥哥为什么要突然动手打世子呢,就因为世子打了个女人,我,我,我当即楞在了那里,完全动弹不得,哥哥莫不是疯了,就算抱打不平,也要看场合,看方式啊。
此时此刻,围观的人群渐渐沉了下来,窸窸窣窣,指指点点,络绎不绝。
“容瑾,你做什么呢!”母亲尖声呵斥,匆匆忙忙从人群中挤了进来,将哥哥拉到自己身旁。
我这才幡然醒神,哆哆嗦嗦地扫向人群,那一双双暧昧眼神,无一不是看好戏的前奏。的确,哥哥大庭广众之下为一个素不相识女子与世子大动干戈,这恐怕脱不开关系了,让人不瞎想都难。
说是迟那时快,墨誉安抚地摁了摁我的手背,一个箭步跨了上去,义正言辞,“世子大人有话好好说就是,何必对着自己的女人动辄打骂呢。”说罢,又大大咧咧地拍了拍哥哥的肩膀,道,“容瑾啊,就算看不过眼,也不可以贸然动手啊,我知道你常年在军中,对对错错看的太重了,可这里毕竟不是军营不是。”
四两拨千斤。墨誉三言两语一下子扭转了舆论,将哥哥的行动简单地归结为看不过眼。
“啊呀呀。”话音刚落,赵夫人磕磕绊绊地冲了出来,百般怜惜地抚着世子的面颊,对着哥哥嚎丧起来,“我说叶公子,我儿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对我儿下如此重的毒手?”说着,厌恶地睨了一眼蜷缩在角落的女子,理直气壮道,“这女子本就是世子的妾室,世子管教妾室也需要叶公子操心吗,真是不得不让人怀疑叶公子的用心啊。”
说着,灰败面容阴恻恻地盯着哥哥,犹如鬼魅。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扶额不语,这,这要怎么解释的清呢!再看身旁的母亲,胸膛剧烈起伏,颤抖的指尖几乎将手中团扇掰断,几近昏死过去。
“这位夫人还请慎言……我不过是看不过男子殴打女子的言行罢了,何至于此不堪入耳。”哥哥一夫当关,昂首而立。
“你这话谁知道呢。”赵夫人勾唇讥笑,大言不惭,“我儿这妾室本就是从前安王大婚时,自己偷偷摸摸爬进我儿的客房,谁知道她这是不是第一次呢。”
我顿时目瞪口呆,这话她也说得出口。我原先在入宫拜年时,与她说过话,还以为这位赵夫人还算矜持,如今看来,真是大错特错了。
在场诸人,不是达官就是显贵,且里里外外站了不下百人,如今哥哥就犹如置身于碳火中,周遭意味不明的目光就是那熊熊烈火,流言猛于虎,任何辩驳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
“赵夫人,我敬你比我长上几岁,可也不能信口雌黄,生生毁我儿名誉啊。我儿向来是至诚至孝之人,维护亲中长辈理所应当,有什么可置喙的呢!”母亲突然地大义凛然站了出来,眉梢带煞,双目湛湛有神地盯着赵夫人。
赵夫人眸光一噎,冷冷笑道,“亲中长辈?什么亲,叶夫人可别说笑话了。
母亲盈盈勾唇,说不出的气韵悠闲,“这位史小姐是府上世子的妾室,可也是我们容瑾的姨娘。”
“什么?”赵夫人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不止她,就是我也是神情呆滞,惊的有如石化,容瑾的姨娘,这年纪,编的也有些不妥当吧,母亲到底是怎么想的。
“叶夫人真的为了掩盖自己儿子的罪行,什么瞎话都敢编啊。”世子自然也不信,吊儿郎当地揉着面颊质问。
当场窃窃私语渐起,三人成虎,母亲大概是打着这主意。可偏偏母亲樱唇含笑安详,面似秋水宁静,不紧不慢地低笑出声,“世子错了,这位史姑娘正是我那同父异母姐妹的妹妹。”
世子和赵夫人见母亲情真意切,有一刻退缩,又瞧着众人,不免壮了胆子,犹自嘴硬。
这时,安平侯府的陈夫人站了出来,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这事儿有些年纪轻的或许没听说,我却是知道的,你那姐姐本是你娘家父亲外头的私生女,但与你却是私交甚笃,后来还跟你一道入了叶府为妾,只是命薄,早早去世了。”
“陈夫人说的是。”母亲握着陈夫人的手,眼角含雾,有些哽咽,“说起我这妹妹,我真是伤心。十八年前,因为我患有严重的咳疾,身子实在弱,为了叶府香火,我便将我那妹妹聘为良妾,只是可惜,一年后她因为难产去世了。要知道这个妹妹与我是顶顶要好的,她虽是外室所出,但得了我母亲允诺,经常入府来请安,与我也谈的来。后来父亲去世,妹妹的生身母亲也改嫁了,聘为一户姓史官家的小妾,这位史姑娘便是她生身母亲后来生养的女儿,只是不幸,这位官家也去世的早,孤儿寡母的,官家主母底下哪有好日子过。我那妹妹虽已入了叶府,但也常常接济,我都是知道的,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带着这位年岁尚小的史姑娘到我府上耍过。不知史姑娘可还有印象?”
那位史姑娘颤颤巍巍地扶着方几,见母亲温和地望过去,惨白面色终于现出一丝灵动,“好像有些印象,只记不大得了”。
母亲慈眉善目得叹了一口气将那史姑娘拉到跟前,宽慰着,“你那时不过两岁,不记得也属正常。”
“这么说,论理这位史姑娘的确算的上是璟哥儿的姨娘,的确是长辈。”陈夫人思忖着,神情严肃,也是频频点头。
在场好几个妇人都是纷纷附和。
“这事儿可不就是这么着的,我桩桩件件都是知道的,有谁若是不信,尽可以打听去的。何必用这不存在的腌臜事,冤枉了这样一个好孩子呢,”大伯母苦口婆心地掖了掖眼角,看着很是伤怀。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许是被大伯母影响的,我也激动欣喜地看向哥哥,总算他不会再为难了。可却瞧见哥哥长身玉立的背脊瞬间佝偻下来,盯着那史姑娘,满目的郁郁寡欢,自言自语着,最后默默低下了头。我不禁奇怪,哥哥怎么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人会再相信世子和赵夫人的片面之词了,何况世子府上还是这么个光景,旁人怎么相信呢。
墨誉和哥哥用过了午膳还是要去军里的,我趁着送墨誉出门,门廊口拉住了哥哥,眼见着没人,直言问他:“哥哥今日为何这样莽撞?人家到底是伯府世子。”
“这……”哥哥面色泛红,囫囵吞枣地回了一句:“你不觉得那女子甚是可怜吗?”
我脑中现出那女子匍匐在地时楚楚悲鸣的模样,也是暗叹一口气,同为女子,她的命运是要悲惨许多,我不是不同情,只是纲理伦常有时真是让你寸步难行。
“可是,人家到底是世子的妾室。”我思忖着,板起脸郑重告诫他,“无论你如何同情她,这事上你莫要再沾染,否则于你于她都是祸事,你不仅帮不了她,还会害了她。”
“可是,可是,母亲不是说那是姨娘么,我看她似乎过的很不好,我们不应该帮帮她吗?”听了我的话,哥哥莫名激动地涨红了脸,满口胡言乱语。
我着实诧异,犀利地上下打量起哥哥,“我觉得你甚是奇怪呢,你又怎么知道她过的很不好了。”
他不语,却是垂头丧气。
墨誉站出来拍了拍哥哥的肩膀,附和道:“既然如今大家都知道这位姑娘与我们沾着亲,想必以后伯府不会亏待她的,你这是关心则乱。”
“什么关心则乱?”我气闷,眉梢一横,瞪向他,哥哥和她是什么关系,谈得上关心则乱吗?
墨誉只好憋屈地缩回了头。
“既然是姨娘,我和母亲都会和伯府打招呼,多多照应这位姑娘的,你无谓操心。”
哥哥被我说的,灰溜溜地走了。
我连忙拉住了墨誉,努努嘴:“你帮我看着他点儿,问问他怎么回事儿。”
墨誉冲我嬉皮笑脸地应了。
说实在的,我倒现在犹自不相信,那清素丽色姑娘竟与我们沾亲带故,还记的,上次安王大婚,回府时,大伯母倒是说起过这位姑娘,叫做,母亲却是一副不愿深谈的态度。更稀奇的是,母亲从前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竟然是府上的良妾,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个人的存在,母亲和府中诸人竟是完全不曾提起,真是奇了怪了。回头,我又就这位姨娘的事情问了母亲,母亲面色骤冷,斜眼看我,“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好聊的。”我吐了吐舌头,也就没再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