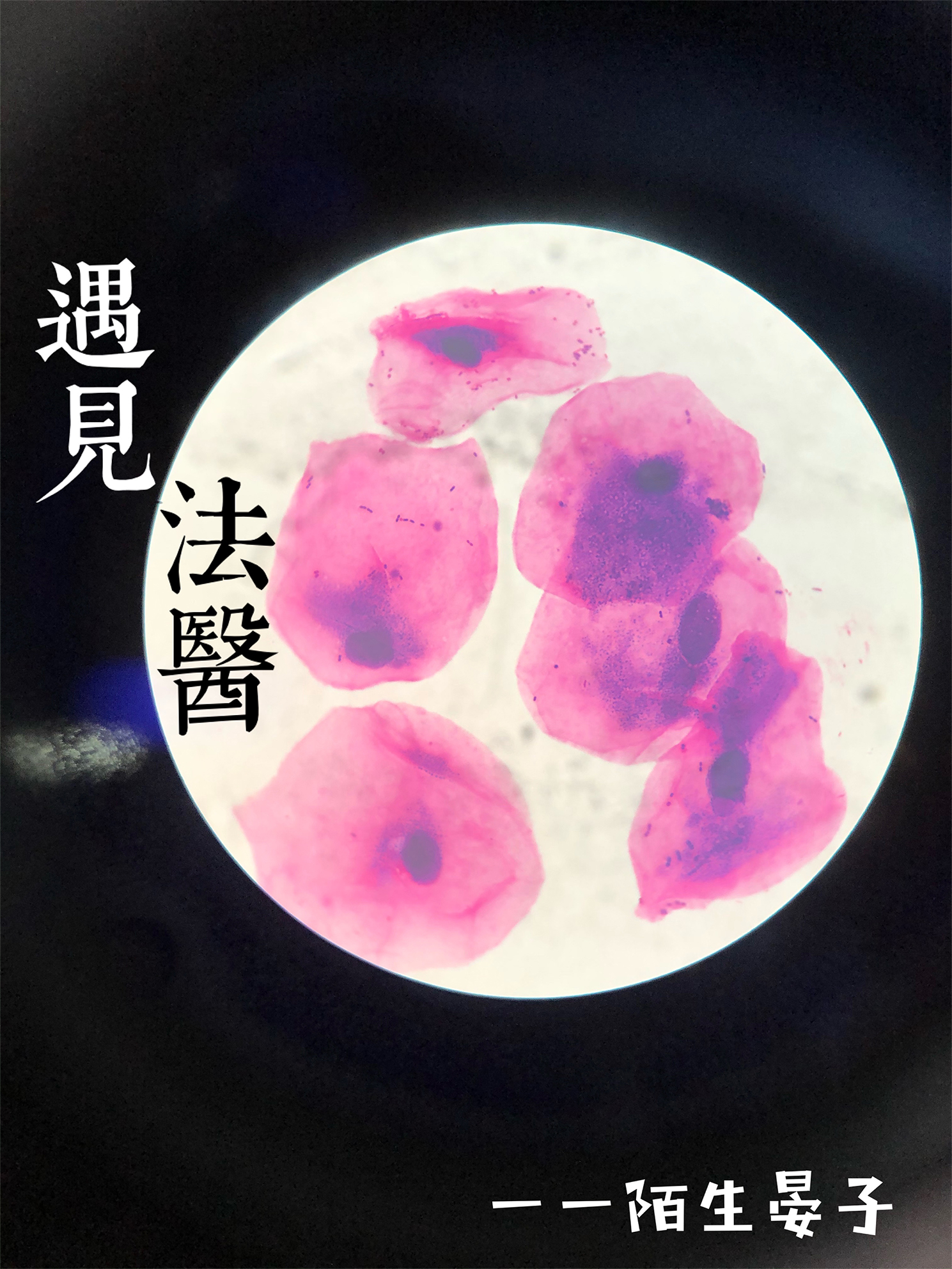莫离的律师事务所坐落在沧滨市天堂中心地带、滨江区胜利大街19号的宏达大厦。大厦有二十七层,律师事务所占据了十七层东侧半个楼层。西侧是还未开业的商铺,被装饰面板牢牢包围着,看不出半点端倪。
早上十点五十五分,林非走进事务所前厅,年轻漂亮的前台小姐抬起头,脸上挂着程序化的职业微笑。
“你好,我是林非,和莫律师约好的十一点。”
“您好!林小姐,莫律师在隔壁,我马上请她回来。您先请坐。”前台小姐边起身,边伸手邀请林非在墙角的沙发落座。
正对着沙发的墙上挂着幅半人高的油画。蓝色夜幕下,马戏团的篝火点燃人们的睡眠。空中飞人在一条钢索上旋转宛如时钟。狮子跳着火圈,小狗像是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绕着圈旋转奔跑。十几个的小丑在表演场边缘一字排开,同一张脸,同一个动作,咧着红色大嘴欢笑。
初初看去,恍然觉得画中一切都那么正常。
然而,林非稍稍倾斜身体,蓝色天幕中隐隐的那双眼,瞪得她背脊发硬。旋转的空中飞人不同寻常的脖颈长度,好似已经被绳索勒毙。在他对侧,另一条钢索断成两截,另一位空中飞人悬落半空,仿佛下一秒就要砰然落地摔成肉泥。成排的小丑笑意狰狞,手中并不是常见的彩球而是尖锐利器。利器的顶端不知是被篝火或是鲜血染成血红。还有观众席上沉睡人群,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或面目模糊或五官迸散,影影绰绰,好似鬼魅。
画家的名字用血红的颜料斜斜签在画布的右下角。
杨奇。
杨奇?这个名字像钢针扎入林非的眼睛,让她浑身一颤。是不是徐默和吴云熟识的那个杨奇?
“林小姐,请喝水。”前台小姐送上一杯柠檬水。她话音未落,事务所大门被推开,一男一女边低声交谈,边走进来。“等过两天,其余的画运过来,你再过来选选。”男人彬彬有礼地说。
“莫律师,杨先生。”前台小姐赶忙招呼。
莫离微笑着对林非点点头。棕黑色齐肩大波浪卷发,精致的俏眉亮眼红唇,修身的裙装,将她一米七左右的玲珑身段衬托的干练大方又成熟妩媚。
莫离身边的杨先生四十多岁,肤色浅黑,却有着满头花白的头发,格外刺眼。棱角分明的鼻梁上方,挂着浅浅的微笑,精明有神的眼睛正和林非相互打量。一道长长的伤疤横过左脸,从太阳穴一直划到唇边,让人触目惊心,也为他带着笑意的眉眼添了几分凌厉。超过一米七五的躯体强壮有力,毫无赘肉的上身穿着做工精良的浅灰色衬衣,脖间系上本季最流行的斜纹领带,黑色休闲西裤下的英式皮鞋一尘不染。细长的手从袖口探出来,十根指甲都被精心修剪成漂亮的椭圆形。他脚步笃定地走过来,热情地将一张名片递到林非手中。“我叫杨奇,是隔壁咖啡馆的经理。我们本周日开业,敬请光临。”
杨奇!
他就是杨奇!
杨奇依然微笑着,几不可察地点点头,视线一动未动与林非对视。那双眼所传达出来的心情,说明了一切。
他认识她。
有意?或是无意?渐渐苏醒的梦,好似原地打转的线轴,宛如洞穴中的影子,不管多久,最终,被迫直面。
两分钟后,林非又见到了那位正义女神。不是在纸上,而是在莫离的办公桌上。
莫离的办公室很大,空荡荡的。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天花板,深褐色的地毯,显得高雅沉稳。墙上没有任何装饰。房间一角放着三个带锁的灰色铁制文件柜,正对着浅灰色的皮质双人沙发。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打火机、烟灰缸和香烟盒。窗前就是大大的办公桌,台灯、台历、简单的文具,没有相框,没有照片,多余之物一概没有。只有那位正义女神。
“林小姐,请坐。”莫离边准备文件边说,见林非一直打量塑像,又说,“这是我考到律师证的礼物。”
“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林非背出这句原本刻在塑像背后的拉丁文。
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请叫我林非。”
“好,只要你不再叫我莫律师。叫我莫离。”
两人相视一笑,笑容化解了彼此的陌生感。
快速浏览过文件,林非惊讶地差点合不拢嘴。文件的内容并非关于婚前财产公证,而是徐默要将名下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无偿转让给她。这几年房价飞涨,这套在省城的公寓,保守估计价值都已经超过百万。“我不能签。”林非阖上文件,又设法心平气和地解释,“徐默没有和我沟通过这件事,我不能签。”
莫离认真思考后才开口说:“也许,这是徐先生给你的惊喜,或者说,是礼物。”
礼物?林非看看文件上不动产的总值,深吸一口气。“上百万的大礼,我受不起。说实话,也许我一辈子也挣不到那么多钱。”
莫离用怀疑的眼神又看了看林非:“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财产,对吗?”
望着面前数本红色封面的房屋产权所有证,林非目瞪口呆。每本房产证上的产权所有人都是她。最早那处房产的购买时间,居然是林非和徐默在酒吧重逢的一周后。那时,她正在为罗科犯下的连环杀人案焦头烂额。更让林非惊讶的是,凌胜街77号居然也在自己名下。
莫离看着她,她看着莫离。停顿了好些时间,林非猛地将椅背往后一顶。“不好意思,我想先打个电话。”莫离谅解的点点头,起身走到窗前,盯着远处的云。
徐默的电话无法接通。林非算算时间,也许他正在回程的路上。
林非突然笑了笑。“徐默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守口如瓶。”
莫离也笑了。“不做警察,徐先生也能做个好律师。”
将面前的房产证往莫离方向推了推,林非无奈地说:“如果在夫妻的立场上看,这也是他最大的缺点。”
莫离将房产证收回文件柜。背对着林非,她说:“我很喜欢的作家写过个故事。男主角说,如果他真正爱上一个人,他马上立一张平安纸。”
“平安纸就是遗嘱。”莫离接着解释,“交代了身后事,害怕毫无预兆的走了以后,不能再保障那个人的生活。”
林非没有说话。
“而徐先生的这种方式,对于你的保障比平安纸更稳妥。”
无关生死,不管离合。
垂下头,林非掩住全部的情绪。手指拂过文件上那个名字,黑色的墨迹透过皮肤,印进肌肉骨骼,刻下最深的烙印。最终她抬起头,坚定地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签。”
看一眼依然空白的转让文件,莫离淡淡地感慨一句,“多少夫妻兄弟为了微薄的财产互不相让,你们俩却有人送也不肯要……”她笑着摇摇头。
你们俩。
除了林非,还有一个人不肯接受别人的财产馈赠。
而且,这个人,林非认识。
林非表情复杂地盯着莫离。莫离像是知道自己说漏了嘴,面露尴尬地岔开话题,“如果你今天还有一个小时能给我,我有件私事,想要拜托你。”
淡蓝色的天空下,大厦旁的街心公园里,两个女人沿着静谧的小径缓缓踱步。高大的银杏树隐隐显出秋日来临后的绚烂,为整条小径投下树荫。往前走了段路,莫离在木椅上坐下,林非也坐到另一侧。一座飞机轰鸣着飞过,在高高的蓝色画布上划出道弧形的白线。两人默默望着飞机消失的方向,秋日午后金黄色光束中漂浮着梦幻般跳动的飞沫,投下肩并肩的背影。
莫离掏出个精致银色烟盒问:“你抽烟吗?”
“我不介意,你抽吧。”林非摇摇头。看着莫离莫离拿出打火机,点燃香烟,她又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有些人只看到烟。”
莫离深深吸口烟,幽幽开口:“还有些人能看见火,却装作看到的是烟。”
说完,两人又相视一笑。
盯着远方一朵像鲸鱼的云,莫离忽然问:“你和他认识多久了?”
“五六年。”林非直接回答,并没有反问“他”是谁,“我认识阿瑞这么久,我觉得,他是个不会爱的人。”
莫离惊愕。
树影恰到好处的映在林非眼底,她继续说:“人心在他看来,是最善变的东西。他不敢爱,所以也不会爱。”
“你错了。他亲口告诉过我,他爱一个人。”莫离反驳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嘲弄,还有不甘。
“是谁?”
“是……”莫离眺望着黄绿相间的树丛,“是个很好的女人,她嫁给了我哥哥。”
“那你介意的是什么?”
“我介意什么?”莫离反问。
“你介意的是,他爱着一个女人?”
“他爱着一个很好的女人?”
“还是,他爱着嫁给你哥哥的女人?”
莫离用了十秒才理解林非话中的含义。她将吸了一半的烟碾灭在随身的小金属烟灰缸里,又刻意瞥了林非一眼。“我们为什么要在如此美丽的秋日午后,说这个讨厌的人?”
“我以为这是你想说的私事。”林非的语气里透着笑意。
莫离深吸了一口气,像是鼓起勇气,直接了当地请求:“不是。我是想请你,帮我查些警方档案。”
“你想查什么?”
“一桩半年前的自杀案。”
“谁?”
“杨小丽。我的高中同学。”
“你为什么怀疑她不是自杀?”
莫离一怔。
“沧滨市有个规矩,所有的自杀案都要由市局的法医中心派人现场勘察。他杀能伪装成自杀,逃脱法网的几率很小。”话虽如此,林非依然掏出记事本,记下了杨小丽的名字。
“我不是怀疑你们的专业水准。”莫离小心翼翼地看看林非,唯恐自己的话惹她不快,“但我遇到了件奇怪的事。”
“一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杨小丽寄来的信。信上说,她打算来看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务必见见她。”莫离边说,边从风衣口袋中掏出一叠纸,“然而,信的落款日期是半年前。她写下信的第二天,就自杀了。但那份信寄出和收到的邮戳日期都是一月前。”
“寄信的人是谁?”林非立刻追问。
“我不知道。信封里,只有杨小丽的信。这是信封和信的复印件。”莫离将那叠纸递给林非。
谨慎,莫离的性格里有着不寻常的谨慎。但林非觉得,这种谨慎,并不是阿瑞和徐默能如此信任她的全部原因。
盯着复印件,林非又问:“你怎么能确认,这封信就是杨小丽本人写的?”
“在高中时,我和杨小丽虽然不同班,但都是文学社的社员,关系不错。”莫离侧过身,手指划过复印件上的一行小字,“在这份信里,她叫我美少女侦探莫小妹。这是我们在文学社相互开玩笑叫的花名,知道的人并不多。”
“警方有纪律,我不能把档案给你。但是我会复查相关的材料,看看是不是有疑点。”林非诚恳地建议“如果你打算自己查,不如让阿瑞帮帮你,我知道他……”
“不!”莫离打断林非,十指交叉放到膝上,“不要告诉他,也不要告诉徐先生。”
沉思片刻,林非拿出张自己的名片,在名片背后写下个名字和一串数字,交到莫离手中。
“吴云?”莫离看着名片,“他不是徐先生的版权代理人吗?”
“对。吴云现在是负责徐默的版权代理,但他也是我朋友。你要是想查一些事,可以请他帮忙。他很专业,嘴也很紧,值得信赖。”
“谢谢!”莫离收好名片。
“我该回去了。你放心,我会尽快把复查的结论告诉你。”林非起身理了理风衣,随口又问,“你上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莫离停了停才回答:“上大学以后,我没回来过。”
“你现在能这么做,很不容易。”
“我一直放不下这件事。”
“不,我的意思是,你能回来,很不容易。”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客套话,莫离从林非平和的语调里听到了真正的理解,身为异乡客的理解。忽然间,莫离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被陌生人关怀的温暖,似有似无的亲切,就像面前的那抹秋日暖阳照进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