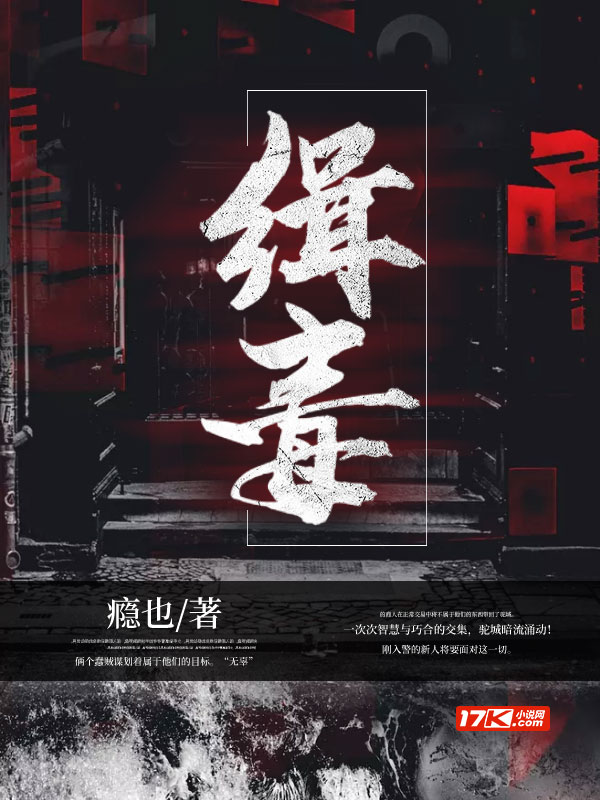田锦荣,这个孤零零写在纸面上的名字,和其他人之间没有任何已知联系。
早上七点十二分,林非坐上开往沧滨市林宏乡的大巴车,摇摇晃晃地盯着记事本上自己手绘的涉案人员关系图。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警方办事效率的了解,林非相信,刑侦支队已经对所有涉案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做了广泛调查。但从那晚发现抛尸者冒充张卫强时,在场人员欣喜若狂的表现看来,正义女神的案子查到现在,已经获得的、有价值的线索并不算太多。尽管不知道警方下一步的调查方向和重点,林非本能地选择了田锦荣作为调查的突破点。她隐隐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田锦荣那种反常的“与其他人毫无联系”很可能就是破解正义女神身份的关键。
沧滨市到林宏乡由高速公路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再走六十多公里才能到达在林场中心地带的均安镇。但那六十多公里全都是两车道的盘山公路,中巴车一路颠簸。快十点多,车终于进入了均安镇。但对于如何开始打听田锦荣的情况,这一路上林非依然没有做好准备。
均安镇地处偏僻,但是人口密度并不小,居民主要是原来林场的工人和附近开垦茶场的茶农。田锦荣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亲戚朋友想必不少。而和他有过短暂婚姻关系的前妻朱红琴早已再婚,现在朱红琴段树新夫妻俩就在镇上开照相馆。当地派出所协助刑侦支队前期调查过田锦荣,想必他“杀人抢劫犯”的恶名早已在这个小镇上家喻户晓。警方前期调查发现,实施抢劫之后,曾经有人在均安镇见到过田锦荣的身影,但却没有人承认和他见面交谈过。抢劫所得的现金,除了少量遗留在出租屋中,有十五万元至今不知踪影。更何况与以往和方亚静一起行动不同,现在林非孤身一人,又没有警方的合法身份,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如果贸然打听田锦荣,出于普通人惯有的防范意识,直接碰钉子的可能性很大。
均安镇的中心是一条双车道的柏油马路,两侧店铺林立,百货超市、理发店、网吧、手机营业厅等等,应有尽有,足够满足镇上居民日常生活所需。中巴车避让着骤然增多的行人和车辆,缓慢朝着汽车站开去。林非盯着路边正在翻修扩建的均安镇卫生院,心中突然有了个主意。
汽车站紧邻着镇上的集市,赶集的人很多,挨肩擦背,非常热闹。摩托车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顾客们怀抱着大大小小的货物,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从人群中见缝插针般的疾驰而过。
林非下了车,正打量着周围环境,一辆摩托车停到她面前,四十多岁胖乎乎的司机叼着烟热情地招呼她:“小姐,要坐车吗?”
林非笑着摇摇头。“我想找个照相馆洗几张照片。”
“上车,我带你去,五块钱!”司机一拍后座。
“去照相馆还要坐什么车啊!”另一个高高瘦瘦、年纪相仿的摩托车司机站在路边,冲着林非喊,“别听他的,往前走,看到胖胖网吧就左转,沿着那条路再往前走几十米就到了。这里就一个照相馆,旁边有个小超市。”
“嘿!搅我的生意!我撞死你!”司机一踩油门,冲着那人就去了。等到了人前,却一捏刹车停稳,伸手接住被抛过来的一支烟。
林非对着嬉笑打闹两人道了声谢,朝照相馆方向走去。她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左转进入一条五六米宽的安静小街。沿街大部分都是住户,照相馆在小街的中央位置,是一栋破旧的单层平房。它的门脸不大,双开玻璃门顶上的黄色招牌写着“红琴照相馆”五个字,红漆的字迹已有些斑驳。林非没有贸然推门进去,而是从旁边小超市里买了一瓶运动饮料,边喝水,边站在照相馆大门旁观望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没有一个顾客进出照相馆的大门。
将手中的饮料喝完,林非不紧不慢地推开照相馆的大门。二十平米的屋子里空无一人,地面很干净,墙体贴着白色瓷砖,没有任何杂物,两侧的墙上挂着数十张黑白彩色的人像照片。左手边靠墙有台老式电脑,两张方凳,右手边的橱窗里面陈列着各种镜框和相册。正对着门的是玻璃柜台,柜台后面的墙上挂着照相馆的营业执照,表明照相馆的老板正是朱红琴。
“请问有人吗?”林非对着里屋招呼。
“来了,来了。”一个身材纤瘦,文文静静的中年女人快步从里屋出来。她看见林非愣了愣,立刻又一脸笑容的招呼她,“小姐,你想照相还是洗照片?”
“我想照一张两寸的彩色证件照,洗四张。”林非微笑着回答。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好。”女人指着柜台玻璃上贴着的价目表说,“半个小时就能取,四张两寸十五块。”
林非低头从手袋里掏钱包时,一个中年***在照相馆大门外大声喊了句:“红琴,老段人呢!手机怎么打不通!”
“他去山上啦!信号不好!”朱红琴探起身大声回复一句,又抱歉般的对林非笑了笑。
林非微笑着将十五块零钱放到柜台上,朱红琴刚从抽屉里拿出记账本,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从里屋跑了出来,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妈妈,我要吃果冻!你给我钱!我要去买果冻!”
朱红琴没看男孩一眼,假装生气地说:“不许吃!刚退了烧!快回去躺着!明天好不了又不能去上学了!等期末考得不好,看你爸不打烂你屁股!”
“我要吃!我就要吃!”小男孩走到柜台前,眼快手急地抓起林非放在台面上的一张十元人民币,快步冲出照相馆,边走边喊,“吃了果冻病才好得快!我明天就去上学!”
“那是客人的钱!”
朱红琴拔腿要追,林非急忙打圆场拉住她。“没事,没事,我是要照相的。”
虽然林非毫不介意,朱红琴又气又尴尬地解释:“我这儿子来得不容易,被我们两口子宠坏了。”
朱红琴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和田锦荣离婚两年后,二十七岁的她嫁给现在的丈夫段树新,过了九年,一直到三十六岁,夫妻俩才有了唯一的儿子,想必也是捧在手心里如珍似宝。
林非笑眯眯地说:“长得很像你,很聪明的样子,学习成绩一定不错的。”
朱红琴边将林非让到后面的房间,边不好意思地说:“哎,贪玩的很,期中考试数学才考了七十几分,他爸气得追着他打。要不是他奶奶拦着,腿都打断了。”
站在房间门口,林非四处打量了一番,这间屋子应该就是整个照相馆的摄影棚。十五平米不到的狭长空间里,摆满拍摄用的衣物、鞋帽和背景画布,只留有那面白墙和前面两米不到的拍摄位置。
朱红琴从角落里拖出来两个摄影灯,一左一右摆到一面白墙前,又搬来一张方凳,回头见林非站在房门口张望,忙招呼她:“屋子有点乱,我们原来准备下个月就重新把店里装修一下的。到时候会新买一套洗照片的机器,还有最新款的相机,再多添几套衣服和背景。”
“拍证件照足够了。只要技术好,那普通相机也能拍出漂亮的相片。我看您店里墙上挂着的那些照片,拍的人都很漂亮,还特别精神,有气质。”林非坐到方凳上,善解人意地转移话题。
“哎,哪里,你客气啦。以前没见过你,是第一次来镇上吗?”
“是,我是学医的,听说这边镇卫生院招人,过来看看。”
“你是医生啊?他们是在招人呢。你头往左偏一点。”
两人正边说着闲话,边摆弄着姿势照相,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招呼声从照相馆大门处传过来:“红琴!红琴!”
朱红琴还没来得及放下相机,一个中年女人满脸通红地跑进房间,大声喊着:“快去看看你儿子!他憋过气去了!”
男孩侧躺在隔壁超市的地板上,胸口急速起伏,嗓子里发出低沉的喘鸣,脸色和嘴唇已经憋得有些发青。另一个年龄相仿的胖男孩站在旁边,涨红着小脸哇哇大哭。朱红琴两步迈到儿子身边,跪倒在地,扶起他的头不住地问:“儿子,你怎么了!怎么了!”
中年女人站在一旁急忙解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他就买了包果冻,两个小家伙在旁边打打闹闹的,突然咳嗽了两声就倒在地上了!”
果冻!
扫一眼散落在地面的几个果冻,林非冲到胖男孩面前问:“你们是不是吃果冻了?”
胖男孩边哭边点头。
“他是不是卡住了?”
胖男孩又点点头。
“卡住了?那快去卫生院!”朱红琴立刻抱起儿子。
“先急救!”林非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对朱红琴说,“帮我扶着他!”
朱红琴愣了愣,立刻“嗯”了一声,将儿子抬起来。林非站到男孩的身后,深吸一口气,心中默念,“Heimlich maneuver.”双臂环抱住男孩,林非一只手紧握拳头,用拇指的掌关节顶住他的上腹部,另一只手的掌心压住拳头,控制住足够的力道,又不至于造成内脏和骨头的损伤,快速地挤压腹部。一次、两次、三次,林非咬紧牙一连挤压了十几次。终于!男孩重重地咳嗽一声,吐出半个果冻,然后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
观察了半分钟,林非确认男孩已经恢复了正常呼吸,急忙对朱红琴建议:“好了,快去卫生所!”朱红琴立刻背起全身瘫软的儿子,林非和中年女人一左一右扶在两侧,一同往卫生所方向跑去。
因为林非及时将堵在男孩气管的果冻取出,他窒息缺氧的时间并不太长,医生做了详细检查后,最终诊断男孩幸无大碍。心有余悸的朱红琴仍然执意为儿子办理了住院手续,要求继续留院观察。看着朱红琴和护士将男孩送进病房,林非没有跟着进去。她掩住满身的倦意,摇摇晃晃地坐到走廊墙边的座椅上。
一个高瘦的中年男人急匆匆地冲进病房,一脸紧张的站到朱红琴身边,连声问道:“怎么回事?老婆,怎么儿子突然病成这样?”来人正是朱红琴的丈夫段树新。
原本情绪已经平稳下来的朱红琴,一见段树新的面,眼圈立刻红了起来,靠住中年男人的肩膀不住地抽泣,小声将事情的原委从头说了一遍。和惊魂未定的朱红琴不同,死里逃生的男孩早已恢复了精神。他半躺在病床上,手里拿着朱红琴的手机,眼睛一会盯着屏幕,一会看看小声交谈的父母,吐吐舌头,做做鬼脸,一副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模样。
林非怔怔地望着不远处的一家三口,慢慢低下头,凝望住自己的双手。这双手,曾经救助过很多人,曾经探寻过无数案件的真相……然而,在那样的一个雨夜,她却无能为力……至今,那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身受重伤,生死不知……悲伤和悔恨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她,林非猛然将脸埋进手掌中,掩住湿漉漉的双眼。
“小姐,真是太谢谢你了!”和段树新一同站在林非面前,朱红琴感激地说,“我们去找院长,告诉他你刚刚救了我们的儿子!”
朱红琴的话让林非哽住的喉咙里泛满苦涩,她抬起头,终于说出心里的话:“我不是来卫生院找工作的,我叫林非,是市公安局法医中心的法医。我这次来,其实是想找你问问关于……关于……”林非扭过头,将目光投向病房里,看着男孩没能再继续说下去。
夫妻俩的笑容凝住,朱红琴瞪大双眼,紧紧盯着林非,还强撑着微笑。搂住妻子的肩膀,段树新冷着脸,压低语调小声说:“法医?法医又不是警察!你有什么权利来问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朱红琴不知所措的看着丈夫,又看看林非,垂下头,没有说话。
轻声叹口气,林非微微颔首,“你说的对,身为法医,我的确没有权利来问你们。”
“那你还不快走!”段树新握紧拳头,低声呵斥道。
“但我今天,不是以法医身份来找你们的……”林非舔了舔嘴唇,强压住哽咽,“一个月前,我的丈夫也被人袭击了,现在在医院里只剩下半条命。袭击他的凶手,和杀害田锦荣的,是同一个人……”
“你老公是死是活,关我们什么事!”段树新瞪着林非恶狠狠的又说,“你不要救了我儿子就能……就能……”
“老公……”朱红琴握上段树新的手臂,对他轻轻摇摇头。
段树新轻轻拍拍朱红琴的手背,安慰般的和她对视一眼,扭头从裤兜里掏出钱包,又对林非说:“感谢你救了我儿子,我……”
迎着段树新的目光回望过去,林非缓缓起身,段树新下意识的将朱红琴护到身后。
“我不会要你的钱。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法律有权利、有资格对他们进行公正的审判。而不是被那种自诩为正义女神的暴徒,夺去生命,再把他们的身体……随随便便……丢到街上。”林非低声说。
朱红琴猛然用一只手捂住嘴,低下头,将额头用力抵住丈夫的后背。
平静地看着手足无措的朱红琴,林非又仿佛自言自语般继续说:“不好意思,我骗了你。照片我其实是用不到的,我也不要了。祝你的照相馆生意兴隆。对不起,打扰两位了。”
林非收回目光,转身慢慢向楼梯走去。刚走出去三四步,她忽然扭头又说:“还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你们,田锦荣抢的钱到现在还有些没找到。但那些钱,银行和警察那每一张都有记录,是不能花的。”
林非的最后一句话,让夫妻俩霎时变了脸色。
“林小姐!”朱红琴突然快步追上来,她挽住林非的手臂,强作镇定地说,“你救了我儿子,现在已经中午了,让我请你吃顿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