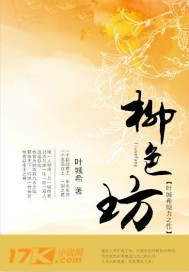老蔫一家子到处治病,周嫂子一个人经营面摊子,女人家抛头露面不方便,更何况西城本来就靠着大山,人烟稀少,老蔫媳妇也不过二八年华,看在男人眼里自然是水灵灵的一朵娇花。
周嫂子拿棍撵过,拿石头砸过,也没砸掉那些老光棍的坏心思。她不敢给婆家人说,怕老蔫多心,便养了条大狗,整日不离身地跟着。
那晚周嫂子收拾摊子,把东西搬进屋里,半天没见大狗跟进来,刚准备扭身去叫,被人从后面拿帕子捂住了嘴,帕子上有药,周嫂子挣扎了几下就失去知觉。
周嫂子是被婆婆用冷水泼起来的,睁开眼,看见老蔫和婆婆站在身边,老蔫神情暴躁、痛苦,婆婆目光怨毒。自己则躺在地上,赤身裸体,连个遮掩的都没有。
老蔫媳妇知晓发生了什么,侧身蜷起身子,任由婆婆疯了般的辱骂和抓挠。此刻,她连眼泪都流不出来,甚至有些想笑,觉得活着怎么这么难,为什么别人伤害了她,她还要被世人唾弃,她做错了什么?
女人不能生得忍辱吞声,得被休掉,丈夫不能生,就可以抱养。别人伤害了她,受打骂折辱的还是自己,所有人都责问怎么就是你遭难,怎么不祸害别人,肯定是你有问题。
难道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坨狗屎,人见了都躲开才正常?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关心一下受伤害的她的感受,问问她是不是很害怕?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她的人们,是不是就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会被人迫害?
老蔫媳妇一个人在西城面摊放行李的茅草房里呆了两个月,没有人过问她的生死,也许他们盼着她死,这样大家就不用尴尬了。
连续几天,老蔫媳妇发现自己经常呕吐,发困,爱吃酸的,月事也没来,常年想要孩子的她当年知道这是怀孕了。
慌乱过后,周嫂子打定主意,不论这孩子是谁的,总是她的骨血,是她在这世上的唯一念想,她要保住他,不然在这冰冷的世界上还有什么盼头。
周嫂子回老蔫家提出了和离,她就是讨饭也能会把这孩子养大。母为子则刚,周嫂子昂头独自面对老蔫一家的辱骂,手放在腹部,没有辩解。
老蔫娘气极,巴掌往周嫂子脸上招呼。周嫂子拨开婆婆的手,反抗道:“你们怎么骂都行,这个孩子我是留定了,你儿子不能生,难道要让我一辈子当不了妈?”
老蔫媳妇嫁进门这么久第一次和婆婆顶嘴,忍了许久的周嫂子战斗力爆发,出招就冲夫家的痛处下手。一句话出口,就让咒她不得好死的婆婆住了嘴。
“你们要沉猪笼我也认,起码我死的时候这辈子嫁人、当妈都体验了。沉了我,说不定你们家能娶个可以治好你儿子毛病的好媳妇,我这媳妇不称职,也当得窝囊,你们赶紧休了我,对大家都好。”
周嫂子娘家孩子多,想得到更多的资源就得自己争取,她自小也是个泼辣的女子,不是好拿捏的软柿子。
嫁人前,娘嘱咐她夫家家境富裕,规矩和他们家不一样,得多收敛脾气,孝顺公婆,才能在家里有地位。真心换真心,一家人过日子,你对别人好,别人嘴上不说,心里也会明白的。
所以进门后,她处处小心,加上一直没有孩子,她也气短,才事事忍让。今日不是豁出去不过了,她都快忘了自己原本是个什么脾气。
一家子被周嫂子镇住,好像不认识这个媳妇一样。
老蔫爹吧唧吧唧抽着旱烟,一直没开口。等到隔壁传来喊孩子吃中饭的声音,老蔫爹起身,把旱烟袋在桌边磕了磕,说:“留就留吧。”
老蔫娘尖叫:“这个孽种不能留!你想让别人笑话我们一辈子吗?”
“早都被笑话了,也不在乎时间长短。”老蔫爹说:“儿媳妇,饭点了,去做饭,今日家中有喜事,我要喝两盅。”
周嫂子愣住,她知道公公说话算话,让她留,这孩子不仅能保住,还能有个完整的家。
“爹,我.....”周嫂子哽咽,对着公公跪下,眼泪下雨一样把地面打湿了一小块。被婆婆咒骂时淡定的周嫂子对公公感激涕零,能接受这样的事,她后半辈子一定把公公当亲爹伺候。
“行了,哭啥,这是喜事,说明大夫给的药起作用了。”老蔫爹说:“去做饭吧,饭点快过了。”
老蔫爹发话,家里默认了这个孩子,对外说是治疗见效果了。几个月后,孩子出世,是个大胖小子,一家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周家有后了,忧的是看见孩子心里难免膈应。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孩子一天天长大,没一点像老蔫的,好事者将当年的事捕风捉影,拼凑成了一个香艳的故事,成为青坪镇茶余饭后的新话题。
在这个老蔫借腹生子的版本中,让老蔫媳妇怀孕的那个人是个长相俊俏的串货游郎,和老蔫媳妇在城西的铺子里几度春宵后周嫂子成功怀孕。周嫂子一个人在西城住了几个月,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甚至加入了老蔫娘反复思想斗争的过程,老蔫爹给了那人一笔钱让签了保证书证明孩子以后和他无关,老蔫又是如何给媳妇下跪做思想工作,媳妇如何含泪答应。
这个可以无限遐想的话题让小镇的人兴奋,不断地增加枝节末叶的描述。老蔫家始终没有回应过这些事,路上碰见说闲话的,当没听见一样过去打招呼,议论的人自己就不好意思了。
大家说老蔫下面蔫了,连骨气都蔫了,背地里开始老蔫老蔫的称呼他,后来顺嘴了就当着他的面也这样喊,他的真名倒是很少有人记起来。
老蔫羞愤,回家只能拿老婆出气,对周嫂子动辄打骂,打完了又内疚,抱着老婆哭,生怕老婆离开自己。周嫂子心疼老蔫,日子却也实打实地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