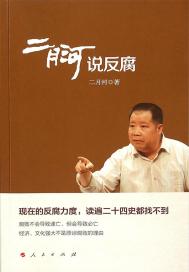曹白
战争既然开始,一天到晚坐在屋子里听炮声,爬到屋顶上看飞机,虽说也算得“战时生活”,但总不是办法。首先使我想到的,是应该着着实实的做些事情的时候了。但又并不是说我自己要上火线去拿枪杆。枪杆,我是不会拿的。我所能够做的事,大抵只能在后方。
然而这也难。我东奔西走,入会,开会,提议,讨论了好多天,毫无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后来忽然听到一句“谣言”了,那仿佛隐然的说:“救国无门呀!”于是我这才觉悟,在后方,并不是没有事情,恐怕是在事情的周围造了高墙了。
但这种觉悟了的味道是苦的。
有一天的黄昏,偶然遇见了浓眉毛的H,他瞪着眼,对我描述了平时只会手拿佛珠,口年弥陀的和尚们,这回却戴着笠帽到火线上去救护伤兵的勇敢的故事之后,他说起有一个慈善机关正在救济难民,开办难民收容所,可惜没有人去帮他们忙。我倾听之下,很欣喜,就马上决定了:
“我去!”
一去就是办登记。——我拿了铅笔和登记的表格,走进难民丛中去,第一个我登记的是一个老头儿:
“老伯伯,你叫什么呀?”
“我的家住在杨树浦,先生。”
“不是,我问你,你名字叫的什么呀?”
“噢噢,问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叫阿二。”
“姓数呢?”
“姓王,——三划王。”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吗?我是三十六岁到上海的,先在偷鸡桥摆一个小摊,后来摆小摊是,也难,咳咳,也难过。到四十岁上,我的儿子也到上海来了,诺,就是这个,他叫福郎……”
“你的儿子的名头,我也要写的。现在你只要告诉我,你今年几岁了?”
“噢噢,我今年五十一岁了:属猪。”
“你是哪里人呢?”
“南京。”
“南京吗?听你的口音,有点像泰兴的呢?”
“不,我不是泰兴——我不是江北人!先生,你若是不信,随便去问哪一个去!江北人是黑良心的呀——我的的确确是南京人!不是江北的!”
“不是的,老伯伯,这不打紧的,你哪里人就说哪里人,不要做假。”
“唵,先生真是,我还要做什么假呢,反正到了如此的地步了!”
“那末,你是做的什么生意呢?”
“到上海,先摆一个小摊,在偷鸡桥。后来福郎来,他的娘舅是好心肠,他把福郎荐进芋荷去,织哔叽……”
“你儿子在怡和厂的吗?”
“是,是在芋荷。是大英的。我就去烧饭,福郎的娘在上次‘一二八’,被东洋人一个炸弹,她——”
“那末,我问你,老伯伯你家——”
“我家就在杨树浦××里十二号,你若是不信,随便去问哪一个去。这回我和福郎,要是不逃得快,先生,真是,也要和福郎的娘一样了……”
“老伯伯,不要着急,我们打了胜仗了。”
“谁着急呢?打了胜仗了吗?打到杨树浦了吗?”
“打到杨树浦了。汇山码头也夺回来了。”
“好好!”
然而不好。因为我们的收容所是设在电影院里的。电影院的建造,本来只为了享乐的人们,并非了的受难的百姓,那首先第一的缺点,就是窗牖的稀少。能容二千左右观客的这么一个巨大的电影院,还只收了四百多个难民呢,就觉得窒息不堪了。天又热,而难民们在逃亡之际,总想多带一点自己的财产,所以有许多箱笼包裹,并且有些人还驼着棉衣或夹袄,情愿脸上挂着一条一条的汗流。可是,这样一来,汗臭霉臭,便充满了一屋子。
再加呢——说起来,真要使语堂先生大笑不止的,就是这些难民大抵是粗人,没有出过洋,用不来抽水马桶;有的竟至于一面抽水,一面撒污,水污交迸,溅满了一屁股。所以两间厕所,不到半点钟,就一塌糊涂,变成马厩那样了。于是在汗臭霉臭之中,夹以骚气,充满了一屋子。
事情既然到了这般地步,我就在难民中选出几个人,组织清洁队,教授“抽水马桶使用法”,把厕所洗刷了一番。然而虽然这样,到底还使有些调查的委员,“慰劳”的摩登女郎们,掩鼻而过,或者戴起卫生口罩来。
难民的每天的粮食,是我们上司发下的。发下的是饭。一日两顿,每人每顿吃一斤——十六两。据我的经验,他们要比囚犯吃得少三两。但能够弄到饭吃毕竟要算上上了,有的地方,只喝两顿稀饭哩。——也要过日子!
但那电影院的业主们确使我讨厌的。单以点灯而论,他就只给难民开了五十支光的两盏,可是他却偏偏横说自己是“牺牲”了,竖说自己是“牺牲”了。有一位还竟至于每见我时,总爱侧着头,斜耸着肩胛,直着眼,像一匹傲悍的公鸡。对于难民,他是开口猪猡,闭口猪猡的,以显示他是高踞“猪猡”之上的大人物。
大概真是“猪猡”之故吧,有一个难民收容所,被解散了,浓眉的H还几乎被带到“局”里去,但H是平安的。而那些被驱的难民,大部分又向南火车站逃去了。然而,呜呼,当然就来了一群日本的飞机,将他们跟别的一起,炸的无影无踪了。我想,其中谁是幸免于“难”的?——谁知道呢!
此之谓“难民”。
但自己的收容所里的难民,也委实会出“难”题目。他们自动集合了二十多个人,全是青年,连王福郎在内,一致要求我代他们设法到前线去,那理由是:
“我们在这里光是吃吃睡睡,无聊。我们愿意上火线,扛子弹,掘壕沟……枪不会放,力气是有的。”
我是明知道自己没有“代他们设法”的能力的,但为了不使他们失望,也就只好连连点头,答应了他们。
但是当天的黄昏,王福郎却扯着我的衣角,嘴巴附在我的耳旁,低低地说道:
“先生,你不要告诉我的爹,说我是要上火线去的啊!”
夜晚,我在守夜。
电影院业主们所赐给这四百多个难民的两盏电灯,放着惨淡的光彩,这巨大的建筑物,就显得异样的幽黯和昏沉。难民呢,他们大抵摆脱了白天的焦灼和哀愁,渐次入梦了。
我寂寞的环视了这灰暗的戏院,难民的鼾声起来了。在鼾声的相互的拍击中,我发现一支毛竹的扁担,竖在一只坐椅的背后。走近去看时,我才知道,这扁担是王阿二家的,福郎为了睡觉的舒服,一只手还贴紧了扁担的下端。然而那扁担的上端却已开裂了。
我在睡着了的难民的中间,来回的走着,小心翼翼的,唯恐惊醒了他们。偶一回头,就看见福郎的扁担,在整然的坐椅中间矗立着。因为灯光的衰微,它显得格外的粗大,宛如一支倔强的铁铸的臂膊。
十二点的半夜过后,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上的大炮又在隆隆的轰鸣了。我忽然这样想,“也许,我就会变成难民的吧。”但我听得格外清楚的却是围绕在我身边的四百多条生命的强烈的呼吸。
1937年9月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