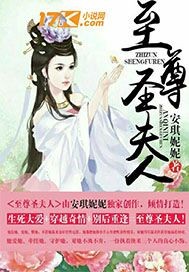不知是巧合还是太子气数已尽,众人的瞩目的寿王大婚宴会散场之后,太子意犹未尽,拉着光王、鄂王、林少顷等人回东宫接着豪饮,却不知城府极深的驸马杨洄跟着他们一同回了府。
通宵达旦饮酒,众人都喝的醉醺醺的,太子李瑛酒上心头,数落当今皇上偏袒溺爱惠妃娘娘,才会招致淑仪娘娘一生抑郁,含恨而终。酒后失言,他更是大放厥词,取出床头的霹雳木人偶玩起厌胜之术诅咒惠妃娘娘不得善终。
酒场疯语,大家听后都不以为然,一笑置之。
谁又知,祸从口入,杨洄回到驸马府枕边风轻轻一吹,天还未亮咸宜公主已前往皇宫通风报信。太子等人还沉醉在酒乡时,一封由杨洄执笔添油加醋描述一番的加急文书以及已通过咸宜公主送到了武惠妃的手中。太子众人再次卷入是非风波,事无巨细,就连那尊酷似武惠妃的霹雳木雕像也描述的极为详尽,令人无从辩驳。
“咸宜,驸马所写之事可否确有其事?”武惠妃当即皱起眉头,沉声问,脸上寒意渐浓。
咸宜公主用力的点了点头,认真且肯定的回答,“母妃,千真万确啊!您还不知道,驸马向来千杯不醉,有酒中君子之臣。今日他三更天气嘟嘟的回府,将昨晚的大小事一同记下,非要去换身衣服去父皇那里参太子等人一本。儿臣怕他冲动误事便将他拦下,劝解一番后,这才刻不容缓的进宫面见母妃呐。”
这世上当坏人容易,可是既当祸害贻害千年又能保全自身的坏人不多见。因为这种人,越是被激怒,就越理智,运筹帷幄才出手,而武惠妃恰巧是这种人。
武惠妃目光森然盯着信件上力透纸背的一行行字,嘴边扯起一丝残忍的笑,“真好,本宫还未想出什么招数对付他们,他们就自投罗网了。”
“是啊,母妃,昨日是寿王弟弟的婚宴,太子一党竟公然触咱们霉头。不仅藐视、辱骂您还想用那厌胜之术置您于死地,这种背后中伤您的行为,既狠毒又卑鄙,枉为父皇仁君的教诲。咱们一定不能坐以待毙,否则他日待太子一行人羽翼丰满后便会觉得咱们好欺负,更加肆无忌惮的。”咸宜公主气急败坏的火上浇油,冷哼着挑拨道。
“本宫自然不会放过他们,一个都别想逃!咸宜,你的话提醒了本宫。太子所作所为确实有违皇上仁德之教诲,所以这出戏还得由皇上来唱。”武惠妃心里盘算一番后,薄唇轻抿,胸有成竹的冷笑道,大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之意。
闻言,咸宜公主的眸子精光闪闪难掩兴奋,脸上一副虔诚受教的模样,“儿臣最喜欢看戏,母妃,这出戏咱们如何导演?”
“不急,不急,咸宜,你要记住,万事布置周详才能一击而中、一招见血。这厌胜之术是枚本是太子置我于死地的一枚死棋,如今到了本宫手里却是枚活棋。”武惠妃胜券在握的说,双唇勾出妖媚的弧线。
暗夜即过,旭日东升。
端坐在梳妆台前,茯苓用手拨弄着铜镜的角度,镜面里映出一张可怖的脸,同时也映出站在她身后的端着洗脸水的绿萼。她扳着镜子自嘲的说,“绿萼,我的模样是不是真的特别丑?”
被她问得一怔,绿萼捧着水盆,放也不是不妨也不是,见茯苓的神色并无异常,一本正经的说,“公主才比天高,聪慧过人,纵然舍了这份美貌,也必能俘获如意郎君的心。”
“进宫这些日子,多亏你在我身边照顾。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对我好,不必拘束,这里也没有外人,今日咱们姐妹说些掏心窝子的话。”茯苓对她刻意安慰的话十分感激,起身拉了个椅子来,示意她坐下。
绿萼诚惶诚恐,如坐针毡的问,“公主,您有何话同奴婢说?”
“绿萼,你有心上人吗?”茯苓轻声问。
“没…没有。”绿萼头摇得似拨浪鼓,深怕会被人怀疑似的。
茯苓无不羡慕的低叹,“不知愁的年纪真好!”
“公主不必担心,以貌取人最肤浅,奴婢相信真正懂得您的人绝对不会在乎您的容貌。况且,这伤只是暂时的,很快便能被御医们治好的。”绿萼不忍见她黯然伤神,脱口而出一句能冠冕堂皇的自欺欺人的话。
“有人刻意陷害,治好谈何容易?”茯苓哀伤的看了她一眼,继续道,“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强大之人,强大到忽视容貌也可以。我以为我能不因容貌而屈服于歹人要挟,哪知我太高估自己。面对丑陋的容颜,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般肤浅。对一个女人,不管美与丑,容颜永远不能说不重要。而对于一个男人,若想让他真正不在乎女人的容貌,除非他瞎了。”
绿萼一时语塞穷词,不知如何宽慰她。
“你未经历过爱情,跟你说你自然不会懂的。”茯苓无奈的摆弄着手指,漫不经心的问道,“最近宫里有什么动静?”
“华妃娘娘还是老样子,病气入体,已是许久不下床走动了。倒是今儿听说,惠妃娘娘病了,而且病得很是蹊跷。”换了个话题,绿萼如释重负地回答。
她说的是轻描淡写,可茯苓听到耳朵里却不那么轻松,好奇的问,“如何个蹊跷法?”
“听人说今早惠妃娘娘无缘无故晕厥,数十名御医诊断都没有结果。惠妃自醒后便疯疯癫癫,哭着喊着有人要杀她,直说自己心口疼,皇上去了也是束手无策。如今新婚燕尔的寿王也即刻进宫侍疾。公主要不要去看看?”尽管屋中只有她们二人,绿萼仍旧是压低了声音。
茯苓看了屋外明媚的阳光,意味深长的说,“闲来无事,咱们去远观一下也好。”
梳妆完毕,两人正要出去,却听门口的小太监在门口回禀说,忠义侯求见。
准了他的拜见,茯苓重新坐回座上,摆着一张晚娘脸,冲着进门的谷天祈冷嘲热讽的说,“忠义侯今日怎会这么有雅兴来未央宫这种小地方?”
“绮玉被皇上召进宫为惠妃娘娘治病,我抽空看看你。”谷天祈怎会看不出她的心思,低柔的说道。
绿萼福了个万福,识趣的退了出去。
“小女子何德何能,竟然使得忠义侯拨踵前来?”茯苓见他如此云淡风轻,眼中带着怒意。
“你还在生我的气?”谷天祈走近一步,微笑着问。
茯苓不自觉的退后一步,冷冷的说,“别的女子亲昵的称你为相公,看着你们打情骂俏,难道我应该大度的拍手叫好,祝贺你们吗?不好意思,我没那么伟大,我做不到。”
“苓儿,你误会了,绮玉受伤才会记忆错乱,我与她没什么的,我以为你能理解的。”谷天祈低下头,声音沙哑的说。
还是就这一句解释吗?茯苓露出失望的表情,“把我晾了这么多天,你一句误会便想打发我,你不觉得自己既可恨又残忍吗?”
谷天祈苦涩的一笑,“很多事我也是身不由己。”
“为何我们之间会有这么多的误会,难道你一句身不由己,便能完全抹干净吗?我没有河图洛书,不能推测你的心意。我累了,也厌倦了费神费力的猜测你的心情。如果爱一个人会这么累,我情愿放弃。”茯苓没有表情地说道。常常为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一句话、一件无不足道的事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这种小心翼翼的情绪,她受不起。
“那我先走了,这是我配置的药,希望对你脸上的伤有帮助。”谷天祈脸上露出痛苦的情绪,苍凉的说,将手中的药盒塞进她的手中转身就走。说不出口啊,她是他从小就疼爱的女子,他多么想告诉她他的苦衷,可是,他发誓要保护那个有关绮玉的秘密。
没想到一时气急,竟然说出这般无可挽回的气话,茯苓想出口挽留,却在看到他绝情的背影后,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见谷天祈踉跄的迈出大殿,绿萼从门口闪了过来,“忠义侯好不容易来一趟,公主何苦要弄得两人都不开心呢?”
“要走的人留不住,要留的人赶不走,一切都是命。咱们去夜华宫看看。”茯苓含糊其辞的回答。
“还没进入夜华宫,茯苓已听到歇斯底里的叫喊声。走进去一看,更是大吃一惊。富丽堂皇一向整洁有序的夜华宫,已是乱糟糟的,桌椅被踢翻,精美的花瓶摆设碎成一片片。就连高贵无双的惠妃此刻也是蓬头垢面,疯言疯语。
“爱妃别怕,到朕这里来。”唐玄宗温柔的低语,脸上的哀伤与担心一丝不假。
武惠妃一只手绞着自己的乌发,另一只手握着一支发钗对着众人防止接近,对着唐玄宗神经兮兮的小声说,“皇上,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我。”
“有朕在,没人敢动爱妃的。乖,到朕怀里来。”唐玄宗循序善诱的劝着。
武惠妃向他走了几步,却突然躺在地上打起滚来,便哭边喊,“好痛,我的心,咳咳,我呼吸不能了。救我,救我!啊!啊!!”
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听得人心寒,寿王连忙上前扶住她,冲着一旁的御医怒吼,“御医,我母妃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御医擦拭着额头的冷汗,意有所指的说,“依惠妃娘娘的病症来看,只怕不是病,而是……”
“知道就快说,别支支吾吾的。而是什么?”唐玄宗蹲下身将她摁在怀里,不忍见惠妃咬着手腕靠自残来以痛止痛,随即将自己的手放进她口中。
在唐玄宗强硬眼神的逼迫下,老御医颇为为难的开了口,“以微臣愚见,惠妃娘娘怕是中了厌胜之术。”
“你少胡说,父皇最忌恨厌胜之术,宫里谁人敢这么大胆子!”寿王冷冷的看了老御医一眼,那一眼有着说不出的犀利与森然。
此时,咸宜却是跪倒在唐玄宗脚边,痛心的道,“父皇,本来儿臣不想吐露此事。可是为了母妃的安全,儿臣只得实话实说了。”
“都什么时候了,咸宜,你要是知道什么,还不快说!”被惠妃的利牙咬得生疼,唐玄宗火急火燎的说。
咸宜公主这才哭哭啼啼说,“昨日驸马从太子府中饮酒回来,曾醉意朦胧的对儿臣说太子酒醉后指责母妃媚颜惑主,扰乱后宫,还拿出一尊霹雳木雕像行厌胜之术,诅咒母妃不得好死。儿臣见驸马醉醺醺的,恐他所说之事与事实不符,又念着与太子的兄妹情谊,故而不想将此事禀报父皇。谁知,御医竟诊出母妃中了厌胜之术,父皇,您一定要救救我母妃啊!”
“岂有此理,这个逆子!”唐玄宗身体不由微微一震,脸上露出狠绝戾气,“寿王,你速速带领一百名羽林军到太子府搜查,并将昨日醉酒等人全部带回宫中。”
看到这,茯苓悄悄拉着绿萼出了气氛有些紧张的夜华宫。
“公主,你怎么不看下去了?”直到走到一处无人的假山处,绿萼才不解的问出口。
茯苓只是浅笑,了然与心地说,“确实是一场好戏,只可惜不对我的胃口,我并不像趟这池浑水。”
“好戏?”绿萼茫然的问。
“惠妃娘娘倾情演绎,难得还算不上好戏吗?”茯苓冷笑着说。
“奴婢愚钝,以奴婢之见,惠妃娘娘真疯了,公主为何说她是演戏呢?”看出了她眼中的轻蔑,绿萼更加茫然。
茯苓耐心的指出可疑之处,“一个疯子会如此不着痕迹的避开满是碎片的地面,只在干净的地方打滚吗?一个疯子会有如此精明的眼神吗?一个疯子又怎么会思路清晰的喊出这些话?”
“这么说,太子是被诬陷的?”绿萼好一阵的心惊胆跳,说话时舌头都有些打结。
茯苓连忙捂住了她的嘴,嗔怪道,“笨蛋,这么大声,被人听到你不想活了?”
“晚了,这番话已经有人听到了。”说话间,两个身影从假山后侧走了出来。
皇宫就是个大污池,身在污泥内,岂能逃脱不染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