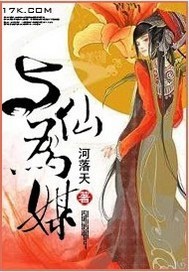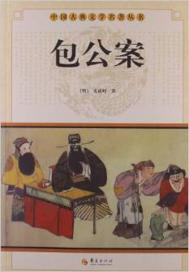只因苏盛这句话,武落蘅原本鼓起的勇气又一次消散,她默不作声,帮李隆基整理着案几上杂乱无章的奏折,而后又将空碗收起来转交给烟波,看着李隆基全神贯注的阅读,她打了退堂鼓,一个人悄悄的退了出来。
回到鹿鸣殿姚玉早已经等在厅内,一见她回来,焦急上前询问:“姐姐如何?”
武落蘅有些愧疚的说:“妹妹,我……其实……你知道姚相都在宫外做了什么嘛?”
她这么一问,姚玉心凉一半,看来武落蘅没有为自己的父亲求情,不过这对她来说并不重要,于是忧伤的说:“不瞒姐姐,开始我听到那些风言风语的时候并不相信,但时间久了,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父亲真如他们所说。”
武落蘅带她落座后,安慰道:“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事关社稷,岂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好在查证此事的人是范秦苑,我相信他不会让姚相蒙受不白之冤。”
姚玉叹了口气,也只好如此,心中盘算若能救出自己的母亲才好。
武落蘅见她依旧忧伤郁闷,有意岔开话题,向她请教道:“对了妹妹,昨日我听烟波说你做的桂花酥甚好,我也想学来试试,你可否教我?”
姚玉听此话灵机一动,马上回话道:“如此说来,臣妾的母亲才是做桂花酥的好手,里面有些秘方都是她亲自调配,连我都不得知,姐姐不如将她请来,一同传授。”
武落蘅点点头,这也不是什么麻烦事,便让清廉带着她的腰牌出宫去请,若是姚玉派人去请,姚崇必然不会放人,可惠妃来请,他却不能推辞,于是姚母顺理成章的进了宫,暂居微希殿。
话说两边,范秦苑与张说搜查王府后果然发现新的线索,一本王吉写的游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里面没有山水刻画,也没有风土人情,记录的竟是行程地点,很是可疑。
张说带回去研究了半日,才看明白,这原来就是各地各府售卖私盐获利后的分赃记录,他兴奋不已,找来范秦苑一起商讨。
“如何?”张说将已知的人员和游记中的地点一一对应解释后问道。
范秦苑恍然大悟,不禁赞叹道:“亏你想的出来,果然是这样。”
张说又把游记往后翻了几页,指着上面说:“你看这个,觉得应该是哪里?”
“瑶池?”范秦苑当然知道这字面意思指的是王母瑶池,可是哪里能称的上是王母瑶池呢?他细想了一下问道,“听闻塞外以北有一神山终年白雪覆盖,人迹罕至,群山中有一池水,可比王母瑶池,是不是指的那里?”
张说摇摇头不同意道:“塞北以外多是蛮夷,怎会需要精盐,何况送到那里有何利益,范兄往近处想。”
“近处?”范秦苑小声嘀咕着,一边在屋内踱步一边冥思苦想。
见他愁眉不展,张说得意的从桌边抽出一张纸,大笔一挥写下姚相府三个字,范秦苑看后,大吃一惊,但细想也算合情合理。
“张兄是说,幕后之人竟是姚相?”范秦苑一向佩服张说的推理能力,不过凡事都要大胆猜想,小心求证才是,便谨慎的说:“可是这都是猜测,光凭这些无法让群臣信服呀。”
张说自然知道,他早有打算,又将游记翻了几下,找到一句话读了起来,“自庆南出入武夷山终落瑶池。”
范秦苑与他并肩而站,专注的说:“庆南指的应该是庆南刺史李文敬,如果瑶池指的是姚相府,那这个武夷山就应该是他们的利益联络人,会是谁呢?”
“武夷山什么最有名?”张说问道。
“常听人说武夷山小种茶最有名。”范秦苑话一出口,便想到些什么,问道:“听闻武友慈每年都会给姚相送家乡特产白毛茶,会不会暗指是他?”
张说默认的点点头,“此人正在大理寺,范兄有没有兴趣一同去会一会。”
说完话二人一同到了大理寺,这里不止关押着武友慈,还有王守一,张说决定先提审武友慈,再提审王守一,便让狱卒将犯人带上。
二人高堂上坐,稍等片刻武友慈蓬头垢面摇晃而来,一拍堂木吓得他立刻跪了下来,连喊饶命。
张说清了清嗓子问道:“武友慈,你卖官之案已经定审,证据确凿无需多言,现在本官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可要好好珍惜。”
武友慈颤抖的跪在下面,心里不知是何戴罪立功的机会,只好胆怯的回话道:“大人开恩罪臣定当珍惜机会。”
“我来问你,王吉你可认识?”张说缓缓而说。
武友慈忖度着,小心回答:“认识,他与罪臣有公文上的往来。”
“他参与私售私盐一案,你可知道?”
武友慈连忙否定,大呼:“大人明鉴,我们虽有公文往来,但他所做之事我毫不知情呀。”
张说大怒,拿起堂木一掷吼道:“你还敢狡辩,他遗留下证据,写明与你如何分赃,你最好如实招供,免得受皮肉之苦。”
武友慈能从一名小小的官吏走到今日除了溜须拍马的功力,就数察言观色的能力最强,他透过碎发向堂上瞄去,张说虽然威严厉呵,但表情略显僵硬,而坐在一旁的范秦苑更是提着一股气很是紧张的样子。
武友慈心想:‘他们兴许是想诈我一下,看来我要咬紧牙关了。’
“大人,罪臣真的是冤枉,根本不知道什么贩卖私盐的事情,还请大人明察。”这武友慈是哭天喊地。
张说暗叫不妙,没想到他是个这么难缠的人,看来自己想要从他身上突破找线索的希望要落空,正想到这里,突然见狱卒慌张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大人,不好了,王守一……他,他死了。”
“什么?!”张说与范秦苑同时跳了起来,一前一后跟着狱卒向牢房赶去。
此时王守一已经没了气息,嘴角上挂着殷红的鲜血,眼睛瞪得犹如牛瞳,张说见仵作摇头,知道回天乏术,便问狱卒:“怎么回事?”
狱卒哭丧着脸显然也被吓得不轻,语速如飞说道:“我刚才送饭来,都是按照一直以来的顺序发到各牢房中,刚送完就听到王守一的牢房里传出惊叫声,赶来查看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了。”
范秦苑仔细观瞧,斩钉截铁的说:“应该是中毒,毒药就在牢饭中。”
张说揪起狱卒的衣领大吼道:“牢饭都经谁手?”
“这,这……这可多了,厨子,差役不说,就光牢里我们三个人都碰过。”狱卒委屈的说,这样说来的确不好追查,不过张说可不是一般人,他不会轻易放弃。
把这里的事初步料理后,范秦苑问他:“武友慈那边怎么办。”
张说冥思苦想,表情微妙的缓和下来,“王守一的死对他来说兴许是一记重拳。”
二人连忙返回公堂,武友慈依旧老实跪在下面,张说并不急于开始,好像是在等着什么,武友慈觉得奇怪,神情越来越紧张。
大约半盏茶的时间,一小吏前来回事,“回大人,牢中犯人已全部转移,除了王守一所食牢饭中有剧毒外,还在另一碗中发现毒物。”
“哦,是何人的牢饭?”王守一不慌不忙的问道。
那小吏高声说道:“是武友慈。”
跪在下面的武友慈一瞬间如被雷击,整个身体都软了下去,有人要杀他?
张说挥手让小吏下去,转而看向武友慈,范秦苑心中不免赞叹,果然好手段。
“武友慈,为什么有人要杀你呢?既然已经定案,只待陛下朱批便可,为什么还要送来毒药?”张说故意绕来绕去,就是为了扰乱他的心思。
果然武友慈在死亡面前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贩售私盐的事情,张说连夜将口供,物证准备妥当,准备隔日入殿。
虽然姚崇努力剪断之前的联系,但还是被张说抽丝剥茧,查到了最致命的证据,贞观殿上,李隆基怒不可竭,将案卷看完后大骂道:“监守自盗!枉朕如此信任,将六部交与他手,他就是这样回报朕的吗!”
殿中下立之人,除了张说和范秦苑外,还有宋璟,其实早在张说他们呈送案卷之前,宋璟已将姚崇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奏折递了上来。
数罪并罚,李隆基再无怜悯之心,即刻下旨,罢免姚崇宰相一职,命中书令宋璟清查姚府。抄家,流放,获罪已不可避免,念他也曾兢兢业业过,李隆基特将其家人赦免,凡查实无参与者送回原籍。
姚崇被罢,宰相之位有多少人垂涎三尺想要得到,不过谁也没想到,李隆基早已有了安排,这几年朝纲清肃,现在正是稳步发展的时候,宰相之人不需大才,但一定要刚正不阿,所以宋璟便是最佳人选。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后宫,德妃最是不甘心,以为推倒了姚崇,自家兄长就有机会,没想到被宋璟抢了便宜,只能再静待时机。
而贤妃全家被抄,她却显得格外淡定,对她来说已将母亲接入宫中,姚家与她再无瓜葛。
事情渐渐平息,眼看立春,万物复苏,武落蘅的身形也一天大似一天,李隆基没了烦心事,也能好好的陪在她身边。
“奇怪,我看你这肚子可比五个月的大不少,竟像足月的样子。”李隆基轻轻抚摸着武落蘅的肚子,任由她将双腿放在自己身上。
武落蘅也不知怎的从上个月开始自己的肚子竟像吹气球一般,呼的一下大了起来,自己的食量也是平时的三倍,有时候刚吃完又觉得饿得慌。
听她这么说李隆基连忙让清莲去请御医,要当面问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