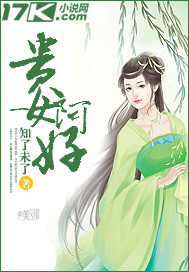初三清风书院一别后,范秦苑一直没有再出现宫中,学上也是匆匆而来,慌慌而去,连武落蘅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范卿,事情查的怎么样了?”李隆基下朝后立刻回到贞观殿,因为今日是他与范秦苑相约之日。
十五日前,在清风书院对对后,姚玉陪着武落蘅到后街玩乐,李隆基则与薛林凌,范秦苑同在书院煮酒围炉,三人正饮的畅酣,突然有一白衣书生闯了进来,双眼含泪磕头不止,还未问及原由,只见那人从怀中掏出血书大喊冤枉。
此书生名叫张九龄,其父是淮南御盐行道衙门主吏使张鑫,因发现上级御盐私用,更改官船盐运记录,使得官盐转做私盐卖,从中得利,而欲上书户部揭发此事,谁知三个月前,户部回文说事关重大让其父连夜兼程赶到洛阳亲自面圣,可是父亲一去数月音信全无,他甚是担心,才来到洛阳寻父。
谁知一到洛阳便看到秋决告示,原来自己的父亲早在秋决时便被斩首,罪名竟是贩卖私盐,自己到大理寺,刑部多次申诉,根本连门都进不去,所以才投身到清风书院,希望能考取功名,为父伸冤。
而血书正是张九龄为让自己牢记家父冤情,激励自己所写,李隆基看后不禁觉得字字诛心,更觉得他文采飞扬,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一边命范秦苑暗中追查此事一边请薛林凌好生照顾张九龄,说他以后必成栋梁之才。
范秦苑利用与张说的关系,到大理寺去调阅卷宗,其中发现不少疑点,更与张说发现卷宗中证明张鑫贩卖私盐的罪证居然与王吉案中的借条如出一辙,这让张说很是兴奋,大胆推论小心查证后终于理清。
今日范秦苑正好与张说同来回话,“回禀陛下,臣等已经查清,张鑫所举报官员乃是淮南御盐行道衙门主司陈怀德,他利用职务之便更改官盐账簿,私售私盐,与他对接之人正是王吉,他们以借条为传递凭证,未免暴露官员间私相授受,他们已贾岩为借款人,其实质指的是假盐,并非个人。”
李隆基一边听他说一边打开奏章仔细阅读,有理有据很是明了,不过张说也补充道:“陛下,臣想王吉也许是个关键,这么大的利益链不可能只有两个人,臣请搜查国舅府。”
李隆基将奏章合上,大骂道:“王守一已经关进大理寺,哪里还有什么国舅府,不必请旨,你们去查就是。”
两人拱手正准备离开,张说突然停在原地,李隆基见状问道:“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张说犹豫了一下,正声说道:“陛下,王吉曾在兵部任职,王守一与姚相曾定过儿女嫁娶事宜,臣恐这么查下去难免会……”
李隆基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便从怀中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玉佩,交给苏盛,“见此物如朕亲临,你们好好给我查一查,是谁干出此等祸国殃民之事。”
范秦苑与张说领旨后退出贞观殿,范秦苑不解的问到:“张兄一向谨言慎行,未有把握不会多言,这次为何会把皇甫大人,姚相一同说出?”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确没有证据能说明是他们某人主使,但范兄想想,只靠王吉他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私售私盐只会是一处御盐行道衙门所干的事情吗?”张说所言范秦苑也曾经想过,不过他仍不愿相信,朝廷明令法旨私售私盐会被除以极刑,为什么还有人甘冒其险。
二人离开后,李隆基同样也陷入苦恼中,自己虽然让他们放胆去查,可是若真是朝廷上下无一块完璧自己又该如何是好?
正在此时清莲在门外请见,说是惠妃请陛下过去尝新花样,李隆基正好心里烦闷索性去武落蘅那里放松一下。
还未到鹿鸣殿,却遇到站在竹林边哭泣的德妃,李隆基也不能当做没看见,便上去询问道:“德妃,怎么在这梨花带雨?”
皇甫裕婉听到李隆基的声音,连忙擦干了泪,回身行礼道:“陛下有礼,臣妾失礼了,刚刚在此看竹出神,竟没注意到陛下。”
李隆基觉得奇怪,看竹怎么能看哭了,自己不免也凑上前仔细观瞧,原来这茂密的竹林中有一窝鸟雀,想来是前几日大风把鸟窝吹落了,可怜这些刚刚孵化的小鸟嗷嗷待哺,其母却找不到巢穴,如何能哺乳。
“苏盛,叫人小心一点,看看能不能养活。”李隆基吩咐道。
皇甫裕婉马上走上前说道:“陛下,可否将小鸟交与臣妾,一来臣妾可以悉心照顾,二来也能让瑶儿学些怜悯之心。”
这一番话说的李隆基心里暖暖的,不禁盯着德妃细看,不由自主的说:“德妃总是如此善良,叫朕欣慰。”
皇甫裕婉脸颊微红,害羞的说:“臣妾与兄长自小在父亲膝下学习,父亲曾以育鸟教导我们兄妹,要善待每一个生命,分食要公平不藏私心。”
李隆基点点头,“难怪你也要言传身教,等过几日,朕去你宫中看看瑶儿。”
皇甫裕婉含笑屈膝,“是,瑶儿前几日正好会唤父皇了,陛下来了可听他的小奶音。”
李隆基心里还记挂着武落蘅,便点头离开了,皇甫裕婉微笑着目送他离开后,长出了一口气,站在身后的司书问道:“娘娘怎么不帮公子说说私盐的事?那张说可是怀疑到公子的头上了。”
“不过是怀疑,没有证据不能作数,陛下现在肯定对此事特别敏感,我要是求情了岂不是自乱阵脚。”皇甫裕婉在李隆基出现前,刚刚从范秦苑那里打听到案件进展,王吉的证据与兄长无关,只要能把王守一解决便不会露出马脚。
李隆基刚到鹿鸣殿就听到里面传来阵阵笑声,似乎不止武落蘅在,果然走进一看姚玉也在,她二人正在桌案前涂涂画画。
“什么事这么好笑?”李隆基好奇的问到,顺便看了一眼桌上不知是何物的吃食,略带谨慎的说,“婠婠这又是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上次的布丁可是让我苦不堪言呀。”
武落蘅前几日凭着记忆做了一款布丁,当然没有现代装备,做起来总是怪怪的,最后李隆基试尝的时候,差点没甜死,愣是喝了半天的茶才冲淡嘴里的糖精味。
武落蘅拿起刚刚打发的蛋白得意的说:“三郎放心,今日这个定能让你回味无穷,我做了个蛋糕,马上蒸好,再加点奶油就行了。”
“蛋糕?”看着几乎已经变成案板的书桌,李隆基真是哭笑不得,前段时间心血来潮学对对子,这书房还好好的像个样子,现在又做什么新鲜花样,书房都快要变厨房了。
姚玉手上都是面粉,也不知该如何行礼,只好比划一下,说道:“陛下,臣妾去收拾一下,您先外面请,臣妾给您倒茶。”
倒茶倒是其次,主要是她实在觉得书房已经无处下脚,趁着李隆基来此找个理由出去避一避。
退步出了书房,李隆基在厅上坐下,一边喝茶一边欣赏武落蘅的“功夫”,只见她一会右手快速画圈,一会又换到左手,停歇之后索性左右开弓,弄得蛋液四处飞溅。
“陛下,这是臣妾早些时候做的桂花酥,请您先尝一尝。”姚玉转眼间已经洗手净面把围裙摘掉,不过发丝上还悬挂着点点面粉。
李隆基尝了一口,不禁称赞道:“没想到贤妃的手艺也这么好,朕还是第一次尝到这么好吃的桂花酥。”
姚玉笑了笑,喃喃的说道:“陛下过奖了,臣妾这都是小时候跟母亲学的。”
李隆基不免感叹道:“姚相一手好字你练得,母亲的好手艺也得真传,二老也该知足。”
这话听起来有些奇怪,原来李隆基是在想近些日来,多有言官上奏,说姚相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又翻出几件旧案,说他有意包庇手下,再加上今日张说之言,未免让他有些心寒。
姚玉早知道这些事情,想到姚相让她在陛下面前求情,今日此景正好可以说出,“陛下明鉴,臣妾知道近日外界流言四起,说臣妾之父有诸多恶行,臣妾并不相信,也请陛下不要轻信小人的谗言。”
李隆基转头看向姚玉,冷笑道:“小人谗言?贤妃久居宫中是从哪里听来的小人谗言呢?”
姚玉被问得哑口无言,不知如何作答,李隆基复而质问:“更何况朕的大理寺多有正中不阿之人,中书省也不乏刚毅正义之臣,怎会任由小人进谗?贤妃是多此一举了吧!”
说完李隆基起身甩袖离开,姚玉呆坐在席上惊恐万分,武落蘅不知情况,只看到李隆基径直离开,疑惑的走出来问:“三郎这是要去哪呀?”
姚玉泪光点点,想到母亲还在姚府不知要受何种待遇,心里焦急万分,见武落蘅问,连忙跪着爬到她身边,呼喊着求道:“姐姐可要帮妹妹一次,救救我的母亲。”
武落蘅十分诧异,将手中器皿交于烟波,扶起她轻声说道:“你别着急,慢慢说,能帮上忙,我一定会帮的。”